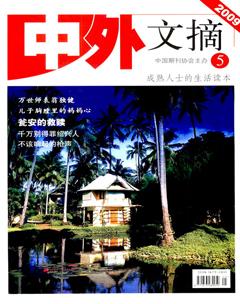古代公務員如何上班
2009-08-11 02:58:32完顏紹元
中外文摘
2009年5期
完顏紹元
雞鳴即起
古代的上班下班時間,和現代相似,也是晨聚昏散,但具體時辰上又比現代一般機關之朝九晚五的通例要提前,與農業社會中大多數人的作息習慣相適應。《詩經·齊風·雞鳴》中,妻子催丈夫起床:“公雞已經叫了,上朝的都已經到了,東方已經亮了,上朝的已經忙碌了”(雞既鳴矣,朝既盈矣;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因知古人雞鳴即起準備上班的傳統,至少在春秋時代就已形成。往后,這個時段逐漸定型為卯時(早晨五至七時)。
由中國傳統的行政體制所決定,古代公務員的所屬機關,可分中央和地方兩類。凡在中央各機關供職的官員,一定品秩以上,或有職務所規定,必須參加由君主親自主持的最高國務會議,通稱朝會,故京官上班的第一道程序,便是“上朝”,亦稱“朝參”。朝會有大朝、常朝等區分。《梁書·武帝紀》里有一篇梁武帝的詔書,道是一切國務,必須先在朝會上咨詢大家的意見,所以百官應該“旦旦上朝,以議時事,前共籌懷,然后奏聞”。也就是說,除法定的節假日外,這種具有實際內容的常朝,幾乎每天都要舉行。倘是君主生病或怠政,所謂“從此君王不早朝”,那便是例外了。
借光行路
上朝規矩,除一二品大員年高者,特賞可以騎馬或坐椅轎外,其余人一律步行入宮。又因隨從不得跟入的緣故,沒人給你舉燈照明。說是黎明開會,但若是把從宮門步行到朝殿(開會的大殿)這段距離算上,加上御史整隊、等候傳呼,得提前一些時間抵達。明高啟《早至闕下候朝》詩云:“月明立傍御溝橋,半啟拱門未放朝。……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