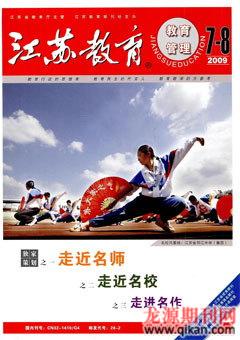啟功:歷史煙云里的文化追憶
周維強
最早知道“啟功”這個大名,是從《紅樓夢》這部書上。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我還在念中學,曾經囫圇吞棗地讀過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的程乙本《紅樓夢》,見書內標明啟功注釋。這么一部大書(“文革”曾傳毛澤東說《紅樓夢》要讀多少多少遍),名物典章、風俗人情這么多,以一人之力作注(魯迅先生的著作就不是靠一個人給注解的),“啟功”這人真了不得!
及至念大學,才知“啟功”是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的教授,點校過《清史稿》,與也是畢業于北師大的王重民等著名學者一起編校過《敦煌變文集》。他又是滿清皇族后裔,名牌大學“博學宏詞”的學者,還有“家學”淵源,當然也就能以一人之力給《紅樓夢》作注了。后來又陸陸續續從《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文史》、《學林漫錄》(后兩種均由老牌的中華書局主辦)等雜志上,讀到啟功先生的談學(學術)衡藝(書藝)的論文、札記,以及回憶齊白石老先生等的散文,其行文清雅簡潔,句句不落空,很耐讀。我很喜歡,所以就常常會去找啟功的著述來看,譬如那時剛由中華書局印出來的《啟功叢稿》(是一卷本,不是前幾年出的三卷本)。俞平伯先生允推啟功先生的識見和功底,還說過“注《紅樓夢》非啟元白(引者按:啟功,字元白)不可”的話(見鄧紹基《讀啟功先生的學術著作》,載《啟功學術思想研討集》,北師大中文系編,中華書局、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7月)。“貴胄天潢之后常出一些聰明絕代人才。”則是上個世紀50年代葉恭綽老先生在閑談中對啟功等人作的考語(參見黃苗子《夕陽紅隔萬重山——啟功雜說》,載《畫壇師友錄》,黃苗子著,三聯書店,2000年6月)。
聽系里的先生說,啟功對故宮內的藏品,對故宮,對清史,如數家珍。這些該是屬于“傳聞”吧。今讀《啟功口述歷史》(啟功口述,趙仁珪等整理,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7月),確知這是事實。啟先生說:
……從1971年7月一直干到1977年,任務是校點“二十四史”。我的具體任務是校點《清史稿》……和我一起負責點校《清史稿》的還有劉大年、羅爾綱、孫毓棠、王鐘翰等先生,其中劉大年先有事撤出,后羅爾綱、孫毓棠也因病離去,只有王鐘翰和我堅持到最后。在我們接手之前,馬宗霍等人已經作了一些初步的整理,但遺留了很多的問題。據他們說整理此書最大的困難有兩個:一是滿清入關前,即滿清建立初期——努爾哈赤時代,很多典章制度都不系統明確,很多記載也比較簡略凌亂,整理起來很困難;二是清史中的很多稱謂,如人名、地名、官職名,和歷朝歷代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特別是人名,本來就挺復雜,再加上后來乾隆一亂改,很多人一遇到這種情況,就拿不準、點不斷了。
但啟先生熟稔滿清典章制度、清人稱謂等等,所以他在這部口述歷史里接下來很自信地說道:
但正所謂“難者不會,會者不難”,這些對我來說就跟說家常一樣,易如反掌,因為我對滿人的這套風俗習慣和歷史沿革還是很熟悉的。所以工作量雖然很大,一部《清史稿》有48大本之多,但工作一直進行得很順利,發現并改正了大量的錯誤,如《清史稿》中居然把宋朝人的、日本人的著作,甚至對數表都放了進去。經過點校,《清史稿》和其他各朝正史都有了準確、通行的本子。
《王鐘翰學述》(王鐘翰著,姚念慈等整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有關點校《清史稿》的記述,可以作部分的旁證。王鐘翰還說道:啟功和王鐘翰曾向當時的中華書局領導提及要做《清史稿》的《校勘記》,“回答是從未向上級提及《清史稿》要做《校勘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還是以不出《校勘記》為妥。那時,剛剛打倒‘四人幫,也可以說這是一個時代的印記。”(《王鐘翰學述》)。
啟先生學問中很多部分得自親歷親驗親見親聞,而不全來自書本,這恐怕是其他治清史者不太可能有的。啟先生在這部口述歷史里說道:
從原始含義來說,文是文,獻是獻。早在《尚書》中就有“萬邦黎獻共惟帝臣”的說法,孔穎達注曰:“獻。賢也。”孔子在《論語》中也說過:“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朱熹注曰:“文,典籍也;獻,賢也。”可見,“文”原是指書面的文字記載,“獻”是指博聞的賢人的口頭傳聞。
所以啟先生說:
我從長輩那里聽到的一些見聞,也許會補充一些文獻中“獻”的部分。
司馬遷寫《史記》,有的材料就是得自民間而非書本(著名的如《項羽本紀》、《孟嘗君列傳》、《魏公子列傳》等篇章都有例可證)。也是這個緣故,我也很喜歡讀一些記錄“三親”(親歷、親見、親聞)的文章。譬如啟先生這部口述歷史書里記錄的有關乾隆皇帝為什么對太后非常“孝敬”,乾隆跟他的同父異母的弟弟和親王之間的關系,慈禧和光緒為何會同日而死的“內幕”等等,啟先生娓娓道來其中的故實,一一點破其中的關節。這里面就有許多材料可以補充我們從書上得來的知識,增廣我們的見聞。這都記在《啟功口述歷史》這部書里,用不著一一轉述其詳了。我尤其感興趣的是這部書里記錄的過去學校里的氣氛,師生的關系,其間大有深意。“入學前后”一節里有很多發生在北京匯文學校里的有趣的校園故事,其中有一個是這樣的:
……我和張振先是同桌,一到課間休息,甚至自習課老師不在時,我們倆就常常“比武”,看誰能把誰摁到長條凳上,只要摁倒對方,就用手當刀,架在他的脖子上說:“我宮了你!”算作取得一場勝利。直到幾十年后,我們在歐美同學會吃飯時,彼此的祝酒詞還是“我宮了你”。這種童真和童趣是非常豐富值得珍惜的,有了它,人格才能完整。而開明的老師,常能容忍孩子們的這種天性,這對孩子的成長是有利的。
還有一個故事也很有趣:
我們班有一個同學叫宋衡玉(音),平時常穿日本式的服裝。我們都管他叫“小日本”,他自然不愿意聽。有一回在飯廳吃飯時,有人又叫他“小日本”,他急了,追著那個人不依不饒,那個人就往飯廳外跑,他嘴里罵著“兒子(讀作zeU)!兒子!”地往外追,正好和路過的校長撞個滿懷,校長擰著他的嘴巴說:“你又沒娶媳婦兒。哪來的兒子?”大家聽了哄堂大笑。因為大家覺得校長實際上是以一種幽默的方式加入到這場游戲中了。
講完了學生們淘氣的故事后,啟先生又說:
……我不是提倡淘氣,但興趣是不可抹殺的,在這樣的學校,每天都有新鮮有趣的事發生,大家生活、學習起來饒有興致。
在教會學校輔仁大學,有幾則師生的故事,也許也是有深意在的。譬如國文系主任尹石公(炎武)與學生的故事。尹石公“平常愛當面挖苦學生”。有一回,兩個學生張學賢、楊萬章作文沒做好,尹石公就當面譏諷他們道:“你居然叫‘張學賢,依我看你是‘學而不賢者也:你還叫楊萬章,我看純粹是‘章而不萬也。”尹石公的挖苦都有出典,“學而”是《論語》中的一章,“萬章”是《孟子》中的一章。但接下來,事情弄大了:
不料第二天他(引者按:指尹石公)再去上課,這二
位(引者按:指張學賢、楊萬章)給他跪下了,說:“我們的名字是父母所起的,如果您覺得哪個字不好,可以給我改;我們學業有什么問題,您可以批評,但您不能拿我們的名字來挖苦我們,這也有辱我們的父母。”尹先生一看二位較上真兒了,也覺得大事不好,連忙道歉,問有什么要求沒有。這二位也真執著,說:“我們也沒什么要求,只求您以后別來上課了。”尹先生一看玩笑開得太大,沒法收拾了,便很識趣地寫了辭職報告,打點行裝,到上海文物管理委員會另謀職業了……
這個故事,可能會對治民國高等教育史有用:對一般的教師,也許也會有點用處,啟先生接著說:
現在想起來,這雖是一時的笑談,但陳校長(引者按:指輔仁大學校長陳垣)的教導:“對學生要多夸獎,多鼓勵,切勿諷刺挖苦他們”是多么的重要!
這部書還記錄了老先生們——如賈羲民、吳鏡汀、戴姜福、陳寶琛、齊白石、張大千、陳垣、楊樹達、余嘉錫、陸志韋、馬衡、沈兼士、唐蘭等等,以及溥心畬、溥雪齋——的許多逸事,叫我們想見那個時代的老先生們,以及滿清皇族藝術家們的風貌,還有書畫鑒定里的種種掌故,真是很有趣味。
啟先生的書畫造詣、古文獻學和文物書畫鑒定的學問,大名鼎鼎,“藐予小子,何敢贊一詞!”啟先生在書中說他的“書畫鑒定”:
……自解放前就擔任故宮專門委員的,到今天只剩下我一人了,經我眼鑒定的文物大概要以數萬計,甚至是十萬計,從這點來說,我這一輩可謂前無古人,他們從來沒見過這么多東西,就憑這一點我就應該知足了。
我讀到這里,所起的就不是“知足”或“不知足”的感嘆,而是想起古語“觀千劍而后識器”。在高科技尚未廣泛用于書畫文物的鑒定之前,沒有對實物的博觀,哪里談得上“鑒定”!以前考古學界有人說,早年就學于北師大史學系的北大考古系的祖師爺蘇秉琦老先生好閉著眼睛摸陶片,于是北大的同學也學蘇先生閉著眼睛摸陶片。雖則蘇先生說這話“三分是夸張,七分是誤解”,但他也還是從長期的考古實踐中認可這個“摸”對陶器的考古的重要性(參見《中國文明起源新探》,蘇秉琦著,三聯書店,1999年6月)。引申到書畫的鑒定,應與啟先生的體會是相通的吧。所以我認為現在以收藏文物書畫為個人投資者,多半屬于不得要領而把錢去打水漂的。還有誰能像啟先生他們那樣看過那么多的古代書畫啊!見不多識不廣,談什么鑒定?無鑒定又哪來收藏?古玩字畫鑒定不易,就是當代名人書畫,被造假亦有幾達亂真的。據聞京城潘家園,有名的古玩市場,各地畫商來這兒批發當代名人字畫贗品,“捆載而去”(見《雀巢語屑》,唐吟方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2月)。自己若無鑒定的法眼,要以收藏古玩書畫作投資,難保不會像俗語所說“被人賣了還在幫人數錢”。
現在再來說說《啟功口述歷史》這部書的記錄。有的事,相同的一件,不同的人卻有不同的記錄。譬如點校《清史稿》,前引的啟先生的口述是:“但正所謂‘難者不會,會者不難,這些對我來說就跟說家常一樣,易如反掌,因為我對滿人的這套風俗習慣和歷史沿革還是很熟悉的……”但在《王鐘翰學述》里,則有另外的記錄,王鐘翰說,有一回啟功對他說:
五禮的吉、嘉、軍、賓、兇中,我也許知道其中一小部分,哪能什么都知道呢?
啟功還“感慨說”:
我們雖然從事清史研究有年,在某些方面也許多少有些一知半解,但就整個清朝一代300年全面來說,叫我們來干這項工作,是很不合適的,而我們實在也干不好。
記錄這些話后,王鐘翰又說:“啟兄所云,實是通人之論,我也深有同感。”
按王鐘翰的記憶,啟功負責《清史稿》的“志”的點校,則啟功后來在《啟功口述歷史》中所言(“我對滿人的這套風俗習慣和歷史沿革還是很熟悉的”)應是實話實說。如果王鐘翰記憶無誤、記錄準確,那么,啟先生前后對同一事的不同態度(前者“謙卑”,后者“自信”)的變化,細加考究,也許是很有意思的,至少可以表明,在不同的年代里,啟先生這樣的曾被劃作“右派”、“文革”中又被當成“準牛鬼蛇神”的老知識分子。其精神風貌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還有一些事。啟先生本人即有不同的記錄。舉一個例子。在輔仁大學時,有一次,啟功作詩寫溥心畬故居恭王府的海棠,有句云“勝游西府冠郊堙”(海棠常稱西府海棠,“西府”是海棠的品種之一)。啟功拿給陳垣校長看,另一位“同門”(柴德賡)也在。這位“同門”說“恭王府當時稱西府呀?”《啟功口述歷史》里接下來說:
陳校長仍不說話,又用手朝他(引者按:指啟功的那位同門柴德賡)一指,柴德賡馬上意識到又出錯了,臉都紅了。
但是啟功在寫于1980年6月的《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載《勵耘書屋問學記——史學家陳垣的治學》,三聯書店,1982年6月)一文里,卻是這樣寫的:
……老師(引者按:指陳垣先生)笑著用手一指,然后說:“西府海棠啊!”這位“同門”說:“我想遠了。”
這兩處的記述就有比較大的差別,不知該以哪一處的記述為準。
從《啟功口述歷史》一書的編輯來看,也許還可以加一個附錄,譬如啟先生刊于《北京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5期上的《北京師范大學百年紀念私記》一文,就可以作為附錄,可跟正文對照閱讀。《啟功口述歷史》“院系調整”一節里,說上個世紀50年代,北師大中文系有位教授“專赳李長之先生”:
……有一位教授,雖不是黨員,但比黨員還黨員,成了當時的“理論大師”。他現淘換一些馬列主義的詞匯標簽到處唬人……他的學問是很有功底的,也深通義理之學……他專赳李長之先生……
這段歷史對過來人,當然很清楚,對其他人就未必了。《北京師范大學百年紀念私記》對這位教授則有指向更明確的表述:
當時中文系師生許多劃為右派,只有劉盼遂先生讀書多,記憶強,雖沒劃右派,但口才較拙,上課后在接著的評議會上,總是“反面教員”。譚丕謨同志最受尊敬,王汝弼先生常引馬列主義,學生也無話可說,他在批判別人時常給他們加上一些字、詞,被批的人照例無權開口
再譬如,《北京師范大學百年紀念私記》里說,“文革”結束后,“原來的系主任還有時根據蘇聯專家留下的理論,說只要把書教好,不需要什么‘科研。他帶的碩士研究生不許做論文,而學校制度已然規定要通過論文。學生只得拿著論文請旁的老師為他看”。而在《啟功口述歷史》“院系調整”一節里,對這位“原來的系主任”則有指向更明確的表述:“師大初建時(引者按:指1952年前后院系調整時的北師大)任副系主任(引者按:當時僅一位系主任,一位副系主任)后來又擔任過主任的那位教授。”
舉這兩個例子只是想說,把啟先生以前寫的有些文章,作為這部書的附錄,恐怕也是有必要的。
最后給這部書的整理工作,提一個小小的意見。這部書,從頭至尾,直到整理者趙仁珪教授寫的《后記》,均無啟先生口述時的時間和地點的明確的記錄,只在《后記》里籠統提到一句“啟先生在九十一歲高齡的時候……為我口述了他的經歷”。這對于口述史學來講,也許是不太夠的吧。
佳作鏈接:
1,《知堂回想錄》,周作人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
本書是周作人最后一部作品,也是他畢生篇幅最大的著作。著者說:“文中多有跑野馬處,或者還跑得不很夠,亦未可知。但野馬也須在圈子里跑,才有意思,這卻極不容易耳。”此言得之。
2,《黃藥眠口述自傳》,黃藥眠口述,蔡澈撰寫,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
此書詳細記錄了藥眠先生坎坷、傳奇的一生,尤其是他鮮為人知的追求和參加革命的經歷。先生是一個著名的文化老人,文藝學家,美學家,詩人,教育家,半世動蕩的回憶,未及全部寫畢,即與世長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