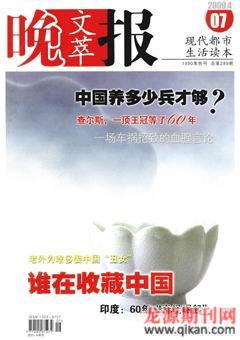不是所有民族都能有一個國家
馬少華
春節長假,游覽了位于太平洋北馬里亞納群島的塞班島和天寧島。一個突出感受是:美麗的風光與殘酷的歷史,再沒有像在這里一樣表現得如此沖突。對于這幾個島上的原住民族查莫洛人和卡羅尼亞人來說,他們有的只是別人的歷史。具體而言,是美國和日本軍隊在二戰后期殘酷廝殺的歷史。每一個民族都不會沒有自己的歷史,但在今天的塞班島和天寧島,歷史敘說的空間,已經被60多年前的槍炮聲充滿,就像二戰的各種遺跡、指示標牌和日本人的墳墓、紀念碑充滿了這兩個小島一樣。
對塞班,我不能順口稱其為一個“島國”,因為它確實不是一個國,也許從來也不是。塞班和天寧給我一種中國人難以理解,也從未有過的感受,那就是:不是所有的民族都有一個國家,也不見得所有民族都需要一個(自己的)國家。至少從1565年西班牙人登陸該島后,這里就是一個又一個西方列強的殖民地,先后經德國、日本的長期殖民和美國的長期托管,直到1986年,北馬里亞納群島經全民公決,歸屬美國。所以現在,這幾個島的人民是美國公民,這幾個島很小的政府機構上空,飄揚著美國國旗,這幾個島的海岸和海面上停泊美國軍艦,盡管全世界大多數人知道的美國,遠在離他們數千里外的美洲大陸上。美國需要太平洋中的這個戰略據點,而當地人民只需要無憂無慮的和平生活。我們在塞班全島的最高點,看到三艘美軍補給艦紋絲不動地停在塞班近海。據說,塞班人每天早上只要看到這三艘美國軍艦還好好地停在那里,就會心神氣定,認為天下太平。如果哪一天美國軍艦突然看不見了,那就是出事了:要么去外海增援戰事;要么臺風來了,需要到島的另一側避風。所以,那三艘美國軍艦差不多是塞班人的定心丸和天氣預報,關系著全島人心穩定,輕易不能挪動。
我想,在塞班原住民這樣長期的被殖民、被托管的歷史境遇中,民族國家的觀念、民族國家的需求早已經消失了——也許根本就不曾存在。實際上,民族國家的觀念本身就是近代歷史的產物,是民族覺醒、民族奮斗的歷史產物,并非從來就有。
二戰歷史,作為一種“旅游特色”,與原住民的土風舞不同,其實帶有強勢的民族國家的遺響,是強勢國家意志在美麗風光中的強烈表達:包括位于天寧島的美國轟炸日本的原子彈裝載地遺址、被美軍轟炸得只余斷壁殘垣的日本空軍司令部遺址;位于塞班島萬歲崖的日本“忠魂碑”——至今紀念著被美軍趕到海島邊緣、高喊著“天皇萬歲”跳崖的日本軍人和婦孺。這座從日本本土運來、用隕石雕刻的紀念碑和旁邊的幾座紀念碑,我感覺有一點美化侵略戰爭的嫌疑。導游告訴我們,它又被人們稱做“口香糖碑”——因為韓國游客到了這里往往用口香糖粘滿碑體,以表達他們的民族仇恨;而日本游客到此碑前,則人手一只小鏟,為他們的“忠魂”鏟去滿身的口香糖。兩個國家的民族意志和歷史情感,至今仍然在這塊碑上對抗性地表達著。這些,都并不是美麗風景的一部分。
中文中有一個詞,叫做“煞風景”。我就覺得,塞班人讓別人的歷史煞了自己的風景,盡管這個小島對自己的自然資源愛護有加,法律禁止任何人哪怕帶出一只貝殼。在日本人立的“忠魂碑”前,我想到:任何一個主權完整的民族國家,都不允許有人在自己的國土上為日本侵略軍人立紀念碑,何況這塊土地有著長期被占領、被殖民的歷史。這里很難被日本人當做一個風光旅游地,而是一塊傷心之地。因為觸目所見,皆是這個幾十年前過于強橫擴張的民族悲慘敗亡的遺跡。
我為那些在歷史中慘死的生命深深地感到不值。一種過于強橫的思想、信念、意識形態,應該為那些死難者負責,應該為一切死難的生命負責,應該對歷史負責。人類在任何時候,都應該對這種輕視人(同胞與他人)的生命而過于“重視”國家的思想、信念和意識形態保持警惕。
(摘自《紹興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