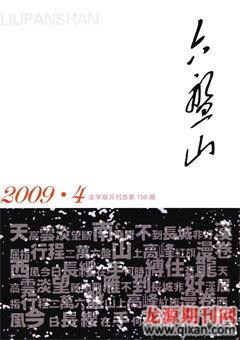駐足西域的筆墨
程耀東
不到新疆不知國土面積之遼闊,民族語言之繁復,糧棉之豐厚,瓜果之香甜;藍天白云色彩高遠,雪山草地層次明晰,戈壁與綠洲相互掩隱,油井與煤田互說冗長;哈薩克人的風干牛肉讓你贊不絕口,維族姑娘的歌聲帶你走進遠古,喀什噶爾的胡楊將精神的圖騰直插天域,塔克拉瑪干的荒漠讓荒涼更加荒涼;掬一杯天山天池的圣水洗滌被塵世玷污的靈魂……
投向交河故城的目光
我投向交河故城的目光,不是生硬,是柔軟。那天,濃烈的陽光潑灑在這些細密的黃土上面,氤氳如水溫順波動。
身臨其境之前,我在《中國國家地理》上見到過這座故城的照片。照片是表象的,是局部的;也曾在很多詩人、作家措述的字里行間里閱讀過故城昔日的輝煌和現在留于地表之上的秘密。詩人在歌唱,作家在憑吊。這是一座反復出現在攝影家鏡頭里的城池,在白天,在夜晚,在春夏秋冬的任何季節,每一秒鐘留給鏡頭的都是變化與變幻。
此刻,它正看著我漸行漸近的身,影,在我的目光里它的輪廓也越來越明晰。
滿目都是被風剝蝕后的黃土建筑,它們以一種集體的力量向四周擴散,一直延伸到兩條河交匯的地方。如果沒有這兩條河,也許就不會有它的存在。澤水而居,人類最原始的選擇。兩條河流以外,是廣袤的戈壁,在陽光下泛著白色的光芒。闊大的光芒,驕傲的光芒,驕傲得使人產生更多的嫉妒。區別于兩條河以外的地質結構,這塊黃土以渾厚的姿態高高地矗立于河岸之上,被河水潤澤,讓戈壁羨慕。是的,羨慕的不僅僅是不會說話的戈壁,還有會說話的人。很巧,從我身邊經過的一對老外大聲高呼:It's very beautiful。我想,任何一個人目光投于此處,他的心靈都會被這座廢墟震撼。
“廢墟?”這樣稱呼似乎不妥。交河故城,故從何來?最崇敬最標準的稱謂應該是2000多年前車師國的國都。這條貫穿南北的大道我們能想象出當年的繁華與威嚴。大道的兩側是極其華麗宏偉的建筑,黃土的影子被牢牢地包裹著。車師國里所有的財富堆積于此,國王想怎么設計就怎么設計,想怎么奢侈就怎么奢侈。然而,國王傾盡畢生的精力構筑的圣殿并沒有被他的子孫一代代傳承下去,而在歷史的流變中,又回歸于樸實無華的黃土。
成群結隊的駱駝在我左邊或右邊的河流里飲足了水,重疊著來時的腳印,緩緩地走向有草的地方。它們從來不在這座廢棄的城堡內歇腳,更不要說尋找草料,因為這里已經寸草不生了。它們的先祖肯定來過,看到過守門衛士的威武,街巷的繁華;聽到過商販的吆喝,更夫的梆聲;在胡楊下納涼,在城根下取暖……它們走得很慢,但最終還是甩開了不屬于它們的繁華與喧囂。因為,它們不屬于這座城堡。它們存在的意義是一生地行走,但它們的價值一點也不比站著的城堡卑微。
曾經附著于黃土之上的那些琉璃翡翠、雕梁畫棟哪里去了?也許就在我腳下。想想,我的腳下踩踏著一個王國的權勢和財富,踩踏著貴族與舞女的靈魂。這,一定嚴重侵犯了車師國王的法律。沒有辦法,物是當年物,人非當年人。這些非當年的人每天絡繹不絕地來此造訪,驚訝,好奇,吶喊,緘默,繪畫,拍照,直到日暮時分,鳥飛去,人散盡,懸浮的塵土重新落下。這些生于斯的黃土繼續鎮守一個王國藏于大地深處的秘密。
2000多年的一座城池,無疑是令人神往的。其間一定隱藏著諸多想象不到的秘密,而這些秘密很少被歷史的書頁記錄,因為它的歷史太久遠了,因為它被歷史遺忘得也太久遠了,我們只能在這些細碎的黃土中閱讀猜測它的過去。假如你的目光能夠穿過這些黃土的厚度,很可能和一個商人相遇。趕著駱駝的商人,褡褳里滿是來自中原的絲綢,西域的珠寶,他急匆匆地從你的身邊經過,留給你的是充滿提防的目光——商人的目光。繼續在故城的街巷里穿梭,我們還可以閱讀和聆聽到交河故城走向衰落時的呻吟。偉大的成吉思汗以及他的后裔們走出窄小的蒙古包,站在坦蕩如砥的蒙古高原四下張望,他們的戰馬就聞到了來自西域紫花盛開的苜蓿的馨香。伴著馬鞭的呼嘯,蒙古人的馬蹄停在了安詳、寧靜、富庶的交河城下。關于這場戰爭,沒有只言片語的記載。戰爭是怎樣的慘烈,是怎樣的殘酷,想象和描寫已經沒有了任何意義。一個國家一夜之間銷聲匿跡,一座都城一夜之間焦土一片。國破山河在。國破時車師人難道沒有撕殺、吶喊和抗爭,真的就埋在了這片不能言語的黃土下了?
一個消失了的國家,留給我的只有這片殘垣斷壁。
沒有了秘密可言,在歷史的夾縫中茍延殘喘的交河如今只是一條被時間流水沖刷過的干涸河床。河床中只有四季變化的溫度,屬于人的溫度與適度早已蕩然無存。即便這樣,胡楊與野草還是頑強地生長著。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被人類丟棄的王國的秘密只能與它們為伍。即便有人想要重新撿起來,也只能在黃土的黑暗里去尋求。
我站在被縮小了的交河故城的地圖前,順著導游纖纖細手指出的方向看,故城四面臨崖,在東、西、南三側的懸崖峭壁上開有三個城門。一條大道貫穿南北,把城區分為東西兩部分。東區南部為大型居民區,北部為小型居民區和作坊,市場,中部為官署區。西區多為寺廟和墳冢。城中大道兩旁皆是高厚的街墻,但臨街不設門窗。到了漢武帝時期,車師國被漢王控制。漢代的屯田中心遷至交河,交河成為西域的最高首腦機關——戊己校尉府。漢唐以來,交河的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佛教也隨之傳入交河。14世紀,蒙古貴族西征,攻破交河,屠城之后,一把大火。同時蒙古統治者還強迫當地居民放棄傳統的佛教改信伊斯蘭教。在戰爭和宗教的雙重打壓下,交河終于走完了它的歷史使命。我相信這是歷史事實,不是導游信口雌黃。戰爭就是戰爭,它的意義就是搶劫、掠奪、鎮壓和屠戮。車師人也好,蒙古人也罷,一座繁華了2000多年的城市轟然倒塌。歷史在這里被攔腰截斷,文化停止了傳承。
自蒙古人以來的800年過去了。它一直就這樣裸露著自己并不完美的體膚,被來來去去的人的目光欣賞,一點也不設防,不忌諱。然而,800年里又有誰把它當作了鏡子?我們認真地聆聽,仔細地閱讀,深刻地研究,所有投向交河故城的目光,目光有多深,意義又有多遠?
被精神養大的石河子
這是一座多草,多花,多樹的城市。
我走近她的時候,草,有節奏地生長。花,五顏六色地綻放。樹,瘋狂地抒發著自己的情感。花、草、樹之間的縫隙里,干凈無比,陽光也干凈無比。藍色十分均勻地分布在城市的上空。沒有一絲風,淡淡的云翳像哈薩克女人擠出的牛奶。
坐在廣場一塵不染的長凳上,我摘下遮擋日光的鏡片。一只細長柔軟的樹枝劃過我的臉頰,讓我有種酥瘁感。和樹枝同時光臨的還有樹枝上的果子。果子不大,向著陽光的一面紅得發亮。它們是城市最美季節的守護和見證者。多虧這些紅得發亮的果子,讓我認識到了一個城市的高度。偶爾也有落在樹下的果子,它們安靜地躺著,聆聽著大地深處的聲音,人的聲音,整個城市的聲音。不急不躁,那
樣自由散漫,直到自己的身體腐爛于其中。然而,這個城市里每天發生的事情,樹再也熟悉不過了。開花的春天,掛果的夏天,成熟的秋天,蘊藏的冬天。闊大的綠地和茂密的楊樹使得它的秋天分外妖嬈。幾只蝴蝶在草叢間輕盈緩慢地飛舞,有那么好看的一只竟然落在了我的鞋面上。
這是一座被詩歌激活的城市。
他沒有被這座城市遺忘。用他的名字命名的詩歌館很大,很高。我知道這是一個令人敬畏的高度,令中國詩人仰慕的高度。他的雕塑安放在這里,縷縷詩魂依然在他的頭頂縈繞。而他的眼睛滿含柔情,注視著過往的每一個人。“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有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是的,我深信在祖國廣袤的疆域上,詩人對腳下的這片土地愛得更為深沉。在這里,他有過近十六個春秋的生活,而且是在他的人生最為低谷的時候。
詩人叫艾青。
為詩人建館、雕塑,一座有氣魄有高度的城市。
在石河子的地域上,我幾次企圖尋覓當年艾青先生居住的地方,勞作的地方,不為別的,只為感受一下遺留在那里的空氣和空氣中彌散的詩歌的氣息。但我知道,詩人生活在這里,以求生存為主要,很少有詩作。詩,肯定是有的,只是深藏于詩人痛苦的內心,深藏于落日走向黑夜,黑夜走向黎明的夾縫里。
我曾在中國詩人網上見到過詩人和他的愛人高瑛在石河子時的一張黑白照片:照片上的詩人很消瘦,愛人跟在他的身后,兩人的表情比較松弛,很坦然,看不出生活壓在他們身上的苦悶和陰翳。這是兩張寫滿干凈的臉,或者說經過諸多風云變幻之后一對生死相依的戀人的臉。純真,純潔,透徹,無一絲隱瞞,如金秋時間新疆大地上綻放的棉花的色彩,這是生命中不可替代的色彩。
在這個陽光好的無可挑剔的下午,我與詩人的雕塑站在一起,空落的內心終于有了一次慰藉,心靈被溫暖而無邊無際的詩歌的語言包裹。
這是一座能留住時間的城市。
石河子是一座多雕塑、多博物館的城市。
周恩來雕塑、王震雕塑、艾青雕塑、軍墾第一犁雕塑。
周恩來紀念館、艾青詩歌館、新疆軍墾博物館。
周恩來紀念館與周恩來紀念碑相互對應。腳步總是勤快的共和國總理來石河子視察,看到大漠戈壁上茁壯成長的城市,被兵團人樂于奉獻的精神深深震撼,為兵團人題詞,鼓勁。碑高7.8米,象征周恩來享年78歲,碑文高6.7米,象征他來石河子時67歲。遒勁的字跡,用心良苦的數字,是石河子人智慧與情感的體現。
據說此雕塑為新疆著名雕塑。我漫步走過廣場,陽光仍然濃烈,鴿子在飛,鮮花在開,雕塑似乎將一切鐫刻于歲月深處,胸中翻滾的是一浪一浪兵團人戰天斗地的風云。
軍墾博物館收藏多為屯墾戍邊的歷史文物。一件物品,可訴說昔日荒原大漠開墾為農莊的景象;一件衣物,可透析勞作者來自肉體的汗水;一張照片,顯示著不屈的精神與堅毅的力量……屯墾戍邊,始于漢代。軍墾者,軍之開墾。放下武器的戰士,撲向土地,如一塊磁石,被耕植的愿望春天般一點點變綠。
博物館,記錄著城市的過去,同時也是對城市前行的另一種祝愿。有根就有枝條,有枝條自然就有綠葉,根壯則葉茂,養分便是人和時間。
廣場上的人越來越少,陽光透過斑駁的樹梢,落在我的身后,身后回響著詩人艾青的聲音:“我到過許多地方,數這座城市最年輕,它是這樣漂亮,令人一見傾心,不是瀚海蜃樓,不是蓬萊仙境,它的一草一木,都由血汗凝成。”
再見,被精神養大的石河子;再見,大西域這座年輕的城。
溫暖而干凈的天池
我在用心凝望著這片久負盛名的水域。
高遠的藍天一不小心將自己身體的一部分碎在了這里,碎成了蕩滌心靈的圣水,碎成了用藍寶石鑲嵌在群山懷抱中的一面大鏡子,鏡子無語。每一個慕名而來人,看見鏡子的同時也看見了自己的罪過與良心。罪過。良心。是兩個唯心的詞,兩個看似簡單而內涵豐富的大詞,它們之間僅僅隔著一滴水的距離。上善若水——老子在他的《道德經》里解釋得更為透徹。
坐在天池邊的一塊石頭上,我用手遮住來自雪峰之外的陽光。皚皚白雪在冰冷與寂靜中俯瞰著天池的波光;巍峨、睿智、沉默、冷峻、又至高無上地統馭著這里的一切。雪山之上的天空被排擠到更高的天宇,只好散漫著游弋著漠不關心的向這里張望,一百年,一千年,一萬年持之以恒。
雪線以下,被無可爭議的茂密挺拔的松樹霸占著。它們是天池一年四季的守望者。在這個白色彌漫的秋天,多虧了這些綠色濡染的松樹,它們讓我領略了生命的高度。偶爾會有一只鷹在它們的頭頂盤旋,飛翔的節奏那樣緩慢,是在欣賞天池秋日的圖景?是在聆聽天籟之音?是在尋找屬于它的目標?我無法想象和描述。
與松樹為鄰的,是針葉與闊葉混雜的小塊平疇。透過樹的縫隙,哈薩克人白色的氈房和縹緲的炊煙若隱若現。幾匹馬啃著樹下的青草,不時甩動的尾巴讓行走在它周圍的羊一驚一乍。羊的叫聲驚擾了正在喝奶茶的主人,主人走出氈房,繞著氈房轉上一圈,很快又鉆了進去,繼續他的“茶文化”。
執著不去的還有陽光。在我旅途經過的有限的地方,不會有那一處能與天池的陽光相提并論了。它高懸在空洞的天域,無遮無掩,讓你無法看清它。來自雪山之上雪的光芒與太陽的光芒相互疊加,炫目的光芒令人屏住呼吸。太陽沒有自己的語言,也沒有自己的文字,可是它創造了無數讓我們表達的欲望。這時候,文字的描述是蒼白的,鏡頭只是一個瞬間,畫筆只能寫意,來自細節的美麗只有你身臨其境才能捕捉到。
天池就被這樣的大美環抱著。這個時候,她在我的眼里顯得很小,像一個嬰兒,熟睡在母體的懷里,身體裸露,肌膚光潔,讓人一覽無余。我蹲了下來,試圖洗一下我的手。在我的手和目光觸到水面的那一刻,心靈被一種寒冷掠過,旋即將手收回。這樣的一池澄澈,我的手會玷污她的靈魂,弄臟她的衣襟。將目光順著水面閑緩地收回,收攏藍天、白云、雪峰、森林與這碧水渾為一體構成的瑰麗畫面。岸的那一邊,一對老人靜靜地坐在石頭上,享受著陽光與水的柔和,神情被這凈水映得愈顯精神了。刻有“圣水祭壇”的那塊石頭旁,男男女女排著隊在拍照,秩序倒也井然,沒有喧囂,也不爭搶。眼睛里的光芒與水的光芒融在了一處。
坐在岸上看風景的還有西王母。這位傳說中的王母曾來此地沐浴,洗去了一身的污垢與疲憊之后,再也沒有離開這里。屬于她的廟宇高高在上,她的塑身落落大方,面容溫和而目光靜佇于水面之上,廝守一池撒滿了陽光的秋水。四時之景在變,不變的是她的目光。坦誠地說,我的雙腳丈量過的山水不少,有人的足跡就有佛與道的影子,看來美麗的山水佛也熱愛!
我打算是要等到太陽落山時看看晚霞中的雪山、松濤和天池的,然而在這里原本屬于我的時間被旅行社的導游分配了。沒有辦法的事情,已經習慣了身不由己。千里之外朝思暮想,不為別的,只為抵達你的高度;千里迢迢一路西來,不為膜拜,只為途中與你相見。留一點遺憾,便多一份記憶。感謝你,溫暖而干凈的天山天池,雖然只是浮光掠影,可在我內心,卻是巨大的充實和安慰。
(責任編輯:楊風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