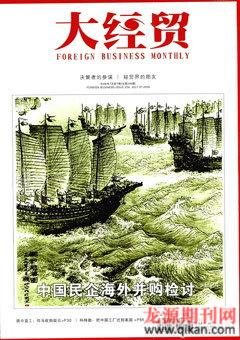聯(lián)想:走向世界的挫折
李 治
日前公布的聯(lián)想2008/2009財(cái)年報(bào)告,披露聯(lián)想巨虧2 26億美元。這是聯(lián)想10年來的首次虧損。
聯(lián)想的虧損主要包括兩大部分,一是營業(yè)性虧損,二是高達(dá)1.16億美元的重組費(fèi)用。如果說前者可以用全球經(jīng)濟(jì)不景氣導(dǎo)致業(yè)績下滑做遁詞的話,那么后者可以說是聯(lián)想高層一系列戰(zhàn)略失誤的累積效應(yīng)。
聯(lián)想的巨虧是意料之中的事。
三化歸一
2002年,楊元慶提出聯(lián)想搞“三化”,即:科技化、服務(wù)化、國際化。楊元慶的三化,核心是轉(zhuǎn)型,把聯(lián)想從制造企業(yè)轉(zhuǎn)型成服務(wù)企業(yè),也就是占據(jù)微笑曲線的兩端——研發(fā)與服務(wù),把利潤越來越低的制造業(yè)務(wù)外包出去。
這其實(shí)是IT乃至家電業(yè)頂級企業(yè)的宿命。IBM出售個(gè)人計(jì)算機(jī)業(yè)務(wù),徹底完成了制造業(yè)向服務(wù)業(yè)的轉(zhuǎn)型。而今天的惠普,實(shí)際上也不是門外漢理解的純粹制造業(yè)企業(yè),它早已不是簡單賣PC和服務(wù)器,而是在賣解決方案了。
今年早些時(shí)候,我了解到,廣州供電局在用惠普的“容災(zāi)/業(yè)務(wù)連續(xù)系統(tǒng)”,這個(gè)方案是個(gè)包括硬件和軟件的一攬子供電管理方案。據(jù)稱,惠普的這個(gè)解決方案,已經(jīng)在全球供電系統(tǒng)中占據(jù)了相當(dāng)高的市場份額。表象是惠普繼續(xù)在PC行業(yè)繼續(xù)纏斗,一個(gè)后臺事實(shí)是,惠普早就在發(fā)展它的新興業(yè)務(wù),走著當(dāng)年IBM走過的路——高智慧、高附加值的服務(wù)業(yè)正在成長,一旦服務(wù)收入占到總營收的50%以上,惠普可能就要考慮出售PC業(yè)務(wù)了。
IT企業(yè)的宿命就是如此,做頂級品牌。最后,必然是把業(yè)務(wù)延伸到微笑曲線的兩端,把中間的制造業(yè)務(wù)外包給代工企業(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