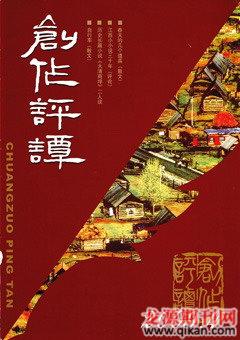越界掘金
1993年“下海”,兩年轉了三家媒體。別人“下海”經商,我“下海”折騰仍跳不出文化圈。不過此圈非彼圈,廣東的文化圈空前浮躁,極少有人潛心靜神搞文學。我未能脫俗,工作之余寫一些憑空捏造的“紀實文學”騙錢。廣東的報刊鬧稿荒,本土作家幾乎不寫作,外地作家又寫不出迎合廣東讀者口味的文章,于是輪到“客家作家”唱大戲。
要說浮躁,香港比廣東更浮躁。香港出版人冷夏計劃出一套“香港名人傳記”叢書,竟找不到一個香港作家愿意操刀。香港不是沒有作家,但像金庸、倪匡、梁羽生、亦舒等會為名不見經傳的出版人冷夏寫書嗎?冷夏何許人呀?說起來挺嚇人的,香港名流出版社社長!其實,在香港想做出版社社長太容易,花幾十港幣注冊一個就是。當時,名流出版社一本書也沒出版過,尚處皮包公司階段。冷夏是土生土長的廣東某媒體記者,找了個在暨南大學讀書的香港女生做老婆,隨妻移居香港。冷夏沒有別的謀生本事,發現注冊出版社那么容易,便弄一個社長大人的頭銜唬人。
香港人嚇唬內地人還真容易。1994年冬我聽說香港出版社社長看中了我,還真有受寵若驚的感覺。這情景,就像當時內地官員聽說來了個香港投資商一樣激動。我什么條件都沒講,就答應寫其中一本《李小龍傳》。冷夏開出的條件是:不拿稿酬寫書稿,由冷夏另署名在香港出版,而大陸版權歸書稿作者。冷夏為何如此摳門,一來他本來就是內地人,摸透了內地作者的心理;二來,他能弄到資料內地作者弄不到(當時去一趟香港,光辦證就得8000元人民幣)。我那時在廣州《現代人報》做一版編輯,當晚班,只能犧牲白天睡覺的時間寫作。三個月后交稿,冷夏評價:是叢書中質量最高的一部。海外版署名“藍潮”出版,大陸版本則是我的名字,于1995年5月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香港的出版業完全市場化,追逐利潤是他們的最高目標。出版商不必對社會、對藝術負責,粗制濫造成為他們的一致行動。香港回歸,帶旺了香港書,幾年功夫,我在香港和大陸出版了一大摞書。當時確實有些小得意:“高產”、“著作等身”、“風行海外”,不簡單啊!尤其是九七回歸前,香港熱達到高潮,《南方日報》曾做過《九七回歸看書市,香港概念牛氣沖天》的整版專題報道,祝春亭“赴港掘金”也成為專版的熱點話題之一。一個江西老表,幾乎寫盡了香港大富豪,寫全了香港百年商戰大事,占天時地利的香港作家和廣東作家沒做到,祝春亭卻做到了!
有熱便有冷。香港概念熱過幾年,到香港回歸后陡然降溫。冷寂下來沉思,我為我的行為汗顏。不采訪,不調研,僅靠出版商提供材料草率成書,我純粹成了出版商賺錢的工具,一個沒有思想的職業槍手。出書太容易,出書也太多,我感到厭倦了。
回顧上世紀80年代,我對文學是多么的虔誠,為她嘔心瀝血,走火入魔。收獲雖少,也沒造成什么影響,但心中有一種固執的崇高感。
我何時能夠回歸文學?
我的這種心態,是大多數“下海”作家的普遍心態。周梅森、熊召政投筆從商后又棄商從文;我的好友劉勇在商海風光了十年,重新拿起筆做職業電視劇編劇。我們這一代作家,不管成大器的,還是小有名氣的,都曾做過宏大的文學夢。
我重拾文學夢,還得從1995年說起。冷夏在籌劃香港名人傳記叢書的同時,還準備做一部全面反映香港百年商戰史的長篇報告文學。冷夏看過我的《李小龍傳》手稿后,決定由我和辛磊共同完成這部書稿。辛磊是廣州人,時任某雜志社總編,他是詩人出身的資深編輯和出版創意人。當初冷夏物色我寫《李小龍傳》,緣于辛磊的極力推薦。
香港原是荒島,香港商戰自然得從1841年香港開埠寫起。我們一頭扎進史料,發現最先來香港發展的英商不是來自英國,而是來自廣州十三行。我們不陌生清朝閉關自守和廣州一口通商,我們卻不知當時全中國的對外貿易全部集中在廣州十三行這個狹小的空間,清政府對外商有那么多歧視性的規定,當時的中國人是那么的狂傲自大!我們立即敏感到,這是一個富礦,有很多鮮為人知的東西有待挖掘,完全值得寫一部題材別開生面的長篇歷史小說!
百萬字的《香港商戰風云錄》趕在回歸前,分別在香港大陸出版。回歸的第二年,香港概念倍受冷落。為了生存,我們一面寫一些商業化的書籍,一面著手收集廣州十三行的資料。那時,十三行遠沒有今天這么熱,除了史學工作者,許多廣州學者對十三行一無所知。研究近代廣州貿易史的資料也非常少,有關行商家族史的資料更是匱乏。資料少可以慢慢地收集,最大的問題是狹隘的歷史觀長期左右史學界對中西關系史的研究!
我們接觸到的歷史教材、史學論著,普遍存在著將西方人妖魔化的傾向:似乎西方人天生就是強盜,他們來中國只能是中國的災難,中國積貧積弱的根源就是西方的殖民侵略和殖民掠奪……照此推理,閉關自守很有必要!
我們動念創作以清史為背景的歷史小說,還受到當時大氣候的影響。歷史小說創作,由80年代前謳歌農民起義領袖,到90年代風向突變,轉為帝王崇拜。以清朝帝王系列為代表的歷史小說,掀起一股為康乾盛世及封建末世涂脂抹粉的熱潮。歷史小說借助電視劇這個大眾傳媒,導致許多人產生錯覺,恨自己生不逢時,倘若生活在大辮子時代該多好!
創作怎樣的歷史小說,首先取決于怎樣的歷史觀。
我們的歷史觀,受以下幾位史學家的影響:
美籍華人歷史學家黃仁宇提出“大歷史觀”概念,他提倡用長時間、遠距離、寬視界來觀察歷史。如若廣州貿易,必須放到有著三千年歷史的朝貢體制的縱向坐標上透視,還必須放到世界近代史的橫向坐標來比較。
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蔣廷黻,1938年出版《中國近代史》綱要。其中一句話尤其經典:“中西的關系是特別的。在鴉片戰爭以前,我們不肯給外國平等待遇;在以后,他們不肯給我們平等待遇。”由于政治的干擾,史學界的許多人直到半個世紀后,才悟出這個道理——在近代對外關系史上,我們也應反省!
法國歷史學家佩雷菲特記述1793年英國特使馬嘎爾尼來華,以向中國老皇帝乾隆祝壽為名,試圖擴大英中兩國交往而被乾隆逐出中國,寫成歷史著作《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以往的歷史書,無不指責英國特使的侵略野心。其實,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越來越意識到馬嘎爾尼的要求大部分是合理的,有積極意義。乾隆斷送了這次中國融入世界的歷史機遇。這部巨著內涵太豐富,令我們最感興趣的有兩點:一是馬嘎爾尼訪華的初衷,是緣于在廣州貿易的英國商人受到不公正、不平等的待遇;二是馬嘎爾尼訪華對中國君臣保守、自大、拒絕外來文明的感悟:“一個民族不進則退,最終它將重新墮落到野蠻和貧困的狀態。”
我們在收集消化史料中漸漸形成這樣的意念:透過乾隆盛世下的廣州貿易,挖掘大國衰落的深層原因。
歷史觀一通百通,我們最為難的還是史料的匱乏——因為寫歷史小說,歷史觀雖然決定作者的價值取向,但是,歷史小說的宏旨仍不是再現歷史,塑造人物形象才是小說的首義。寫一部以十三行為平臺的歷史小說,必須以十三行商人為主角。
我們手頭有一本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再版的《廣東十三行考》(1938年初版),作者是十三行商人后代、中山大學歷史研究室主任梁嘉彬。他所記述的多為嘉慶道光年間的十三行商人,而乾隆年間的行商僅潘振承、黎光華、顏時瑛、倪宏文、張天球、蔡世文等幾位,其中涉及他們生平事跡的文字均很少。
原以為,廣州有不少行商的后代,他們熟悉他們做行商的祖先。調查后發現,行商的后代對他們先輩從事商事知之甚少,甚至完全不知。查閱族譜,潘氏族譜對開山始祖潘振承有關商事的記錄僅寥寥數言,并且連潘振承最為榮耀的職務“十三行總商”都沒有記載!對他的后代,也僅僅是記載他們獲取過什么(科舉)功名,寫過什么著作,而他們繼承祖業繼續在十三行經營則只字未提。十三行后期的總商伍氏家族也是這種情況,族譜只記功名,而忽略商事。然而,在西方的對華通商史,潘振承和伍秉鑒名留史冊,恰恰是他們長期擔任十三行總商,是國際貿易舉足輕重的大人物!曾經出任總商,一口通商時期廣州三大家族之一的盧觀恒,翻遍新會縣(盧氏祖籍)及南海縣(盧氏寄籍)的清代縣志,盧觀恒連名字都沒落下,而盧氏家族有科舉功名者一個不落均有記載。最奇的是,盧氏宗族后人均不知他們的一位祖先曾經是名揚歐洲的茂官(Mowpual)!
士農工商,商人排在最末等。家族并不以先人是名貫中西大商家為榮,而在族譜中抹去他們的經商痕跡。
2002年,瑞典重造沉沒的哥德堡號,準備重走海上絲綢之路訪問廣州。十三行熱赫然升溫,不時有歐美的歷史檔案被翻譯引述。行商的后代無一人保存了先人的畫像,原來先人的畫像在外國人手中,有的是私人收藏,有的藏于博物館。潘振承唯一傳世的畫像為瑞典哥德堡市博物館珍藏,可見當時潘振承與瑞典商人關系之密切。這些國外珍藏的資料,彌補了國內資料的許多空白,比如船牌,清宮檔案有記載,但無實物。又如潘振承被罰十二萬兩銀子的哆羅教案,國外原始資料的敘述與國內奏章諭旨的描述很不一樣。
蘇格拉底說:我們知道的越多,就越不知道。
我們收集研讀的資料越多,越感到資料的殘缺。潘振承是我們確定的貫穿全書的核心人物,他生平的空白點太多了!就說他的婚姻吧,他先后娶了七個妾,族譜只有周氏李氏劉氏譚氏麥氏許氏馮氏,這都是些怎樣的女人,一字未記。又如,中國外貿史的驚天大案——英商洪任輝案,十三行商人尤其是總商深涉其間。就我們目前接觸到的中外資料,涉及行商的內容僅僅是概述,沒有細節。
啊,別忘了我們是寫歷史小說,而不是做史學考證。即使是歷史小說,也都是虛構文學。虛構和想象猶如一只大鳥,可以自由翱翔,但仍不可以無限度地飛高飛遠,仍有一定的飛行軌跡。換言之,歷史小說的虛構,仍必須以符合歷史的真實性的基礎,受作者歷史觀的制約。
歷史小說創作應大處著眼,小處著手;胸中要有“大歷史”,落筆則要貼近“小歷史”。“大歷史”體現出來的是歷史規律,“小歷史”則是一連串人物事件,猶如長河中的浪花、森林的落葉。小說家專注的應是浪花和落葉,一滴水可見太陽,一葉落知天下秋。
經過多年資料的收集和研讀,我們開始投入寫作。由于當時歷史劇風靡銀屏,我們停止歷史小說的寫作改寫歷史劇,2003年夏我們完成電視劇本初稿,劇本版權被廣東南方電視臺收購。殊不知后來廣電總局下了個限播歷史劇的禁令,歷史劇立即陷入滅頂之災,拍好的播不出,籌拍的立即下馬。我們的《大清商埠》電視劇不幸夭折。
同名歷史小說的寫作在電視劇本殺青后便開始,這不是當今書市風行的電視小說(電視劇熱播,把電視劇本稍加一些修飾便冠以小說出版),而是常規意義的歷史小說。我們的觀念是新的,手法卻是傳統的,參照章回體文本進行創作,有意加強小說的故事性。因為百多萬字的小說,觀念再新,若沒有引人入勝的情節,相信不會有人愿讀。
我從2000年結束職業寫手生涯,回到停薪留職的原單位江西教育學院上班,在中文系從事寫作教學。這門課我上了20多年,無須多費腦筋,我的心事全部傾注于小說寫作(辛磊的主要精力在電視劇本)。在寫作過程中,不斷有廣東作家競寫十三行題材的消息傳來。
這些在廣東生活比我更長久的作家,通過十三行這個公開的、萬人矚目的題材發現了什么?
為避免得罪同仁,我隱去具體的作家作品。有個家庭恩怨劇,之所以說它是十三行題材,是因為劇名冠以“十三行”,劇情發生在十三行富商家庭,恩恩愛愛,家長里短。一部準備聘請國內大牌明星出演的電影,表現鴉片戰爭前后十三行商人的眾生相,以此弘揚愛國主義和民族精神。一部長篇歷史劇,走的是港臺劇的路子,中國和外國的男男女女,打打鬧鬧。還有一部小說的提綱,把西方人看成妖魔鬼怪,而忽視他們是代表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富有擴張野心的人群……
十三行是一座人人皆知、品類品相極其龐雜的礦藏,誰挖掘出品質優良的礦脈?讀者比作者更有發言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