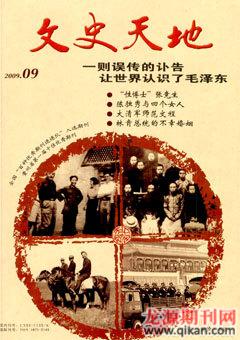韓愈:一代文豪真性情
岑燮鈞
本文在調侃之中,也讓我們見識了一位有血有肉的韓愈。
有一個人喜歡探險,與朋友一起攀登華山最高峰。真所謂“上山容易下山難”,上去之后,覺得無法下來,于是就寫遺書,發狂痛哭。要不是華陰縣令聞訊趕來,多方設法,還真要呆在山上飛升了。
這個人不是別人,乃是——韓愈。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韓愈是一個儒家的衛道士。蘇軾說他“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越發讓人敬而遠之。但是,如果我們走近他,你會發現,他還是一個挺逗的人。他并不古板,跟我們一樣,也愛發牢騷,也常說些酸不拉幾的話。與文學青年在一起時,好為人師,如果你去討教,他肯定熱心得不得了。有時候,也喜歡拉幫結派,交結天下才學之士,而且毫不在乎人家的身份地位。只有一樣,可能與你我不一樣,那就是他蔑視官場潛規則,有時敢冒風險說真話,說鬼話,說“不正確”的話。
且說有一天,賈島騎在驢上,正為他的那句“鳥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傷腦筋,到底是用“敲”好呢還是用“推”好,他不斷地用手勢模擬現場,不知不覺沖進了一個大官的隊伍中。于是,騎兵侍衛就把他推了下來,扭送到大官面前。大官是一個很嚴厲的人,就要處分他。賈島趕緊說明緣由,請求原諒。那大官聽了,早把處分忘記了,還一同幫他“推敲”,沉吟了良久,說,我看還是用“敲”好。說完,就邀請他一起并馬而行,談詩論文,一起走進了市府大院——原來賈島碰到的就是長安市市長韓愈韓大人。
韓愈這個人,雖然大大小小也算是當了一輩子官,可是對待有才學的人,還是蠻“親民”的。李賀拿了詩卷去謁見韓愈。韓愈當時在東都洛陽做國子監博士——國立大學的教授,正好送客歸來,人非常困倦。這時,學生呈上李賀的詩卷,他一邊寬衣解帶,一邊讀詩。當韓愈讀到“黑云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時,立即整頓衣冠,命人邀請李賀進來相見。可見,時人只要有才學,求見韓愈并不難。豈止不難,他還要為你揚名助威呢。有一年牛僧孺去拜訪他和皇甫浞,請求品評。那意思不言而喻,初到京城,想請大人物幫他立足。兩人很是理解他,也因為看重他的才學,竟然故意在他不在時去看望他,借機在他的門上題字:“韓愈、皇甫浞同訪僧孺先輩,未遇。”消息一傳開,牛僧孺立即身價百倍。對韓愈他們來說,也許只是文人的風雅;但成人之美如此,不能不說是有非凡的度量。
年輕人尊著韓愈,韓愈自然樂意做個宗師。但是,人家把你當作孟嘗君,吃著你,喝著你,但并不“寵”著你,還要與你開涮,那么,你能承受多少呢?有個叫劉叉的人,素來喜歡行俠重義,不肯伺候貴人顏色。他也找到了韓愈的門下,與韓門學士們爭論高下,從不肯讓步。臨走時,拿著韓愈的數斤金子,對韓愈說:“這是你‘諛墓所得,不如送給我吧。”韓愈無話可說,也只能任他拿走。韓愈文章寫得好,這是事實。為此,許多人請韓愈寫墓志銘一類的文字。韓愈也不推辭,蓋棺論定時,盡量說人家的好話,以博得一筆可觀的稿費。這也算得是韓愈的業余收入吧。可是,好話批發得太多了,也敗壞行情。今番被劉叉揶揄了一頓,大概韓愈也只能苦笑了吧。
韓愈在有些事上,并不像人想像的那般方正。本質上,他是個文人,免不了意氣用事。有一年,他跟隨宰相裴度去平定淮西的叛亂,凱旋回朝后,皇上命寫《平淮西碑》。大概是為了報答裴度對他的知遇之恩,他用了很大的篇幅敘述裴度的事跡;而實際上,當時是李想生擒叛賊,功勞最大。為此,他對韓愈憤憤不平。這事終于傳到皇上那里,皇上下令磨去韓愈所寫碑文,請翰林學士重寫,這讓韓愈很沒面子。其實,這樣的事,也不是第一次了。他有時激于義憤,來不及調查清楚,就輕率地上奏折。結果因為偏聽偏信,發錯言而被貶官。可是,他并沒有汲取教訓,依然是一副“快嘴”,我行我素。有時,還很執拗。比如李紳彈劾他不參謁中臣,韓愈說這是皇上恩準的。本來,也就是一點小事,如果話稍許說得和緩一些,也許就過去了。可是,互相頂牛,誰也不讓著誰,結果,惹得皇帝很煩,就把他們都給打發了。書生的臭脾氣,在他的仕途生涯中,幾度壞事——壞事就壞事唄,脾氣還得照發。被貶了,就大喊大叫,給這個失意人說,“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給那個落第人出主意道,“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皮里陽秋,曲里拐彎,總覺得“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一副懷才不遇的樣子。還記得嗎,十九歲那年,他來京城趕考,競連考三年不中。二十八歲那年,他曾連續三次上書宰相,請求人仕——是不是很可笑呢,哪能自己要求做官的呢?
活得率性,這是古人比我們精彩的地方。我們做官的,若是降了職,就很少再聽到這個人的消息了。他自己都覺得抬不起頭,又怎會喋喋不休為自己申訴呢?但在韓愈,看得稀松,有上有下是常態,才不屑夾著尾巴做人呢。我們常說,吃一塹,長一智,可韓愈就是不長記性。十六年前,他任監察御史。關中大旱,饑荒嚴重,他上書要求減賦稅,救災民,罷官市,結果觸怒權貴,被趕出京城,貶為連州陽山令。而這一次,他竟然要“教訓”皇帝了。皇上派人去迎法門寺佛塔中的佛指舍利,準備人宮供奉三天,然后再到各寺廟供奉,以掀起一股敬佛熱潮。可是,韓愈以為萬萬不可,就慷慨激昂地上了一道《論佛骨表》。他說,佛不過是外國的東西,他沒傳人中國之前,中國的君王都長命百歲;自從漢明帝時傳人中土,此后的皇帝都短命而死,就是有長壽的,也不得善終。你是至高無上的皇帝,就是佛活著來朝見你,你也只須在宣政殿客氣地見一見,賜給他一襲袈裟,然后護送出境就可以了;何況,現在佛已死了很久,只剩下一截“枯朽之骨”,又怎好迎入宮門呢?我們是政教分離的國家,孔子說“敬鬼神而遠之”,這就是我們的指導原則。應當把佛骨“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后代之惑”。如果佛真有靈,一切罪過,我來承擔,絕不后悔。韓愈態度鮮明,擲地有聲。可是,如此激烈的言辭,終于激怒了皇帝。于是,皇帝要處死韓愈。幸虧得到裴度等大臣的營救,最終被貶為潮州刺史。皇上后來說:“我知道韓愈上《論佛骨書》是出于愛護我;可是,身為人臣,不該說我奉佛就會短壽。因此,我就討厭他太輕率了。”但在韓愈,“欲為圣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他認為不對的,就是有危險,也是“雖千萬人吾往矣”!
這就是“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的韓愈。他到了潮州,并沒有倆犧惶惶,不可終日。因為他覺得自己應該這樣,一股“浩然之氣”支撐著他。當時,潮州鱷魚成患,他還挺逗,命令屬下把豬羊作祭禮投入水中,寫了一篇《祭鱷魚文》,義正詞嚴,警告鱷魚:我是奉天子之命,來此守土安民的,鱷魚你怎么可以與我雜處一地,爭搶領導權呢?你現在乖乖地聽我好言相勸,潮州南面,就是大海,你可以朝發而夕至。我與你約定,三天之內,你帶著你的同類,滾到南海去。三天來不及,就五天;五天還不能夠,我就放寬到七天。如果七天你還不走,那就是存心與我為難。到時,可就別怪我不客氣。我挾天子之威,一定殺了你,你可不要后悔喲!沒想到,禱告的當晚,暴風雷霆自潭中而起,幾天后,潭水干枯。鱷魚竟真的走了——邪不壓正,其此之謂歟?
韓愈曾在一首贊美“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的詩中,想像自己追隨李杜,能夠上天人地,“剌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盡情揮灑自己的才情。而撥開歷史的迷霧,我們見到的韓愈,確實并沒有我們想像的那般正襟危坐,而是真真實實地鮮活生猛地揮灑在一個偉大時代的尾巴里。
(作者單位:浙江省慈溪市逍林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