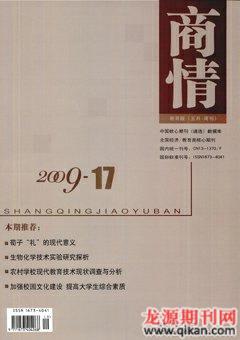荀子“禮”的現代意義
李偉弟
【摘 要】“禮”是荀子思想的核心要素,荀子通過對“禮”的重新建構,賦予了其道德與法律的兩項屬性。“禮”的作用體現在它對人性欲望的控制和提供政權合法性基礎等方面,顯示出與法律的內在共通性,本文旨在在這種共通性的基礎上分析荀子“禮”的現代意義。
【關鍵詞】荀子 禮法 制度
我們考察荀子的禮治思想,會發現“禮”是完善人格并實現社會化的內在道德要求,同時也是外在的一整套制度化工具。荀子建構“禮”的一個重要目標是將禮放置在中國傳統法的概念之上,顯現出道德化的法律傾向,其規范價值也在于此。這種“禮”的思想所蘊藉的現代性需要我們做進一步的分析。
一、荀子“禮”產生的背景
英國著名的劍橋學派強調“情境主義”,即通過對思想家寫作的歷史情境、意識形態背景、語言背景等客觀環境的挖掘,從中理解思想家的真實意蘊。因此對于荀子“禮”的認識仍可以通過這一路徑進行探討。荀子身處于戰國后期,國家之間戰爭頻繁,各國統治面臨巨大的社會沖擊,整個社會處在分裂邁向統一的狀態。社會轉型時期往往是思想迸發最激烈之時,同時也是秩序混亂、道德失范最極端的時期。荀子的做法即是在對孔子一脈的傳統儒家進行繼承的基礎上,結合現實情景加以改造。
荀子的深刻之處就體現在他的理論構建是以人性欲望為基礎的,他認為:“禮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心不窮乎物,物必不屈于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荀子?禮論》)。“禮”產生于個體對物質的需求而產生矛盾需要用禮來加以規范,使欲與物之間的這種需求和供給達到一種平衡。荀子在“禮”中注入了這種濃厚的人性化色彩,個人的欲望在這里明確的受到了規范和限制,把人的需要納入到了整個社會的穩定軌道上來——這即是“禮”建立的必要和現實基礎。通過對荀子“禮“思想的分析,他所要構建的直接產物——禮法制度就產生了。本文的目的在于揭示荀子的“禮”的現代意義,而對于其思想產生的背景進行分析也是為了做一種符合“厚”的理論的分析。
二、荀子“禮”的現代啟示
1.荀子“禮”的思想對于現代社會制度構建的啟示
我們通過比較分析發現,荀子“禮”在道德倫理和刑罰律令上設置了一整套完整的制度,涉及物與欲,政治、經濟與倫理等多角度多層次,從而形成了一個全面宏大的社會制度。而制度性的缺失正是中國始終無法擺脫“人情社會”的原因之一,荀子的全面制度化設計無疑是遵循改革此項弊端的思路進行的。中國社會的制度缺失,增加了權力徇私甚至權力尋租的概率,貪腐行為金額日益增大,涉案人員的級別越來越高。如何建立合理有序的社會規范,有效地防止腐敗行為,荀子的思想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可能的途徑,我們既要有形而上的社會主義理念,同時也要落實形而下的責任意識、權力意識,更重要的是在個人意識與社會理念之后設計一套合理的程序制度作為外在保障。社會核心理念的操作要有人來完成,人性的疏漏不可避免,即使是在一個有著高度文明的社會里,人民的道德理念并不會必然先進。
2.荀子“禮”的思想對于中國法治建設的啟示
現代社會人們往往出于對“人治”的天然恐懼而排斥倫理道德在法治建設中的作用。這種思想既是對中國傳統人治社會弊端的認知,也是對西方“法律概念沒有絲毫的道德含義”觀念的繼承。但是我們需要明確,無論是從法律的產生上還是在法律發展的過程中,倫理道德都是無法絕對排除的。正如博登海默所言:“至于一個法律是否能夠完全不使用含有道德含義的廣義概念,如誠信、犯意(犯罪意圖)和違背良心的行為等概念,也是頗令人懷疑的。”而哈貝馬斯認為在康德那里我們可以繼承這樣一種理念:“實在法服從道德法,而道德法引導實在法。”荀子的“禮”由于有了“法”的輔助而具備了道德屬性和法律屬性。這恰恰與現代中國所提倡的“依法治國”、“以德治國”形成了某種對應。我們可以看到在荀子這里,二者恰恰由于工具理性而都成為保證國家有序進行的手段,荀子之“禮”為道德與法律建立某種平衡、融合提供了可能,遵循荀子的路徑,對于擺脫中國法律的濃濃人情與西方法律移植中國之后面臨的水土不服等局面都有積極地意義。在荀子的觀點看來,“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是兩個層面的東西,德治在于人的自我內心,同時它也是法治建立依存的理念框架。法治在于外在制度,但同時它也是人的道德意識中不可逾越的一部分。因此中國的法治建設必須要處理好與道德的關系,統一于社會主義建設當中。
3.荀子“禮”的思想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啟示
荀子“禮”對人性的關照,對“義”的高舉,為傳統“義”與“利”的緊張關系做出了協調。從中西傳統價值思想比較中發現:“西方價值觀在價值取向上的重要特征是重利輕義”,無論是理性主義價值觀,還是功利主義價值觀都是立足于個人本位、求取個人利益。但近代以來,西方亞當斯密、休謨等人的經濟思想為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協調提供了思想基礎。西方工具理性的轉向,由“義”及“利”的轉向似乎都說明了中國傳統倫理中“取利舍義”思想向現代“義利共存”發展的可能,“義”與“利”的路徑之間不存在絕然的阻塞。荀子“義利兩有”、“以義制利”的禮治思想為打通這兩者之間的堵塞已然提供了中國化的解決辦法。“法”與“禮”的融合不僅僅為“義利兩有”提供了倫理指導,更重要的是為“義”與“利”的分配關系做出了制度上的保障。今天中國所面臨著貧富分化所代表的社會公義的缺失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私利”盛行的道德問題。荀子之“禮”既是對個人能力與社會資源分配做出了對應的制度化管理,同時“其禮、法制度從德性要求與制度規范上對人們的經濟行為和經濟活動進行倫理價值導向與法律規范,力圖做到符合儒家價值理念的起點公平與過程公正,使各類經濟活動的成本安排盡可能的合理高效,并真正實現人類難以‘近盡的物質欲望與自然、社會資源‘相持而長”為我們解決上述道德困境與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社會利益分配提供了解決之道,從而使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備了立足現代同時注重傳統的理論資源。
參考文獻:
[1]阮青.價值哲學[M].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