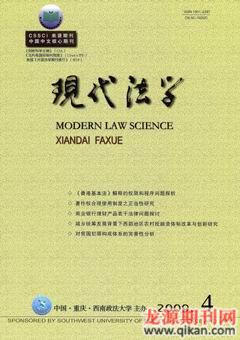論任意雇傭原則在美國勞動法中的衰落
胡立峰
摘 要:從19世紀末開始,美國普通法上形成的任意雇傭原則授予雇主任意解雇員工的權力而不要求其承擔任何法律責任,對勞動者權利保護甚為不利。考慮到絕對任意雇傭原則所帶來的種種消極影響,在許多方面已經不適應現代勞資關系的發展,美國立法機關和各州法院已經形成該原則的多項普通法例外,任意雇傭原則逐步走向衰落。由于任意雇傭原則在美國社會長期實行,擁有深厚的社會基礎,動用立法權和司法權等國家權力也并非以廢止該原則為目標,因此迄今為止其仍然是調整美國雇傭關系的重要規則。
關鍵詞: 任意雇傭原則;普通法例外;美國勞動法;衰落
中圖分類號:DF472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09.04.08
從19世紀末開始,美國在解釋不定期雇傭合同時所采取的默認規則(default rule)就是任意雇傭。任意雇傭作為雇傭關系的基本形式,內在地包含了任意解雇的方面,即除非雇主和員工雙方之間另有協議,否則任何一方都能夠在任何時候解除雇傭關系而無需承擔法律責任。該規則使雇主獲得了不受限制的經濟武器,其導致的最重要法律后果是:被任意解雇的員工不能起訴其雇主不當解雇。晚近以來,隨著任意雇傭原則的弊端日益凸顯,美國立法機關和各州法院為減小該原則受到雇主濫用內在可能性,采取了一些緩和該原則嚴格性的舉措,絕對的任意雇傭原則已經遭到實質性削弱。這意味著,傳統的任意雇傭原則為適應現代勞資關系的發展正逐漸做出讓步,也由此開始了其逐漸走向衰落的歷程。筆者在本文中嘗試從傳統任意雇傭原則衰落這一視角,透視美國雇傭關系發展的基本脈絡,引發人們對新形勢下美國勞工權利保護問題的思考,為促進我國解雇保護制度的完善提供域外法制的參照。
一、美國勞動法上的任意雇傭原則
任意雇傭原則又稱雇傭自由原則,是美國普通法上一項雇傭關系的基本準則。在歷史上,美國普通法的發展與英國有著深厚的淵源,深受英國相關制度的影響,在私人性質的雇傭關系上也不例外。早在殖民地時期,美國就開始沿用英國制度,私人性質雇傭關系被認為是一種主仆關系。(注:在英國,早期所謂私人雇傭合同關系一向是指一種家庭中主仆關系(master-servant relationships)而言,具有極為強烈的封建制度的社會地位(status)或階級(class)意味,雇主通常負有保護受雇者的義務,而受雇者則需負忠誠服務的責任。關于該點,可參見Joseph DeGiuseppe, The Effect of the Employment-At-Will Rule on Employee Rights to Job Security and Fringe Benefits, FORD. URB. L. J., Vol. 10, 1981, pp. 3-4.)18世紀后期,美國引入英國《雇傭法》有關規定:只要沒有相反的證據,沒有明確規定期限的雇傭關系均被推定為1年。到了19世紀后期,由于法院之間對于沒有明確期限的雇傭關系在雇傭期限和通知要求方面存在分歧該法律處于混亂狀態[1]。針對這種情況,1877年,Horace Gay Wood在他撰寫的關于主仆關系的論文中提出了任意雇傭原則,但沒有對該原則進行正當性方面的分析[2]。隨后,在一段不長的時間里,Wood關于任意雇傭的思想很快影響了全美的工作場所。起初,任意雇傭原則是為了保護企業經營自由而設計出來的,雖然它對員工造成不利影響,但在19世紀最后25年里仍然逐漸得到美國多數司法機構的采納。如今,除了蒙大拿州之外,美國其余各州都通過立法對該原則加以確認。
“像許多其他類型的合同一樣,雇傭合同經常是不完備的(incomplete),存在重要條款遺漏或約定不明的問題。法院已經創設出各種規則用于填補這些空缺。這些規則之一就是任意雇傭原則,在雇傭合同當事人未明確約定合同期間的時候,它就成為調整雇傭關系的默認規則。”[3]根據任意雇傭原則訂立的雇傭合同,被解雇員工沒有針對雇主的索賠權,不論解雇的具體理由為何;同樣,雇主也不能起訴辭職的員工,因為根據任意雇傭原則他們擁有隨時辭職的權利。
在早期,任意雇傭原則的適用僅限于從事非體力勞動的雇員,后來實際上擴展覆蓋至各種類型的工人。這一規則后來被濫用的典型,是雇主享有了絕對自由的解雇權:無論被解雇員工人數多少、解雇理由充足與否甚至違反道德要求時,解雇行為也是絕對自由和合法的。任意雇傭原則被尊奉到最極端程度的一個表現是,連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也對之深信不疑,甚至認為雇主任意解雇權是一項理應受到美國憲法保護的權利。(注:關于這一點,可以參見美國早期的兩個著名判例Adair v. United States, 208 U.S. 161 (1908); Coppage v. State of Kansas, 236 U.S. 1 (1915).)根據任意雇傭原則,法院或者立法機關均不應干涉勞資雙方對雇傭條件協商確定的結果,而應由相關當事人基于契約自由原則以自己的意思來處理相互關系。該原則顯然是以勞資關系雙方當事人談判能力彼此均等為前提條件的,除非存在例外情形,員工就解雇對其雇主并不具有法律上認定的訴因或索賠原因[4]。因此,基于合同法或侵權法原理,多數對員工的解雇是不可訴的。但是,任意雇傭原則在一般情況下可以排除對政府雇員和受集體談判協議保護的雇員這兩大群體的適用[5],因為這兩大群體不可能受到普通法上任意雇傭原則的影響。(注:在大多數西方國家,公共部門的雇員享有穩定的工作保障,法律對解雇設置了具體限制,明確規定要有“正當理由”才能解雇雇員。而在私營部門,工作保護的規定卻相對較少,美國勞動力市場在這一點上表現得尤為突出。參見J. Addison, Job Secur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Law, Collective Bargaining, Policy, and Practice,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Vol.24, 1996, pp.381~418.而集體談判協議對受集體談判協議保護的員工而言,等于勞資雙方對解雇事宜另行作出的專門約定和安排,工會憑借其參與集體談判的機會,大多已經在集體談判協議中設置了約束雇主任意解雇權的條款,入會員工由此而受到保護。)
根據任意雇傭原則,雇主可以自由地解雇員工而不受到任何來自于法律方面的約束;因此,在大多數的司法判決中,雇主在解雇員工時,不承擔商業合同所要求的誠實信用和公平交易的責任。雇主在作出解雇的決定時,也不承擔其根據侵權法通常所本應承擔的對員工的合理照顧義務。可以說,片面追求契約自治和財產權保護的任意雇傭原則是以犧牲員工利益為代價而發展起來的偏袒雇主利益的勞資關系準則。
任意雇傭原則的實施促進了自由放任、經濟個人主義和契約自由等理念的盛行[6],這些理念都認為雇主擁有控制其企業的權利,員工也擁有與其雇主自由協商的權利。基于這些理念,任意雇傭原則推定雇主和員工都可以通過締結合同來保護他們自己,認為任何對勞資關系的管制都等于干預雙方當事人的契約自由。截至20世紀,任意雇傭原則在美國一直受到人們的普遍推崇。它的出現契合了19世紀末的美國經濟不斷發展的需求,通過授予雇主任意終止雇傭關系的自由,促進了當時稀缺的勞動力在各種職業或行業之間的迅速流動,同時也有利于雇主通過削減雇傭員工的工資成本,靈活應對社會經濟風險,保持和提高自身的競爭力。
雖然任意雇傭原則是美國法上處理解雇爭議案件的基本準則,但是,基于該原則的實施過分偏袒雇主的利益,沒有為占社會成員絕對比例的普通勞動者提供有效的保護,因此引發了后者的強烈反對。特別是立法機關和法院考慮到在勞資關系中,員工通常根本無法擁有與雇主相匹敵的談判能力而不得不接受雇主所提出的條件接受雇傭,趨向于主張應對雇主的權力加以限制,于是逐漸開始對不當解雇行為進行法律干預。由此,雇主原本不受拘束的解雇權受到了控制,傳統任意雇傭原則出現了衰落的跡象。
二、任意雇傭原則衰落的主要表現
(一)成文法對任意雇傭原則的限制
1.聯邦層面立法
在美國,勞資之間最激烈、最殘酷的斗爭,至今約有100多年的歷史。在這期間,美國資本主義經歷了由高速發展到經濟蕭條、動蕩不定、劇烈變動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現代勞動關系才逐步形成和發展[7]。現代勞動關系的發展,對傳統雇傭關系規則形成了有力沖擊。“近幾十年來,任意雇傭原則已經遭到聯邦制定法的重大削弱,這些制定法禁止對那些擁有某個受保護團體成員資格的員工加以歧視,或者禁止對那些參與某些受保護活動的員工進行報復。”[8]在聯邦層面上,美國國會作為立法機關針對任意雇傭原則制定了大量保護勞動者免受不當解雇的法律法規。
1935年美國國會頒布的《國家勞資關系法》(又稱《瓦格納法》,National Industrial Relation Act,Wagner Act)確立了解雇保護制度,規定雇員不因參加合法組織或從事產業行動而被解雇。“對那些參加或支持工會的雇員,雇主最早采用的報復形式就是黑名單——任何雇主都不會雇傭一個眾所周知的工會支持者”[9],但是《國家勞資關系法》明確規定雇主的上述行為屬于不公平勞動行為而觸犯法律。《國家勞資關系法》是美國在1935年至1947年間聯邦政府處理勞資關系的基本法。該法的出臺,與1929年發生的世界范圍內的經濟危機關系密切。此次經濟危機后,美國政府為恢復經濟和穩定社會,必須要限制雇主對工會和勞動者的不合理的壓制和干涉,以避免由于雇主在勞資關系中的過度專權而引起勞資對抗和社會不穩定[10]。《國家勞資關系法》將雇主采用解雇等辦法以禁止員工加入任何勞動組織的行為和對依法作證或提出指控的員工予以解雇的行為視為違法行為,雇主在雇傭期間不得以上述理由解雇員工,否則即屬不當解雇。
繼《國家勞資關系法》之后,美國國會于1938年通過的《公平勞動標準法》規定禁止解雇那些對最低工資、加班時間提出抗議的工人。從1950年代開始,美國又相繼頒布了類似法律,保護那些對工作安全表示異議的工人,以及對污染環境進行投訴的工人。隨著1964年《公民權利法案》的頒布,美國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法律、法規,對私營部門的各類雇員提供了有限的解雇保護。這些保護性立法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雇主任意解雇員工的狀況,但并沒有為大多數勞動者的工作保障提供足夠的法律支持。
2.州層面立法
蒙大拿州是美國第一個也是迄今為止惟一一個明確表示拒絕適用任意雇傭原則,并對不當解雇進行綜合性立法的州[11]。其1987年制定的《蒙大拿州不當解雇保護法》(Montanas Wrongful Discharge from Employment Act of 1987, WDEA)是美國第一部在州的層面上制定的不當解雇保護專門立法。
《蒙大拿州不當解雇保護法》擴大了員工個人對解雇提出質疑的權利,提供了正當理由解雇標準并優先提供普通法救濟。根據該法案,只有在下列情況下解雇才是不正當的:(1)出于對員工拒絕違反公共政策或揭發違反公共政策行為的報復;(2)解雇并非基于正當理由并且員工已經結束了雇主的雇傭試用期;(3)雇主違反其書面人事政策中的明示規定。根據該法,勞動者有權獲得的損害賠償限于自解雇之日起不超過4年的工資收入和利息以及其他有關收益。如果雇主違反公共政策而解雇員工,或者雇主解雇行為存在事實上的欺詐或惡意,則員工可以獲得懲罰性賠償;但是,不能獲得因精神痛苦、情緒沮喪引起的精神性損害賠償及其他補償性損害賠償。(注:MONT. CODE ANN. § 39-2-904 (2005).)該法律同時規定,在員工將案件提交法院之前,必須先在企業內部詳盡闡述其請求。雇主和員工也可以協商通過仲裁解決這類糾紛,但根據該法案仲裁解決不是強制性的。
《蒙大拿州不當解雇保護法》的適用在蒙大拿州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它是“美國迄今為止簡化解雇法的最成功的嘗試”。(注:美國全國統一州法委員會(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f Commissioners on Uniform State Laws)考慮到各州制定法和普通法原則適用中的混亂局面,不利于保護勞動者的權益,試圖創設一種合理的和統一的解決方案,實現解雇法的簡化。蒙大拿州的解雇保護立法是美國全國統一州法委員會上述意圖的成功嘗試。)然而,其他各州尚未追隨蒙大拿州的先例制定各自的解雇保護法。因此,多數雇主仍然處于嚴格限制雇主自由解雇權的解雇法所創設的復雜而成本高昂的體制中。同時,許多員工還沒有獲得不當解雇保護。” [12]
(二)Petermann案以來各州司法實務對任意雇傭原則的沖擊
司法過程對任意雇傭原則的限制主要是在州法院的層面上發展起來的。在早期,任意雇傭原則適用的絕對性和嚴格性,排除了對其進行司法干預的可能性,導致勞動者針對各類解雇提起的訴訟均被法院駁回,對任意雇傭原則的司法審查難以進行。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在美國,絕大部分州法院已經通過個案發展出各種侵權法或合同法方面的例外,試圖減小該原則受到雇主濫的內在可能性。”[13]起初,絕對的任意雇傭原則是作為普通法上的原則得到各州法院廣泛采納的。如今,法院又不得不對其最初做法進行修正,通過發展普通法例外的途徑矯正該原則的弊端。
比較美國各州的司法實務,加利福尼亞州率先就任意雇傭原則作出重大修正,從而領導其他各州的判例。1959年,加利福尼亞州上訴法院在著名的Petermann v. International Brotherhood of Teamsters案(注:Petermann v. Intl Bhd. of Teamsters, 344 P.2d 25 (Cal. 1959).)中,首次明確宣稱雇主的解雇權應當受到制定法或公共政策考慮的限制。在該案中,某企業員工因為拒絕為其雇主在州議會調查聽證會中作偽證,雇主就以其工作表現不佳為由將其解雇。原告聲稱該解雇乃是雇主對其拒絕作偽證的報復。法院根據傳統任意雇傭原則,雖然承認不定期雇傭合同在一般情況下可以由雇主任意解除,但認為如果解雇理由是違法或違反公共政策時,仍為法律所不許可。反對作偽證的公共政策所體現的公共利益對雇主的絕對解雇權造成限制,原告進而擁有了一項普通法上針對不當解雇的訴因(cause of action),并因此有權利獲得救濟。本案判決以公共政策和公共利益為視角進行考量,正式確立了任意雇用原則的公共政策例外,形成了供其他各州法院效法的范例。
Petermann案作為美國司法實務中最早發展出任意雇傭原則普通法例外的案例,其“意義不在于雇主不能解雇那些拒絕作偽證的員工,……而是第一次為員工提供了解雇方面的訴因。繼Petermann案之后,批評者們開始要求對任意雇傭原則進一步進行變革。” [5] 1061自19世紀70年代起,美國各州法院開始認真地對任意雇傭原則作出修正,到1980年代中期之前,已經在理論上發展3種不同的修正方法:公共政策例外、默示合同例外以及公平誠信原則例外。
第一,公共政策例外(public policy exceptions)。自1959年加利福尼亞州上訴法院在Petermann案中發展出任意雇傭原則的公共政策例外之后,該例外在美國得到了司法實務的普遍承認,各州法院以公共利益和社會福祉為考量,對雇主違反公共政策的解雇行為作出限制,為遭受違反公共政策不當解雇的員工提供侵權法上的訴因。“目前,為員工提供違反公共政策方面侵權法訴因的公共政策例外,正不斷地侵蝕著任意雇傭原則。雖然法院強調任意雇傭原則仍然存在和有效,但近期許多判決集中地展現了力圖擴張公共政策例外范圍的態度。”[14]這種擴張對雇主任意解雇員工的基礎造成了公共政策方面的限制。
公共政策例外的實施雖旨在保護員工免受雇主侵害,但公共政策目標卻是首要的考慮因素。就美國各州司法實務對公共政策例外的適用情況,違反公共政策的不當解雇可以區分為以下4種情形:1.因拒絕從事違反刑法規定或其他違法行為遭到解雇;2.因行使一項制定法上權利或特權而遭到解雇;3.因遵守一項制定法或憲法上的義務而遭到解雇;4.因雇主違反一般性公共政策而遭到解雇。
第二,默示性合同例外(implied contract exceptions)。任意雇傭原則僅承認一般雇傭關系中,雇主是以給付工資,受雇者以提供勞務為最主要的約因。至于受雇者繼續就業的利益,只不過是一項期待利益,在法律上并無執行的可能性。因此,受雇者必須在正式就職前與雇主進行談判,并以書面簽署雇傭合同的方式確定雇傭關系的存續期間。美國各州法院為了保障受雇者不被任意解雇,希望在當事人的雇傭關系中,設法找出某些因素證明雇主愿意受合同拘束,只有在不滿意受雇者的工作表現,或另有正當理由的情況下,才能將受雇者解雇。由此形成了任意雇傭原則的默示性合同例外。
美國法上任意雇傭原則的默示性合同例外主要適用于下列情形:1.受雇者的任職期間極長,并且受雇者在任職期間定期得到雇主的褒獎和晉升,很少被批評工作不力,也沒有出現違反企業規章制度的情況,由此即可推定勞資雙方有默示性合同關系存在;2.受雇者在應聘工作時或者在雇傭期間內雇主明確表示將會繼續對其長久任用;3.雇主在員工手冊(employment manual)或其他有關人事政策(personnel policies)的文件中,明確強調受雇者的職位具有相當的永久性或穩定性;4.在雇主的員工手冊等文件中,明確規定有實施懲戒及申訴的程序,因而推定雇主有受默示性合同約束的意思表示;5.從雇主所從事的一般性行業慣例(general practices),或雇主在過去所一貫采納的政策或做法(past policies or practices)中,判斷雇主除有正當理由外,不任意解雇受雇者的證據。
第三,公平誠信原則例外(covenant of good faith and fair dealing)。勞資雙方成立的雇傭關系中,雙方形成了默示性契約關系,雇主不得基于惡意任意解雇其員工。美國法院以違反公平誠信原則為理由,對雇主依據任意雇傭原則任意解雇員工的權力加以限制,形成了任意雇傭原則的公平誠信原則例外。公平誠信原則最早起源于保險合同。(注:在保險合同關系中,由于締約雙方當事人的談判能力和財務狀況都極不平等,因此,法院往往認定保險公司應以公平誠信原則對待被保險人。)它要求當事人必須以公平誠信原則對待對方,特別強調合同當事人一方不得剝奪他人所獲得的合同上的利益。在私人雇傭關系的情形,除了加入工會組織的員工可以通過集體力量與雇主相周旋抗衡外,一般受雇者與被保險人的情況極為類似,因此也應當以同樣的公平誠信原則來加以規范。
公平誠信原則例外是最晚形成的任意雇傭原則普通法例外,而且與任意雇傭原則相距最大,因此僅有少數州法院采用這一例外[15] 。對公平誠信原則例外,美國各州法院的判例可以區分為下列主要類型:1.受雇者長期任職而積累的相當程度的延期性利益(deferred benefits),但雇主為了規避給付義務而在應當支付相關金額之前解雇了員工。受雇者長期任職而積累的延期性利益主要包括其退休養老金(pensions)或者為雇主推銷商品而理應獲得的相當數額傭金(commissions)等。2.雇主基于一般惡意(malice and bad faith)或報復(retaliation)的目的,將受雇者解雇。3.基于各種相關因素的綜合考慮,雇主解雇員工違反公平誠信原則。
三、任意雇傭原則衰落的主要原因(一)現代雇傭關系發生了巨大變化
與19世紀任意雇傭原則剛出現的時候相比,現代的雇傭關系已經截然不同:
第一,雇傭勞動成為勞動的主要形式。在現代工業尚未發達的早期,人們可以通過從事農業勞動和家庭手工業勞動進行生產,勞動所需要的生產資料比較容易獲得,因此,勞動者具備自我雇傭的條件。今天,由于機器大生產和市場變動導致的經濟風險加大和生產經營成本的增加,勞動者自我雇傭的機會已經大為減少。各種類型的企業得到發展,為勞動者提供了從事雇傭勞動的機會。在勞動者與雇主建立雇傭關系時,勞動者被納入雇主的企業組織和勞動過程,置于被管理受約束的境地。這種狀況表明勞動者與雇主之間已經出現某種地位差別,并進而影響到雙方的利益。 第二,勞資雙方談判地位失衡。由于勞資雙方占有資源數量的不同,雇主在雇傭關系中居于主導地位,除了雇主非常渴求的專門人才外,大部分的員工難以擁有與雇主平等的談判能力。如果雇主憑借其資源優勢,利用勞動者急于就業的心理,勞動者試圖在雇傭合同中限制解雇權濫用的條款就難以達成。缺乏合同約束的雇主在行使解雇權時往往會超越合理限度,在企業仍然盈利、勞動者表現尚好的情況下,為減少成本而不惜使員工持續工作的期待落空。同時,現代社會工作的重要性加劇了員工談判能力缺乏的嚴重性。工作對勞動者而言非常重要,它提供了獲得生活必需品的經濟收入,塑造了員工的個人志向及其家庭的信念,同時也確立了個人的社會地位和身份。工作對勞動者如此重要,雇主如果任意解雇員工,將不但導致員工經濟利益受到侵害,也將損害其精神利益甚至危及家庭關系。
雇傭關系的上述變化,表明任意雇傭原則已經置于完全不同于早期的社會背景之下。為了使任意雇傭原則適應變化了的雇傭關系的要求,必須對其進行必要的修正。
(二)美國社會工會低潮的出現
工會低潮的出現,一方面將使得工會組織喪失對勞動者的影響力,導致勞動者入會率降低,受集體談判協議保護的員工的覆蓋面下降,另一方面資方將可能利用工會低潮的時機,以其強勢談判地位為要挾,千方百計降低員工解雇保護的水準;因此,在工會運動出現低潮的情況下,勞資力量嚴重失衡,容易出現資方控制勞方的局面。這為國家公權力積極介入勞資關系事宜提供了正當性,有助于遏制雇主勢力的過分膨脹。
任意雇用原則在美國的衰落有著工會方面的背景。1970年代,美國發生嚴重經濟危機,對工人利益造成巨大影響。除經濟危機外,從1940年代開始到1970年代美國又卷入越南戰爭,導致社會經濟發展受到嚴重挫傷。同時,由于各行各業生產不景氣,美國政府開始大幅度削減社會福利費用,使得集體合同所規定的工資福利無法兌現,大部分工人工資不斷下降,以至影響了工人參加工會的積極性[7] 317;因此,1980年代以來,美國工會組織出現了普遍低潮的局面。隨著美國工會組織的加速衰退,使得過去那種更多依靠集體談判對解雇進行保護的法律體系已經改變,司法過程中法官對任意雇傭原則例外的承認促使更多的員工為保護權益提起不當解雇訴訟[16]。
(三)維護和發展公共利益的需要
在現代社會中,政府以公共利益為目標對經濟和社會進行廣泛的干預,通過制定和實施公共政策來矯正社會問題,彌補市場缺陷,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以公共政策干預雇主不當解雇行為,是公共政策矯正社會問題功能的反映。從公共政策視角來看,解雇不僅涉及微觀層面上雇主和勞動者之間的利益紛爭,還具有社會層面的意義。在社會長期奉行任意雇傭原則的背景下,不當解雇問題導致勞資關系緊張和社會矛盾加劇,已經成為影響公共利益維護和發展的重大問題。公共政策正是在這一基礎上介入不當解雇問題的解決的。
絕對的任意雇傭原則是與普遍的公共利益要求相矛盾的。 “任意雇傭原則的適用所造成的問題遠大于雇主濫用控制勞動者的權力,還包括對被不當解雇勞動者的社會和經濟影響。”[17]現代社會出于維護和發展公共利益的基本需要,逐漸對基于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傳統雇傭領域進行修正,并將其導入公共政策實施機制的軌道,使之符合公共利益的普遍要求。美國各州法院考慮到美國雇傭關系不斷變化的本質以及不當解雇案件中的遭解雇員工的權利經常受到不當侵害的事實,在判決中出現了不斷吸收公共政策原則的趨勢。在雇傭關系的調整過程中引入公共政策因素,旨在實現雇主有效經營企業的利益、員工謀生的利益、確保公共政策得以實施的社會利益三者之間的某種平衡。
(四)誠實信用原則的強化
誠實信用原則是具有彈性的概念,其內容不確定,有待于就特定案件予以具體化,實體法通過該原則與外界的社會變遷、價值判斷及道德觀念相聯系,實現與社會發展的與時俱進[18]。市場經濟活動本質上是利己的,而道德本質上是利他的。誠實信用原則恰恰是道德在調整市場經濟中的法律反映。[19]
在美國,“趨于所有合同中都隱含誠實信用和公平交易約定的偉大運動,導致了在諸多案例中,法院皆出于日益發育的‘社會啟迪而廢棄長久確立起來的法律。”[20]誠信原則對任意雇傭這一普通法先例構成了沖擊。在雇傭關系中,雇主和員工都需要遵循誠實信用的道德要求。誠實信用原則對雇主的基本要求之一是,不得濫用解雇權力損害勞動者的既得利益,導致勞動者喪失工作保障。根據誠實信用原則,當勞資雙方成立雇傭關系后,雙方便形成一種道德上的約束,雙方應當誠信履約,做到公平對待對方。雇主違反誠實信用原則的典型表現是雇主為降低經營開支而任意解雇員工的機會主義行為。誠實信用原則強調雇主行為時應考慮員工一方利益和需要的滿足,不得濫用其在雇傭關系中的優勢地位。為了限制雇主任意解雇員工的機會主義傾向,在適當場合排除任意雇傭原則的適用,成為保證雇主經營行為遵循誠實信用原則的舉措。
(五)理論界對任意雇傭原則的批判
美國學者們對任意雇傭原則的批判集中于下列方面:
第一,任意雇傭原則的濫用將導致雇主機會主義,對員工利益造成損害。雇主對工作有效率員工的解雇,如果沒有合理的理由,就屬于不當解雇。休?柯林斯(Hugh Collins)認為,至少在兩種情形下,理性的雇主可能會解雇有效率員工。這兩種情形都包括雇主方面的機會主義,即雇主為了在短期內節約生產經營成本而忽視諸如維護企業良好聲譽等長期目標[21]。首先,當員工被控告存在不端行為時,有學者指出雇主應調查指控以確定員工是否是有效率的并因此決定是否留用他,但是調查會導致雇主立即付出明顯的成本,而留用有效率員工的利益卻將要等到較長時間才會顯露出來;因此,雇主很可能為應付緊急情況不經調查就逕行解雇員工。第二種雇主可能解雇有效率工人的情形,發生在雇主已經采用了經濟學家們有時稱之為“遲延效益”支付方案的場合。一個簡單的例子是,銷售員只有等到與客戶的交易完成后才能獲得傭金,雇主在該銷售員有權獲得傭金之前將其解雇,這樣就能夠節省一筆費用。由此可見,雇主出于成本意識,具有通過解雇有效率員工而實施機會主義解雇行為的動機。通過限制任意雇傭原則的濫用,可以防范雇主機會主義解雇的傾向。
第二,任意雇傭原則的濫用也會對雇主利益造成損害。有學者指出,如果員工感到他們的工作保障不安全,就會以企業對他們的最低要求應付工作并且隨時準備抓住各種機會逃避工作任務。可以預見的是,員工只有在一個高度信任的環境中才會作出最佳反應。如果他們感到雇主信賴他們,他們就會把工作做得很好,通過痛改前非、辛勤工作和盡力為公司服務來回報這份信任。雇主通過賦予員工自主決定的權利而非不斷對其行為進行監督檢查,通過避免使員工感到他們經常處于解雇危險之下,就能夠創造一個高度信任的工作環境。從這一角度看,對解雇權進行一些法律控制有利于提高工人的忠誠度和工作效率,最終也能夠給雇主帶來好處[22]。如果不分場合地濫用任意雇傭原則,勢必導致相反的結果,最終給雇主利益帶來損害。
第三,批評者們還指出,任意雇傭原則以過時的經濟個人主義和契約自由為前提,已經落后于時代的要求,進而認為“對契約自由的標榜不能導致市場交易與最低公平要求、理性行為和重要政策的連貫性相隔絕。” [22] 1826勞倫斯?E?布雷茨(Lawrence E. Blades)一針見血地指出,“對自由的最大威脅不是來自政府管制,而是來自那些試圖通過其市場力量對員工職業生涯控制能力構成威脅的雇主。”[23]克萊德?W?薩默斯(Clyde W. Summers)強調指出,要想對員工提供更多的法律保護,必須尋求解雇保護方面立法的完善;因為任意雇傭原則是法院最早通過判例法創設的,遵循先例的傳統使得法院立場僵化,表現出不愿改變它們自己創設的法律原則的態度[24]。他認為,任意雇傭原則作為過時的規則,對于美國社會的高效有序運轉既不必要也不合適,應當加以廢除。
上述觀點對任意雇傭原則的批判,深刻影響了美國雇員解雇法的發展。受富有改革思想的批評者們的激勵,美國法院最終發展出了控制雇主任意解雇原則的上述眾多普通法例外。
四、對任意雇傭原則衰落的法理評析
任意雇傭制度在美國雇傭法上已有悠久的歷史,然而其正走向衰落也是不爭的事實,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任意雇傭原則以契約自由為基礎,該原則的衰落體現了契約自由理念的衰微和雇傭關系以當事人身份、地位為基礎的本質。任意雇傭原則作為美國雇傭法的核心,它的衰落給美國雇傭關系發展帶來了深刻影響。
(一)從契約到身份:雇傭合同對契約自由的背離
現代社會中,契約是構建不同主體間法律關系的重要工具。在現代社會形成的許多種契約關系中,當事人雙方可能是由特殊人格群體組成的對比非常鮮明而相互地位又相對確定的一對,如雇傭合同關系(勞動關系)等。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任由當事人確定彼此的權利義務關系,勢必會導致不公平結果的出現。現代契約理論主張根據當事人在契約關系中的不同地位來要求他們分別承擔相應的義務,“與只注重抽象規范的古典契約法相比,現代契約法更注重當事人在整個契約活動過程中的具體地位如何,單純的個人意志面對錯綜復雜的具體的社會關系,已不再保有對契約關系的絕對的支配力,契約中的‘身份似乎更能左右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25]
在各種契約關系中,當事人實際地位的差別取決于其對資源控制程度和規模的不同。以雇傭關系論,雇主和員工之間存在明顯的利益失衡問題。雇主占有大量的生產資料并通過使用勞動力而控制勞動者,而勞動者只能獲得通過出賣其僅有的勞動力獲得的些許勞動報酬;因此,雇主在資源的控制程度和規模上具有優勢地位。在企業經營過程中,雇主解雇一名員工比這名員工找到新工作要容易得多。“在那些恣意妄為的雇主手里,任意雇傭原則已經變成恐嚇的法律工具,給勞動者的生活和家庭造成嚴重損害。”[17]642在任意雇傭原則的規范下,雇主一般可免受法律的限制,根據其需要和利益來塑造其與勞動者之間的雇傭關系。有時候雇主在經營過程中解雇部分員工,不會對其經營企業造成根本性影響;而對勞動者而言,解雇讓他們付出的是巨大的代價,失業成為他們職業生涯中最難以面對的窘境之一。不但勞動者的經濟收入、社會地位和精神狀態因此受到影響,勞動者家庭關系也因此受到沖擊,有關家庭成員的利益也會遭受損害。在現實生活中,員工大都是出于雇主方面的不正當理由被解雇的,這表明工薪階層需要某種最低限度的保護。如果沒有更加靈活的途徑對待任意雇傭原則,他們將別無選擇,只能成為“其雇主每個要求的溫順追隨者(docile follower)”。[23]1405面對資強勞弱的局面,任意雇傭原則不僅不對之作出有利于勞動者的調整,卻反其道而行,放任乃至強化了這種利益失衡格局的畸形發展。
(二)任意雇用原則對美國雇傭關系的影響
1.從“任意解雇”到“不當解雇”
在19世紀,任意雇傭原則剛剛形成的時候,美國正處在現代工業資本制度的誕生時期。這一時期是工業資本原始積累的階段,作為雇主的資本家需要通過掃除來自社會各方面的障礙謀求工業迅速發展,以獲取高額利潤。任意雇傭原則契合了資本家的這一需要,受到他們的普遍推崇;因此,可以說,19世紀早期新興工業的發展需要構成了美國歷史上承認任意雇用原則的正當理由。而在如今美國工業早已發展成熟的背景下,繼續沿用任意雇傭原則已經喪失了經濟發展的正當性基礎。
對任意雇傭原則導致的解雇自由的看法,過去學說上認為工作權的保障僅止于國家與國民的關系,并未直接規范各個私人企業與國民的關系,因此對于雇主擁有的解雇自由,不應予以限制。目前學說則認為,工作權并非僅止于失業狀態時請求國家提供就業機會的權利,同時也是一種適用于私人間法律關系的權利,因而可限制雇主的解雇自由,因此應當在勞動法中對雇主的解雇自由作具體、列舉的限定性制約[26]。
在嚴格適用任意雇傭原則的背景下,雇主所進行的任何解雇都是合法的并因而是正當的;因而,在早期,美國社會不存在“不當解雇”的說法。只是后來美國立法機關和法院在修正任意雇傭原則絕對性的過程中,才形成了“不當解雇”的觀念,并通過各種普通法上的例外,對構成不當解雇的具體情形加以明確。多年來,美國司法過程中積累的判例大都確認在下列3種情形下,雇員不能任意地受到解雇:(1)雇主的解雇行為違背公共政策,如因雇員拒絕從事違法活動或揭發雇主違法行為而被解雇;(2)雇主的人事政策、管理流程、口頭承諾明示或隱含了續訂雇傭合同的承諾的;(3)違反合同所遵循的誠實信用和公平合理原則,如雇主故意剝奪合同中約定的雇員的權益、獎金或津貼等等 [16]133。基于上述幾種情況而進行的解雇,屬于美國法上的不當解雇。“不當解雇”概念的出現,意味著雇主的意愿已經不是決定某項雇傭關系存續與否的最終因素,解雇行為必須接受法律的價值評價和專門調整,雇主擁有絕對解雇權的情形已經成為歷史。
2.解雇保護的實質化
“當企業的經營自由和解雇不受限制的自由結合起來后,勞動者即陷于一種生存權不受保障的境地”[26]37,為此需要為他們提供解雇方面的保護。解雇保護要求雇主解雇勞動者的權利(力)受到國家強制性法律的制約,必須在必要范圍內基于正當事由而得以行使,否則雇主應當對其解雇行為承擔法律責任。根據解雇保護對契約自由原則的修正程度,解雇保護理論可以分為“限制解雇權濫用理論”和“正當事由理論”。
在普通法上,關于“不當解雇”的理解最初只是程序意義上的,法律對雇主的惟一要求在于其是否給予了員工確定的通知期;而在因員工行為導致的即時解雇(summary dismissal)中,連通知都是不必要的了;因此,雇主解雇行為的正當與否,普通法關心的只是雇主是否遵守了解雇的通知程序,至于解雇的理由何在以及對錯與否,法院均拒絕作出任何裁決。這使得在勞資關系中處于弱者地位的雇員在普通法中處于十分被動的境地。“這種對解雇權的程序控制屬于限制解雇權濫用的范疇。
限制解雇權濫用并不對任意雇傭原則構成有力限制,持該理論者“基本上仍肯定解雇自由權,但以濫用之禁止作為對解雇自由權的一種抑制。” [27]相比之下,正當事由理論走的更遠,它“對解雇自由權做了很大的抑制”,是對民法契約自由原則的“根本修正”,具有從根源上抑制不當解雇的效果,因此得到普遍認可。“以正當事由作為解雇權內在的制約,必須法有明文,始得行使解雇權,違法解雇則無效。”[27] 157美國通常被描述為一個缺乏綜合性不當解雇立法的工業化國家。現行的《公民權利法案》只籠統規定了某些特殊群體有權抵御某些類型的解雇,而沒有對整個勞動者群體的權利做出規定。正當事由理論以法律對解雇事由的明確規定為條件,以正當事由理論制約任意解雇,要求美國加快解雇保護立法和促進現有相關立法的完備。
迄今為止,“任意雇傭原則在美國的發展已經達一百三十多年,其作為美國雇傭法上默認規則的地位仍然沒有根本改變”[28], “即使司法例外和制定法的修正已經削弱了普遍存在的任意雇傭原則,它仍然是一項雇傭關系的主導性推定。”[29]基于任意雇傭原則長期推行所積累的深厚社會基礎,試圖通過立法權和司法權在短期內消除其影響是極為困難的。普通法例外的適用雖然對任意雇傭制度產生了一定沖擊,但暫時無法改變兩者之間制度能量的巨大差異,任意雇傭原則在走向衰落的同時仍然具有廣泛和深遠的影響力。ML
參考文獻:
[1] 楊燕綏.勞動法新論[M].北京: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4:187.
[2] J. Peter Shapiro and James F. Tune, Implied Contract Rights to Job Security, 26 STAN. L. REV. 335 (1974).
[3] Andrew P. Morriss, Exploding Myths: An Empirical and Economic Reassessment of the Rise of Employment At-Will, 59 Mo. L. Rev.680 (1994).
[4] J. Wilson Parker, At-Will Employment and the Common Law: A Modest Proposal to De-Marginalize Employment Law, 81 Iowa L. Rev. 347-350 (1995).
[5] Andrew P. Morriss and Stephen M. Stigler, Developing a Framework for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Common Law: General Principles and Case Studies of the Decline of Employment-at-Will, 45 Case W. Res. 1072-1073 (1995).
[6] John P. Frantz, Market Ordering Versus Statutory Control of Termination Decisions: A Case for the Inefficiency of Just Cause Dismissal Requirements, 20 Harv. J.L. & Pub. Poly 556-557 (1997).
[7] 王益英.外國勞動法和社會保障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286-287.
[8] John Devlin, Reconsidering the Louisiana Doctrine of Employment At Will: On the Misinterpretation of Article 2747 and the Civilian Cause for Requiring “Good Faith” in Termination of Employment, 69 Tul. L. Rev. 1517 (1995).
[9] 道格拉斯?L?萊斯利.勞動法概要[M].張強,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61.
[10] 常凱.勞權論[M].北京: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4:339.
[11] Sandra S. Park, Working Towards Freedom from Abuse: Recognizing a “Public Policy” Exception to Employment-At-Will for Domestic Violence Victims, 59 N.Y.U. Ann. Surv. Am. L. 129 (2003).
[12] Lindsay B. Jackson, A Lesson from Germany on How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Reform Its Laws on Dismissal, 4 Geo. J.L. & Pub. Poly 538 (2006).
[13] Jackson Peck, Unjust Discharges from Employment: A Necessary Change in the Law, 40 OHIO ST. L.J. 1 (1979).
[14] Melanie R. Galberry, Employers Beware: South Carolinas Public Policy Exception to the At-Will Employment Doctrine is Likely to Keep Expanding, 5 S.C. L. Rev. 406 (2000).
[15] Alan B. Krueger, The Evolution of Unjust-Dismissal Legis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44 Ind. & Lab. Rel. Rev., 649 (1991).
[16] 程延園.英美解雇制度比較分析[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3,(2):133.
[17] Madelyn C. Squire, The Prima Facie Tort Doctrine and a Social Justice Theory: Are they a Response to the Employment At-Will Rule?, 51 U. Pitt. L. Rev. 642 (1990).
[18] 王澤鑒.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一)[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303.
[19] 陳年冰.試論合同法中的誠實信用原則[J].法律科學,2003,(6):63.
[20]P.S.阿蒂亞,[美]R.S.薩默斯.英美法中的形式與實質——法律推理、法律理論和法律制度的比較研究[M].金敏,等,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112.
[21] Hugh Collins. Justice in Dismissal, Clarendon Press, 1992, p.110.
[22] Note, Protecting At Will Employees Against Wrongful Discharge: The Duty to Terminate in Good Faith, 93 HARV. L. REV. 1816 (1980).
[23] Lawrence E. Blades, Employment at Will vs. Individual Freedom: On Limiting the Abusive Exercise of Employer Power, 67 COLUM. L. REV.1404 (1967).
[24] Clyde W. Summers, Unjust Dismissal: Time for a Statue, in Alan F. Westin & Stephan Salisbury (eds.), Individual Rights in the Corporation: A Reader on Employee Rights, Pantheon Books, 1980, p.56.
[25] 董保華.從歷史與邏輯的視角透視社會法的體系[A].何勤華.華政法律評論(2002年第1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84.
[26] 尤素芬.關廠規范之理論依據探析[J].勞工研究,1994,(10):37.
[27] 黃越欽.勞動法新論[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156-157.
[28] Stephen L. Hayford and Michael J. Ever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Employment-At-Will Doctrine and Employer-Employee Agreements to Arbitrate Statutory Fair Employment Practices Claims: Difficult Choices for At-Will Employers,73N.C. L. Rev. 443 (1995).
[29] Susan R. Dana, South Dakota Employment At Will Doctrine: Twenty Years of Judicial Erosion, 49 S.C. L. Rev. 47 (2003).
Decline of At瞁ill Employment in American Labor Law
HU Li瞗eng
(School of Law,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Abstract:
In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at瞱ill employment became a doctrine in American common law, which entitled employers to fire an employee arbitrarily without bearing any liability and consequently had an adverse effect on protection of employees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view of its negative influences on modern labor relations, the US legislatures and state courts have made lots of exceptions and the doctrine is declining. However, because of its profound social foundation, the doctrine cannot be abandoned immediately by way of resorting to legislative or judicial power. So as of it is still an important principle in the USA to regulate employment relations.
Key Words:at瞱ill employment doctrine; common law exception; American labor law; decline
本文責任編輯:盧代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