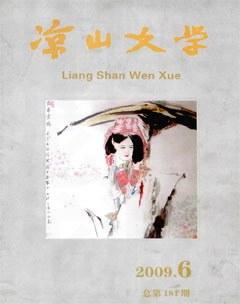在彝家的沃土上徜徉
何萬敏
一
“在中華民族的大家庭中,彝族是歷史悠久、文化燦爛的古老民族之一。四川省是中國最大的彝族聚居區,現有220余萬彝族人口。新中國成立前,世居于四川境內的彝族,由于所處的特殊地理環境,復雜的社會歷史形態,以及獨特的民族風俗習慣等因素,主要聚居在涼山、樂山、攀枝花、雅安、甘孜、宜賓、瀘州等市州,而居住在四川省境內其他各市縣的彝族,分布則較為分散,以雜居為主。早在8000多年前,四川世居彝族的先民就在成都平原、金沙江沿岸、大渡河畔、安寧河谷和大小涼山繁衍生息,并創造了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四川境內居住的彝族不斷與其他民族融合,并逐步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可分割的民族關系、血緣關系、親情關系以及獨具特色的四川世居彝族文化。”曲木車和在他的新著《四川世居彝族文化》開篇的第一章概論中,開宗明義確定其著的整個基調,“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彝族文化與中原文化、巴蜀文化和南詔文化以及其他少數民族文化不斷交流、融合,多元的文化背景孕育并形成了今天悠久燦爛、豐富多彩的彝族歷史文化”。而“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待和研究彝族的歷史,對于全面研究四川世居彝族,更好地認識和了解其發展,更進一步地認識其構成和民族間的關系,對增進各民族的團結,消除隔閡,促進各民族的共同繁榮發展和構建和諧社會有著重要的意義。”
我們知道,文化是一個復雜的概念。不同的文化學家對文化各有不同的闡釋,有人還做過統計,說世界上的文化定義有數百種之多。撇開各種學派、各種角度的解釋,僅就文化的外延來說,大致就有廣義、中義、狹義三類界定:廣義的界定包羅萬象,舉凡人類的一切創造、一切活動都是文化。狹義的文化偏重指向人的精神文化,甚至偏重直指訴諸書面文字的知識和精神娛樂活動。在上述二者之間,則根據不同的需要與理解,既不那么廣泛也非那么狹隘,譬如有的學者關注人的生活樣式和生活態度,有的學者關注制度習俗與行為模式,有的學者看重技術創造與發明或者獲取生活資料的手段與方式等等。從全書內容可以看出,作者所理解的文化及文化出發點,從形式看是包含物質與精神創造,從實質看則是對人們有某種支配意義的、并且為人們所認同的行為、觀念、模式、符號等。
這就是我們常常說到的——文化,是一個民族的標志。
“民族文化既然是一個民族的標志,是一個民族與其他民族相區別的特征,那么它的性質首先無疑就是它的獨特性。無論是有形文化、行為文化、精神文化,還是語言符號,此一民族必然有異于彼一民族。特別是那些外顯的方面,獨特性更為顯著一些。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式樣獨特的建筑、服飾,也有自己的風俗習慣,婚喪禮儀,年節慶典,有自己的語言文字、價值取向,還有整體而言的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等等。”因此,通過《四川世居彝族文化》一書,我們既可以了解四川世居彝族文化的生產、節日、服飾、食俗、建筑、婚俗、生育、喪葬,欣賞他們所創造的獨特的語言文字和文學藝術,更可以一見四川世居彝族文化中充滿神秘色彩的占卜、禁忌等宗教活動和習慣法,從而把握四川世居彝族的源流、民族構成及形成原因,以“家支”為紐帶保持的家族體系,以及四川世居彝族人口的發展情況。可以說,本書對于研究彝族、特別是四川世居彝族的文明起源、社會運行機制、生產生活方式、信仰支配下的儀式等諸多方面,具有相當的史料價值、理論價值和文化價值。即使在已經出版的許多有關彝學的專門論著中,《四川世居彝族文化》也顯得富有獨到見解而別開生面。
二
身為涼山彝族,曲木車和自幼生長在世居彝族聚集的一個“德古”家庭。他從小就在父母身邊接受有關彝族的述源釋源、傳統習俗等知識的教育,跟隨父親與前輩德古們依據彝族習慣法協調各種矛盾糾紛,并親歷判案、斷案的全過程。參加工作后,長期從事民族工作,特別是擔任四川省民委副主任后,經常與許多彝族學者一道共同探討和研究彝族文化,同時還從民族學的宏闊領域比較各民族文化的特質與殊同。這樣就使得他在描述彝族文化的時候占有“先機”并同時站有高度。正如法國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所說:“人類學家自己是人類的一分子,可是他想從一個非常高遠的觀點去研究和評斷人類,那個觀點必須高遠到使他可以忽視一個個別社會、個別文明的特殊情境的程度。他生活與工作的情境,使他不得不遠離自己的社群一段又一段長久的時間;由于曾經經歷過如此全面性、如此突然的環境改變,使他染上一種長久不愈的無根性;最后,他沒有辦法在任何地方覺得適得其所;置身家鄉,他在心理上已成為殘廢。人類學像數學或音樂一樣,是極少數真正的召喚之一。人可以在自己身上發現到這種召喚,即使是從來沒有人教過他。”從這種意義上來說,民族學家和人類學家一樣,都是天生的旅人,是漂泊的行者,人在書齋,心在異域,或者人在異域,心懷世界。我知道作者生活在成都這樣的大城市已經多年,因此猜測《四川世居彝族文化》本來就是家鄉的某種“召喚”的回應,表明了作者的一種文化抱負,那就是民族學家即使是在遠離家鄉之后,仍然在尋找家鄉,當他在領享不同文化的滋養后,反而更加容易以跨越不同的文化的姿態,更加重視對于本民族的文化梳理與觀照,其意圖在于尋找人類相互交流、相互認識以及“和而不同”地相處的知識基礎。
畢竟是在尋找家鄉的途中乃至回到彝鄉的土地上,作者幾乎不用田野調查、卻是用親身經歷的田野調查方法,為讀者徐徐展開一幅四川世居彝族生活的歷史圖景和現實畫面。譬如對彝族人生產、節日、服飾、食俗、建筑、婚俗、生育、喪葬等生活細節的描寫,譬如對彝族重要的史詩《勒俄特依》、《瑪牧特依》和敘事詩《阿嫫尼惹》的完整翻譯,包括對147條類似漢語格言警句的彝族爾比爾吉的收集整理,對幾十首彝族民間歌曲(山歌、情歌、酒歌、悲歌、哭嫁歌、婚禮賽歌)的收集整理,從一個民族的心靈出發,去觸摸和感知民族深層的情感和理智,從自己的感受去體會研究對象行為和思想在其生活上的意義。
還有“信仰”和“習慣法”兩章,盡管篇幅不長,卻如祖宗崇拜地位重要一般,勾勒出彝族的精神活動的重要部分。彝族文化研究的先行者劉堯漢認為,彝族畢摩、蘇尼的祈神驅鬼除了具有為病患者精神治理的功能外,“彝巫的神判在維持舊社會秩序方面也有一定的作用。對此,最重要的則是習慣法。”并進而分析,“由于涼山彝族是父系氏族制和氏族奴隸制,雖有文字,尚無成文法。凡是土地、婚姻、盜竊、毆斗、兇殺等等民、刑事件,均南通曉世代相傳的習慣法者黑彝和白彝來調解各種糾紛。在世界法律史上,古巴比倫的《漢謨拉比法典》、古印度的《摩奴法典》、中國春秋時鄭人的《刑書》,都是階級社會的成文法。涼山彝族舊社會則是遵循其傳統的習慣法,由于它存在于奴隸社會,其中一部分是為奴隸主服務的;
對于占人口75%以上的廣大白彝群眾有利的原始習慣法,在世界法律史上則罕見;這就是涼山彝族習慣法的法學史價值之所在。”曲木車和對此的認識同樣言簡意賅:“四川彝族習慣法與其他民族的習慣法一樣,是人類社會在發展過程中,在一定區域內,為了協調、處理民族內部或民族之間的相互關系,規范人們的行為而制定的大多數社會成員共同認可并共同遵守,適用于這一區域的行為規范。”在作者眼里,一切文化要素一定都是在活動著,發生作用,而且是有效的制約著四川彝族地區人民的行為規范。他認為“家支”是以父系血緣為紐帶而自然形成的社會集團或家族聯合體,一個巨大的、部落間的關系網,在一個廣泛的地區上把許多人以確定的社會形式聯系起來。在這個網里,人們受到確定的關系和互惠責任的約束,共同遵守非常微觀的規則和禮俗;而有著與“家支”相關的、高度發達的神話和巫術儀式,它在部族人的傳統中有著深厚的根源和綿長的歷史,并使得彝族文化源遠流長直至今日。
三
多年前,我曾經被孫隆基先生一本《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專著所深深吸引。他從一個嶄新的角度看中國文化,在一個文化的表面層次上,自然是有變動的,而且變動往往是常態。“深層結構”是指一個文化不曾變動的層次,它是相對“表層結構”而言的。“我們設定:每一個文化都有它獨特的一組文化行為,它們總是以一種只有該文化特有的脈絡相互關聯著——這個脈絡關系就是這組文化行為的‘結構。這個‘結構可以在該文化中人們日常生活的表現里看到,也可以在同一群人的政治行為中找到,同時,它亦呈現在該文化的歷史過程里浮現的規律性中。”順著這條路徑,我們可以明確,人類雖然是自然界中的一分子,然而人類的發展由于借助了文化的動力而遠遠超越了自然屬性,人類所創造的文化代表了其社會屬性、社群關系的高度發達。那么,對于每一個民族來說,文化不僅僅意味著他們的一種基本的生存方式,而且也是維系一個民族存在并繁衍生息的不可缺少的群體要素。“文化的深層結構中保留著一個民族所共同認同的東西,它可以起到對一個民族的凝聚作用。而這個凝聚作用是文化在其中發生影響的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說,民族的存在也就是一種文化的存在。民族的存在是依靠文化來維系的,文化使每個民族獲得了一種立足于自然界生存的依附,在這種依附中,人們發現了屬于他們自己的生存世界。這樣,被特定文化所維系的民族這一禮會構成要素,也就具有了一種從內在到外在滿足人的對整個自然界生存需要的屬性。人們在關于本族的文化觀念中,最終找到了與自然相處的方式。對外部世界的改造與調適,正代表了民族文化的這一特殊功能。”曲木車和盡管沒有在書中就此展開討論,但我依然能夠從《四川世居彝族文化》中觸摸到這樣清晰的文化脈絡。
如果說人生是一個謎,其實文化更是一個難解的謎。面對眾聲喧嘩的文化議題,文化的面目顯得愈加龐雜,延伸波及到那些專門研究文化的領域并造成勉為其難的窘迫。“在任何精確的程度上界定文化研究都是極其困難的。”柯林·斯巴克斯早在1977年發表的《文化研究的評價》中就坦率地道出界定文化研究的困難乃至不可能,“給文化研究畫一條清晰的線索或說我們從一個側面發現文化研究的適當領域是不可能的,指出足以標志文化研究之特征的整齊劃一的理論或方法也是不可能的。由來自文學批評、社會學、歷史、媒介研究等的觀念、方法和關切組成的地地道道的大雜燴,都在文化研究的方便的標簽下面雜陳在一起。”但是,這并不妨礙文化學者對各種各樣文化的研究,就像我們一方面認為“美”是不可定義的,另一方面卻又在不斷地給“美”下定義。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在現代性的多重建構或多元性中,文化始終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層面,甚至不少思想家在解析現代性的矛盾體或矛盾邏輯時,把文化現代性作為基本矛盾的一方面加以考慮。“在某種意義上看,現代性的矛盾就是文化現代性與社會現代化之間的抵牾沖突。”
顯然,在一個更加廣闊的文化圖景下,民族文化的現代轉型或者說時代變遷順理成章。當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條件發生快速變化的時候,作為民族標志的文化也在發生著發展與變化。“民族文化的現代轉型是由文化變遷的發展趨勢所決定的……文化轉型是文化系統的一種自我調整過程,文化在變遷中不僅要考慮如何保存舊有的傳統,還要考慮如何進一步去創造新有的文化傳統,以更好地去適應現代社會乃至未來社會的需要。”似乎,也正是在這個時候,包括彝學在內的中華民族各學派的學術研究更加活躍更加扎實。就在我生長的四川涼山,在數個名目大同小異的彝學組織帶動下,相關的學術著作出版呈明顯的增長之勢;同時,一些外國學者也加入到彝學研究的行列中,極大地拓展了學術研究的視野和方法。當文化在融合與統一、分離與隔絕的交織中綿延,我們欣喜看到中華文化復興大業中民族文化的一次次維護、確認和前行,《四川世居彝族文化》和此前的眾多彝學著述一樣,其影響和意義將隨著時光的推移愈加凸顯出來。因為,“彝族知識分子把他們投身于其中的學術事業描述為‘讓世界了解彝族文化”,在美國的學者郝瑞看來,“彝學研究的宗旨是為了向那些關注彝族的人們(尤其是向彝族人自己)證明,彝族文化是一種值得引以為自豪的文化。彝族文化中有許多東西具有精致、高度發展的特點,彝族文化足以昂首挺胸地面對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