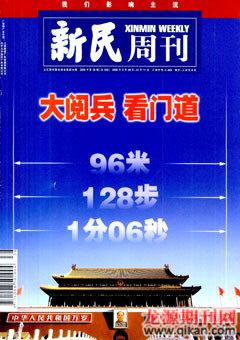危險的歌詩達
應 琛
國際上,除了對海盜行為及公海販毒有明確的“普遍管轄權”的法律解釋外。對于其他違法行為并無專門的法律法規弗約束。人們不禁要問,公海是否成了違法者的“犯罪天堂”了呢?
有一種危險堪稱奇特:當你乘坐郵輪在公海上航行,環顧四周,藍天碧海,心情松弛,這時,毫無防范意識、也不能與外界保持通訊的旅客,很可能面臨偷盜者、搶劫者甚至是殺人者的肆意而為,甚至被隨手拋入大海,死無對證。一旦在公海上受到類似的侵犯,甚至法律也束手無策,因為狡猾的犯罪分子鉆到了司法空白的空子。
8月底,各大媒體爭相報道的、發生于“歌詩達”郵輪上的失竊事件,給人們敲響了這樣的警鐘——郵輪度假涉及中國公民團隊旅行、偷盜案件發生于公海、船只由第三國管轄,這一新興的“案件模式”在我國存在司法空白。
據報道,郵輪在上海靠岸后,上海水上公安部門雖在第一時間竭力協助處理,但遺憾的是,受害方仍被告知,由于管轄權問題該案件不能在滬立案。
而在歌詩達上的“偷盜事件”被曝光后,記者也曾以游客名義致電市政府外事辦、出入境管理處等部門咨詢相關事宜,各部門甚感突兀,無從處理。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國際上除了對海盜行為及公海販毒有明確的“普遍管轄權”的法律解釋外,對于其他違法行為并無專門的法律法規來約束。
人們不禁要問,“歌詩達”們危險嗎?公海是否成了違法者“犯罪天堂”了呢?
“失竊案”情節不夠嚴重?
8月22日下午起,中央電視臺、東方衛視和上海新聞綜合頻道分別對“歌詩達”郵輪上的偷竊案進行報道,隨后全國各大媒體包括新浪、搜狐、騰訊等網絡媒體,新聞晨報、東方早報等平面媒體也紛紛代表公眾向“歌詩達”船方發出質疑。8月24日,“歌詩達”方面發出聲明稱,愿意積極配合相關部門進行調查。
據知情人士透露,在郵輪失竊案處理過程中,失竊方與“歌詩達”號船長交涉中曾問及,“如果在你的船上發生了兇殺案,怎么處理?”船長聳聳肩,無奈地搖頭說:“我也不知道。”又問:“我們租用了你們的保險柜,但錢丟了你們沒有責任嗎?”回答是:“我們不是銀行。”失竊方要求船方打電話請中國警方參與協查被船方拒絕,要求船方協助控制作為犯罪嫌疑人的服務生,但被告知找不到此人。“歌詩達”靠港后,中國警方趕來調查,意大利船方不同意警方上船,迫使中國公安花了4個多小時才辦妥手續依法上船。
復旦大學法學院教授龔柏華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訪時表示,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公民參與跨境活動已經很頻繁。這其中必然會產生一些過去想象不到的法律糾紛,其中包括國際法或法律的涉外效力等,“本案的特點是在公海上,在一艘外國籍(意大利)船舶上發生的偷盜案,后來該船又停靠在中國的港口,受害人是中國籍公民。根據對我國生效的《海洋法公約》第27條‘外國船舶上的刑事管轄權的規定:沿海國不應在通過領海的外國船舶上行使刑事管轄權,以逮捕與在該船舶通過期間船上所犯任何罪行有關的任何人或進行與該罪行有關的任何調查。所以原則上港口所在國當局,不會對在其港口中停靠通過的外國籍船舶進行刑事管轄。”
但龔柏華也告訴記者,這規定并非是絕對的,因為《海洋法公約》第27條規定原則的同時,也規定了例外:但凡下列情形除外——(a)罪行的后果及于沿海國;(b)罪行屬于擾亂當地安寧或領海的良好秩序的性質;(c)經船長或船旗國外交代表或領事官員請求地方當局予以協助;或(d)這些措施是取締違法販運麻醉藥品或精神調理物質所必要的,“可見,如果存在前面兩種情況,中國港口當局是可以進行管轄的。但本案案情還沒有達到該種程度。”
上海市華聯律師事務所海事部主任陳發銀律師也向《新民周刊》記者指出,認定偷盜的事實存在困難,“郵輪到岸,游客紛紛下船,調查取證難,損失依據如何提出?加上本案中,游客的損失金額不大,最多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就算是起訴也是走民事訴訟,而不是刑事。”
“這件事也提醒我們,今后我們需要完善相關外國籍船舶停靠我國港口的管理制度,包括合理解釋‘罪行屬于擾亂當地安寧或領海的良好秩序的性質。如果中國公民被偷盜的數量和人數達到一定程度,就可達到這一標準。”龔柏華補充道。
公海管轄的認定
如此看來,此案的管轄權確實不在中國。那關于公海犯罪的管轄權到底如何判定,國際法上曾經發生過一個著名的“荷花”號案。
1926年8月2日,法國油船“荷花”號在公海上的西格里岬以北五六海里之間的海面上與土耳其船“波茲一庫特”號相撞,土耳其船被撞沉,有8名土耳其人死亡。第二天,當“荷花”號抵達伊斯坦布爾時,土耳其當局對碰撞事件進行了調查,隨后根據土耳其法律對“波茲-庫特”號的船長和碰撞發生時在“荷花”號負責值班的官員——法國公民德蒙上尉給予逮捕,并以死人罪在土耳其地方法院提起刑事訴訟。
1926年9月15日,法院作出判決,判處德蒙短期監禁(80天)和一筆為數不多的罰款(22英鎊)。土耳其船長哈森則被判了較重的懲罰。該案判決后,立即引起法國政府的外交抗議,因法國政府認為土耳其法院無權審訊法國公民德蒙上尉,船舶碰撞是發生在公海上,“荷花”號的船員只能由船旗國,即法國的法院進行審理,并主張這是一項國際法原則。但土耳其法院則依據《土耳其刑法典》第6條的規定,任何外國人在國外犯有侵害土耳其公民的罪行,應按該刑法處理,因此。對本案的管轄權并不違反國際法。
1926年10月12日,法國和土耳其簽訂了一項特別協議,將該爭端事件提交常設國際法院,請求法院判定:土耳其根據其法律對法國船員德蒙上尉進行刑事訴訟是否違反國際法原則?法院判決土耳其沒有違反國際法。但這個判決引起很大爭議。后來1982年第三次聯合國海洋法會議通過的《海洋法公約》規定了在公海上航行的船舶受船旗國管轄:“遇有船舶在公海上碰撞或任何其他航行事故涉及船長或任何其他為船舶服務的刑事或紀律責任時,對此種人員的任何刑事訴訟或紀律程序,僅可向船旗國或此種人員所屬國的司法或行政當局提出。”實際上修正了法院的判決。
“當然,這個案子是公海上船舶碰撞引起的刑事案子,與‘歌詩達號的偷盜案還是有所區別的。”龔柏華向記者解釋,“有關這方面的法律(主要是涉及管轄權問題的),國際上是有限的,因為各國利益不一致,很難協調。另外,有些國家沒有批準《海洋法公約》,如美國,它可能適用的是第一次海洋法會議產生的《公海公約》,但原則基本上是一樣的。”
龔柏華還告訴《新民周刊》,在我國則并沒有專門針對公海的法規,但在相關的立法中,都會考慮到《海洋法公約》涉及的公海制度,“如我國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法》,其中就會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