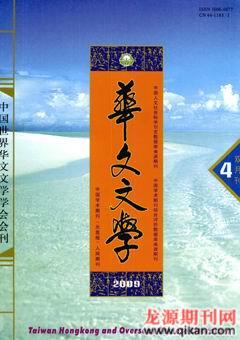高貴的單純,靜穆的求索
鄧秋英 周 亮
摘要:新移民作家林湄的小說創作體現了邊緣作家創作的獨特視角。前期的小說創作,作者把關注的焦點指向女性。通過處身于對物欲橫流的香港社會中的女性以及為取得外國居留權的女性命運遭際的刻畫,展示了男權制下女性的多舛命運。作者旨在喚醒女性的自我意識,探索出一條女性獨立自主的道路。后期的小說創作,主題發生了轉變,由關注女性轉向探索人性、神性,思考個體“小我”向人類“大我”的超越。從這一小說創作主題的轉變中,我們不僅能窺見作家自身寫作意識與創作視角的變化,也能透過林湄審視整個新移民作家的文學創作。
關鍵詞:女性;男權;宗教;神性
Abstract:Novels written by the New Immigrant writer Lin Mei are featured by the marginal writers unique perspective. In her early writings, Lin focuses on the vicissitudes of lives of women under patriarchy by depicting the female images in the materialistic Hong Kong society, and the experiences of those who strive hard for the rights of residence abroad, thus to arouse womens self-consciousness and blaze for them a path of independence. Thematic changes occur to her later writings as the attention is shifted to the universality of human nature and divinity. In light of this transition, we can not only discover Lins writing consciousness and her focus changes, but also get a general view of New Immigrant Literature.
Key words:female, patriarchy, religion, divinity
中圖分類號:I207.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I006-0677(2009)4-0048-06
近年來,新移民作家及其創作慢慢成為文壇關注的對象。他們以漂泊的經歷和獨特的文化感受為華文文學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在眾多的求索者中,林湄不可不說是堅忍、執著且影響頗大的一位。她以豐富的人生經歷及女性獨特的敏銳意識,先后創作了長篇小說《淚灑苦行路》、《漂泊》、《浮生外記》、《艾琴湖》,中篇小說《不動的風車》、《情網》,短篇小說集《羅經理的笑聲》等,并在2004年,推出了被譽之為“坐云看世景”的長篇小說《天望》。
在創作之路上,林湄以“邊緣者”自居,“我從邊緣的特殊視角,將人文精神、書卷經驗、生存感觀、生命意識以及對于靈魂、肉體的哲學和美學的思考,編織成串串問號,然后抽離掉自己的位置,坐在颯颯的白楊樹頂上,望天興問,沉思默想……”正是這一邊緣者的獨特視角,使林湄能以自身的生存體驗與文化感受,審視東西方文化之間的差異,反思現代科技與物質文明造成的社會危機,探索人類靈魂的終極意義。她筆耕不輟,在小說創作過程中完成了從早期的對女性命運的關注到對神性精神求索的主題的轉變。從這一變化中,我們不僅能感受到作者由自我到大我的主體意識的升華,也能窺見在邊緣的基點上,作家所表現出的深刻的悲憫心態和終極的人文關懷。
一
書寫女性,展現女性的時代命運及探討女性解放的出路一直是文學創作的重要母題之一。在創作之初,林湄曾說:“我本身是女性,有自己的豐富經歷,對女性命運特別關注。傾注于作品里的女性是來自現實的,她們的命運與時代息息相關。”因而,對女性命運的探討不僅是林湄早期關注的焦點,也是她小說創作的重要主題。加之作為女性所特有的敏銳感悟與多愁善感,使她早期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形象充滿鮮明的立體感,在展現她們多舛命運的同時又表現了作家對男權制的強烈批判。
林湄真正開始創作小說是在到香港之后。在這一時期,作者以香港為背景,展現了物欲橫流的社會中婦女的生存狀態。《新婚的新娘》中的俞琳琳憑借才藝和美色嫁給了知名富商,新婚燕爾過后卻突然發現被騙。面對百無聊賴的生活,俞琳琳始終處于被動地位,富商只不過將她作為花瓶看待,是一個在男權之下寄生的角色。《孽》描述了靳燕子作為情婦的痛苦與矛盾。原本把愛情看得純真圣潔的靳燕子在知道摯愛之人的丑惡心靈之后自暴自棄,當情人的兒子用真正的愛情感化她時卻又被她親手所扼殺。《云妮的黃昏》則展現了大陸女子云妮為取得外國的居留權輕易與人結婚,最后被人拋棄并淪為瘋子的悲慘結局。
整體上看,這三個女性都沒有真正獨立自主的意識,她們沒有屬于自己的職業,因此要生存就必須依靠男性。她們把男性看成是支撐自己一切的支柱,而一旦男性對她們棄之不顧,她們就如鮮花一樣瞬間凋零。可悲的是,她們生活在男權制下,男子們不是把她們看成泄欲的對象,就是生育的工具,對女性的尊嚴毫無顧忌地踐踏。作者用犀利的眼光剖析女性的生存命運,并把希望寄托在女性的自強上。因而,在《芳齡》中,作者塑造了飽受丈夫病態束縛與虐待之苦的蓮馨,在自殺未遂之后,通過工作賺取路費,最后毅然離家出走。這一決絕的姿態,暗示了女性自身意識的不自覺蘇醒。
林湄通過展示這些女性的被動地位與壓抑命運,反思造成這一現狀的社會因素,并最終領悟到要使女性獨立必須首先在經濟上獨立。西蒙娜?波伏娃在《第二性》里指出:“女人通過有報酬的職業極大地跨過了她同男性的距離,此外,再也沒有別的可以保障她的實際自由。”因此,在《淚灑苦行路》中,作者就別具匠心地塑造了三位新女性。她們有著強烈的自主意識,并想通過自己在經濟上的獨立與男權社會對抗。三位女性分別代表了不同的類型。瑞沁是位傳統的中國女性,身為文字編輯的她溫柔、賢惠、善良,但丈夫不把她當人看。為擺脫這種遭遇,她毅然選擇了離婚并自己撫養幼子,這是以往女性可望而不可即的。正因為她在經濟上徹底的獨立,因而她能沖出婚姻的墳墓,過獨立自主的生活。鳳萍是一位強烈的復仇主義者,她想在商海打拼創立屬于自己的公司,在婚姻觸礁之后,她開始對曾經欺騙自己的男人進行瘋狂報復。多利則是新時代的女性,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視別人的眼光于不顧。
在這里,作者旨在探討新時代娜拉出走之后的女性命運走向。通過展示三位女性在事業與愛情之間的掙扎與痛苦,林湄敏感地覺察到了女性想要改變自身命運的艱難與挫折。在社會沉重的壓力之下,瑞沁被自己鐘愛的文學出賣;鳳萍則在親手殺死了騙自己的丈夫之后,開始質疑自己所做的一切;多利在經歷同性戀之后,也不幸遭遇車禍而殘廢,最后遠走他鄉。這一富有隱喻意義的結局實際上體現了作者在尋求女性出路時的彷徨與痛苦。
在90年代所寫的《漂泊》中,作者繼續把關注的焦點指向女性及其生存狀態。它以女主人公吉利為中心,展示了出國女性的命運悲喜劇。與香港女性不同的是,吉利已回復到女性真正自我的層面,即具有獨立人格與自強的女性意識。吉利在面對異國文化以及丈夫迪克一開始的“狗有時比女人好”的思想時,她不卑不亢,始終保持自己獨立的人格,潛心于自己的繪畫事業。當她在繪畫事業上功成名就時,迪克自卑的心理開始突顯,他對吉利說:“我的價值觀是那么的淺薄、愚蠢,言行粗俗,欠教養,又懶又自私,而你是有身份、有前途、有魅力的女性,我不想成為你的附庸品,也不想讓人因你有我而受人風言風語。”在這部小說里,作者別有用心地將男性置于自卑的位置,并采用強烈的對比,讓女性的真誠與愛喚醒他們心底的自信。吉利的生活模式為女性開辟出了一條嶄新的道路,即首先完善自我、獨立自主才能在生活面前游刃有余。
總體上看,無論是最初沒有經濟實權的全職太太,還是沖破婚姻不幸的“女強人”,或是在國外為取得居留權而奮斗的女子,她們走過的道路都充滿了荊棘與艱辛。林湄將不同的女性作為自己早期小說創作的主角,實際上是想借文學的方式來思索女性尋求解放與獨立的出路。“對于人、人生、生活,我有太多的問號、難題,太多的憤慨……就在這個時候,我找到稿紙,在一行行的空格里,填上我的血與淚,痛苦與快樂、探索和理想。”
應該說,林湄對女性命運的關注是自覺的,同時又是全面與深刻的。在這一關注中,除了對女性悲慘遭遇的同情外,還有對的男權思想和社會制度的批判。在林湄的筆下,“狗比女人好”、“女性只是生育工具”是男權社會的主要觀念。男性就是呼風喚雨的主宰者,他們對于女人的要求是呼之即來,揮之即去,因而女性所飽受的壓抑與扭曲的痛苦就顯而易見了。可貴的是,作者打破了自身文化的制約,將這種對于女性命運的關注放到了文化歷史毫不相同的異鄉文化中。通過中國女子與異國男子結合之后,其被壓抑的生存狀態沒有絲毫改變的描述,賦予女性問題世界性意義,從而使女性自我意識覺醒的呼喚和解放之路的探索更具有厚重感。
二
林湄后期的小說創作,主題發生了質的飛躍,即由關注女性命運,上升到神性的探索之上。這體現在她50萬字的長篇小說《天望》中。在小說的最后,作者用“人的最高特性——神性”作為小說第53章的標題,亦是作者主觀意圖的體現。在這里,神性不僅是基督的神性,也是個人內在的神性。前者能使人們堅信宗教的信仰,后者能使人的靈魂得到凈化,人性達到完善的境界。
20世紀是人類歷史上空前動蕩混亂的世紀,壟斷經濟和科技革命合力沖擊著傳統觀念,慘烈的戰爭、丑惡的屠戮使人類陷入了沉重的悲哀之中。在科技文明發展的同時,人類卻越來越迷失自我,而科技的產品只能造成人與人之間越來越陌生。對于現代人的精神危機,榮格曾深刻地指出:“現代人已經失去了其中古時代兄弟們所有的心理信心,現代人的信心都已為物質安全、幸福及高尚等理想所代替。可是,這些理想要能實現所需要的樂觀成分當然更多。甚至于物質的安全現在亦成為泡影了,因為現代人已開始發覺,在物質上的每一次‘進步階段,總是為另一次更驚人的浩劫帶來更大的威脅。”
林湄敏感地捕捉到了人類這一深層的靈魂病癥,并將它提升到一種形而上的層面。對上帝的仰望與對神性的追求,給這部小說帶上了強烈的宗教色彩。“文學與宗教的關系大致上有兩種現象,一為文學的創作主體有強烈天人感應的宗教色彩;一為宗教的信仰內涵借助文學的思維方式來表達。”林湄不僅是文學創作者,也是虔誠的基督徒,因而借文學表達宗教意識十分自然。在這部小說里,現實信仰、宗教信仰相互交織,戀童癖、同性戀、吸毒、謀殺、偷渡等各種社會病癥層出不窮,真正展現了后工業時代世人的生存現狀。作者透過社會百態,返歸到人性層面上,從紛繁復雜的社會現象中發現了人的最高特性——神性。
小說主人公弗來得是一位堂吉訶德似的救贖者。作為農場主的孫子、生活無憂無慮的他,自小對基督教情有獨鐘,善良且充滿了愛心。在接受了祖父與W牧師的教化之后,他毅然賣掉了農場和土地,選擇了傳教這條路。在他看來,人只有信仰才不會在這個物欲橫流的社會中迷失。他勸人為善,一直為“天國的大獎”而積極跋涉。他說:“我想拯救受難的靈魂!哪怕是少數。”弗來得清醒地意識到現代人精神信仰的衰微與良知的淪喪,他想用宗教的方式拯救人類的靈魂。在他看來,麥古思的放蕩的性觀念,比利的不修邊幅,漂泊流浪的個性,以及羅華明與艾克那種違背人性的同性戀傾向都是不可理喻的。他們是病態的心靈,弗來得要拯救他們。作者這一獨具魅力的角色安排,實際上體現了作家對人類精神取向及其靈魂歸屬的焦慮。
弗來得想用良知與基督精神拯救世人,在現實中卻不斷碰壁。他出于人道主義向法院報告偷渡者的死亡事件,舉報地下工廠,揭發“娛樂中心”實際上是變相妓院等等,遭到黑組織的毒打和摧殘。而他救贖的對象,羅華明、麥古思以及比利、艾克等不僅沒有獲得靈魂凈化,反而嘲笑弗來得行為過于單純與幼稚。到最后,他的腳被人打瘸了,眼睛被人弄瞎了。然而面對這些,弗來得充滿了坦然,這其實是基督受難精神的現實寫照。在基督看來,“我們的生命中存在著一種能夠用來為他人服務的力量,這種力量只能從痛苦中產生,而不能從其他任何渠道產生。”因而,弗來得要想用基督精神拯救他人,就必須犧牲與奉獻。
在作品中,弗來得經常自言自語,似乎和上帝在對話。而在弗來得義無反顧的傳教過程中,這種神性的精神也慢慢地突顯。在經受肉體的折磨時,弗來得尚能忍受,一旦精神遭到摧殘,則整個靈魂陷入崩潰的邊緣。當他得知兄弟依里克拆掉了充滿兒時記憶的小教堂時,整個肉體和精神陷入了昏迷的狀態。周圍人無法得知其原因。在這里,小教堂已成為弗來得精神的支柱,是他與上帝交流的中介,也是他宗教信仰的精神依歸。小教堂消失了,其神性精神也將受到重創。這一天人感應的奇幻刻畫,正體現了基督神性的崇高與神秘。
在弗來得昏迷過程中,依里克不僅聘用了美國的名醫,還試用了剛剛研發的新藥治療弗來得,但這一切都是徒勞。最后是妻子微云的眼淚喚醒了他。在弗來得的大愛面前,微云被感化了,最終回到了弗來得的身邊。微云最后說:“是你的‘愛征服了我,這個世界沒有比愛更具有征服力。”這一象征性的結局又復歸到了基督之愛的精神主題。“愛確實能夠使我們擺脫我們的自我,能夠進入我們的心靈,占據我們的心靈,把自我從我們的心靈中趕出去。”在弗來得真正徹悟大愛之后,也開始傾聽他者對自己盲目優越感的批判,并調整自己的感受、思維和行為方式,神性使他的內心不斷完善。在最后,他原諒并暗地里幫助妻子,接受了自己妻子與別人生的兒子,真正超越了“小我”而升華至人類的“大我”。在弗來得身上,我們看到了信仰的力量,它能激發人的神性,凈化人的靈魂。
在這里,我們能清楚地看到作者的筆觸已不再徘徊于女性之間,而是把視角轉向了那個一味拯救人類的英雄弗來得身上。通過基督教形式的拯救,作者實際上想要探討的是,在后工業時代,在科技文明造成人性異化的迷茫中,神性能否最終拯救人的靈魂。“在高科技的旗幟下,人類的困擾、彷徨、憂傷、驚恐感有增無減,甚至集體地進入喪失生存意義的地步,像被趕到沒有出路弄子里的牛馬一樣。面對這樣的風景,作家的心境如何?渴求的是什么?自我位置和理想怎樣?如何看待文化間的異同?如何對待科學和人性、融入和反思等等問題?文明的真諦到底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這是我的焦慮,也是我對世界人生的思考和叩問。”這一形而上層面的追求,使得作者把寫作的立足點轉向了整個人類生活,實現了作家對自身的超越。而這種超越也是文學自身發展的內在要求,“真正將文學作為人的精神看守,有責任感和使命感的作者和欣賞者,在對生命信仰的沉思中,在轉身的憂嘆中所達成的是對人的活動的有限性的超越,對人性有限性的超越。在精神上超越人的活動的有限性和人性的不圓滿,獲得一種超越生命本身的體驗。”
三
林湄作為新移民作家中默默耕耘的創作者,其十年如一日的寫作姿態,正證明了她對待文學的嚴肅與認真的態度。從她小說創作主題的轉變中,我們能清晰地看到作者思想及其視角的變遷。由關注女性現實命運轉而探討人類精神的歸宿,林湄小說創作所做的跨度是巨大的。追溯其轉變原因,首先得歸因于她豐富多彩的漂泊經歷。林湄在接受采訪時曾說:“經歷、漂泊將我的視角、思考和文學意識帶到一個嶄新的位置……在中國大陸時的創作心態多注重‘自身的生存話語、‘人與人之間關系、‘人與財富權勢等問題的是非榮辱的判斷和思考。出國后改變了我對世界、人生、藝術以及生存方式的看法,開始重視并體會‘人與自然宇宙、‘人與自己關系等大宇宙觀。”從大陸到香港,再到歐洲,她跨越了三種社會制度,體驗到了東西文化的差異,這一漂泊的經歷不僅開闊了她的眼界,也成就了她的文學,使她能跳出蕓蕓瑣事,站在邊緣的位置看中心,審視生命與情愛、靈魂與死亡等終極意義上的人類問題,并對人性深層進行深刻拷問。
其次是宗教對林湄人生觀的影響。從令人艷羨的“紅標兵”一夜之間變成被人唾罵、指責的“黑標兵”;從甜蜜的家庭生活到婚姻觸礁;從滿腹雄心于商海打拼到被騙得血本無歸,林湄所走過的路正可以用她的小說標題“淚灑苦行路”來形容。對于一個敏感的作家,這樣的痛苦如何排遣呢?宗教在這時成了她擺脫痛苦、寄托感情的精神小廟。“我是在屈辱、自尊自愛、憤慨、壓抑、痛苦、失望、悲傷等人生遭難中接近宗教的。宗教能引導人類從紛爭凌亂的塵世中抽離出來,走向自然宇宙,在浩淼的天體里再識‘有限‘無限的奧妙,從而直接間接地幫助人脫離痛苦、不安和躁煩,令心靈平靜、安然、祥和,不為外物所動心,‘無心于事,無事于心,過愉快的日子。
再次是林湄自身堅持不懈的性格使然。她原名叫林梅,之所以改林湄,是為了取“快要枯死之林,種在水之湄上”之意。以表示自己的創作決心和對寫作的憧憬。她本可以安居一隅,但為著自己追求的夢想,不惜輾轉于香港、比利時、荷蘭等,這一特殊生活方式的選擇體現了她不甘平淡、追求縱深的性格。在這一性格的驅使下,林湄小說創作的主題也就越來越深刻。她不會再執著于女性那個狹小的圈子,而是由女性而及全人類,由關注人的普遍性轉而挖掘人的最高特性——神性。
對于新移民文學的發展過程,陳瑞琳曾作了一個宏觀的概括:“新移民文學發端于80年代后期,濫殤于90年代,經歷了由浮躁、粗糙到沉潛、過濾的初級階段,從單純描寫個人沉淪、奮斗、發跡的傳奇故事,已逐漸走向那一代人命運的反思,對中西文化夾縫里的新移民文化心態的表現,進而對生命本身價值的探討。”從這一論說中,我們能看到新移民文學自身主題及內容的嬗變,也能看到在創作過程中,作家創作意識的升華。
在以往對海外華文文學的研究中,研究者更多地是從作品所表現的文化差異、異國情調層面進行研究,認為在這些移民文學的關系中,指涉的方向就是“原鄉”文化。陳國恩教授曾焦慮地指出:“我拜讀過一些學者關于華文文學研究的文章,發現他們經常持有一種固定的觀點,認為華文作家與其所居住的國家一定存在著文化上的隔閡,認為他們在與‘他者的接觸中才認識了自我,因而也就比在中國時更清楚地感受到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那些屬于‘自己的溫馨成分。有沒有這樣的情形?有。但我敢肯定又不全是這樣的情形。”
當然,不同的作家由于經歷不同、思想各異,因而他們在創作時是站在一個更高層次表現萬花筒似的社會人生百態,探索人類終極的價值,還是將本土文化與異國文化執拗地看成“自我”與“他者”的對立,這是作家的創作自由。作為新移民的代表性作家,林湄的這一小說主題演變,在文學創作上有著深刻的現實意義。從中我們不僅能看出新移民作家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也能看到這些作家們在“邊緣”的社會層面,審視世界病癥、把握世界脈搏的創作視角,這是新移民文學的獨特之處。它使人們能真正看到在文化多元的時代,文學打破國與國之間的藩籬之后,向具有世界眼光的文學邁進的趨勢。
從立足個體、群體到立足整個人類世界;從展現物質文化之間的差異到探索人類精神、靈魂的神性特質,并用信仰來填補現代人的精神空缺,這一文學主題的轉變,是林湄對自身和世俗的超越。克爾凱廓爾把宗教層面作為人類生存方式的最高層。他曾說:“人類最高的激情就是信仰。每一代人當中都有許多人走不到那么遠,但也沒有一個人的腳步能超過信仰。”
從林湄的創作轉變中,我們看到了移民作家中一種新的價值整合,即在自身文化身份焦慮已被調適的情況下,他們不會再執著于文化一隅表現漂泊者在面對異域文化時所表現出的惶恐。恰恰相反,他們會將這種悲天憫人的情懷轉向整個人類的精神世界。像指點江山一樣,站在恰到好處的邊緣位置,去審視人類現世的風景。林湄從現代人的精神危機中苦苦求索,并找出了一副治愈人性靈魂的良藥——神性,通過英雄弗來得的形象,昭示了人的靈性之光。這實際上也是作家林湄的一種理想,一種對人類靈魂歸宿的企盼。然而邊緣作家描寫邊緣人的故事是一條孤獨的路。但正是這種總體意義上的孤獨給了這類文學作品以特殊的性質,那就是作家在寫作時是真正地嘔心瀝血追尋真諦,心中完全沒有暢銷與否的俗念。因而,林湄憑借對基督教的信仰,希望通過文學來張揚人的神性精神,并通過這種神性來拯救人的靈魂,以對抗科技文明對人性造成的異化。
林湄:《天望》,長江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第1頁,第280頁,第448頁,第205頁。
王紅旗:《“坐云看世景”的荷蘭華文女作家——與林湄女士暢談她的魅力人生和長篇小說〈天望〉》,《華文文學》2007年第2期。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湖南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771頁。
林湄:《漂泊》,安徽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第209頁。
林湄:《誘惑?后記》,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215頁。
[瑞士]卡爾?古斯塔夫?榮格:《現代靈魂的自我拯救》,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305頁。
鄭志明:《中國文學與宗教》,臺灣學生書局1993年版,第1頁。
[英]詹姆士?里德:《基督的人生觀》,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143頁,第93頁。
肖四新:《西方文學的精神突圍》,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頁。
江少川:《漂流、再思、超越——林湄訪談錄》,《世界文學評論》2009年第1期。
陳瑞琳:《原地打轉的陀螺》(上),《中外論壇》2002年第3期。
陳國恩:《從‘傳播到‘交流——海外華文文學研究基本模式的選擇》,《華文文學》2009年第1期。
[丹麥]索倫?克爾凱廓爾:《恐懼與顫栗》,華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11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