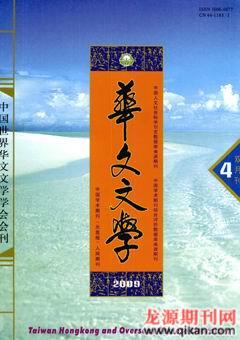酬神、娛人與文化權的訴求
康海玲
馬來西亞華語戲曲的“根”在中國,它是華族移民在馬來西亞異質文化土壤里培育起來的一種特殊的藝術樣式,體現了華族的文化認同。在多元種族、多元文化的國家里,華語戲曲作為一個標志性文化,它是華族的一個象征性符號,與馬來族、印族及其他民族相區別。華語戲曲在馬來西亞存在的意義以及社會文化功能不是單方面的,在不同的語境下有不同的功能和意義,其走向是多元的,表現在從較為單一的宗教范疇,擴大到世俗社會的領域。
一、宗教功能的發揮:酬神娛鬼
華語戲曲在馬來西亞生存的最首要的決定因素,在于宗教功能的發揮。出于華族宗教生活的需要,華語戲曲與宗教祭祀的關系密切,一向都是宗教祭祀中的重要內容之一。宗教祭祀為華語戲曲的上演提供了適宜的機會,同時也利用華語戲曲這一表演形式爭取信徒,擴大影響。華語戲曲屬于俗文化的范疇,和華族的節日民俗息息相關,它在馬來西亞的移植和發展,明顯地表現出民俗性的特征。華語戲曲的宗教功能主要體現在“酬神娛鬼”這一層面上。
不容置疑的是,長期以來,華語戲曲在馬來西亞上演,沿用的是中國鄉間演戲的世俗通例,這些世俗通例,離不開華族宗教信仰的需求,特別是離不開華族的民間信仰。華族的民間信仰是從中國本土承傳而來的,就其歷史形態而論,它是屬于古老信仰的遺存,具有自發、自然、自在的本色。在馬來西亞華人的日常生活中,始終以它的族群宗教風俗的特色,保持著無法遏止的流傳趨勢。它深深地植根于中華傳統文化的沃土之中,廣泛地影響和支配著本土以及海外華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認真、全面地考察馬來西亞華族的信仰觀念,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華語戲曲文化的生成和發展;可以看到馬來西亞的普通華人是怎樣采取超人間力量的形式支配他們的生活;還可以通過他們對神靈、鬼靈、精靈等的崇拜,理解他們賦予這么多幻想物以多么強的意志和多么大的權能;更可以看到他們如何遵照諸神眾靈的旨意采取他們的一系列行動。
酬神娛鬼是馬來西亞華語戲曲最主要的功能,而要考察戲曲的這一最本質的特色在馬來西亞的具體表現,主要得回答三個方面的問題:即活動的主體是誰,誰來酬神娛鬼;酬哪些神娛哪些鬼;酬神娛鬼的目的是什么。華語戲曲在馬來西亞流播,離不開華人社會給予的有力支撐。華人社會的形成與發展為華語戲曲的生存儲備了相應的觀眾群體,而這個特殊的游離于馬來西亞主流社會之外的廣大的華人群體構成了華語戲曲酬神娛鬼活動的主體。從觀眾的角度而言,馬丁?愛思林說過:“沒有觀眾,就沒有戲劇。” 同時,華人社會以其內部特有的幫群組織結構為華語戲曲各劇種提供了賴以發展的可能。戲曲所服務的主要對象即神鬼等,大多移植于中國本土,其中有一部分已經本土化。馬來西亞的華族早先大多來自閩粵兩省,華語戲曲所服務的鬼神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即閩粵兩省移民共同信奉的神鬼和各方言群體各自所信奉的神鬼。在中國本土,閩粵兩省的宗教信仰特別發達,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所信奉的神靈范圍廣泛、數量繁多。種種神靈信仰,不僅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而且也輻射到馬來西亞華人社會,建構了一個廣闊無垠、上下莫測的自然宇宙和一個光怪陸離、奇異神秘的幻想世界。
華人通過演戲酬神娛鬼,其實質體現在功利性上。在華人的信仰里有大大小小的、名目繁多的神鬼,其原因在于各路神鬼與人有各種各樣的利害關系,所以崇拜眾多的神鬼,就成了現實之需。華人用崇拜的各種手段與神鬼進行利益上的酬答互換,在這個意義上,戲曲演出包括木偶戲的奉獻是最隆重的酬神娛鬼還愿儀式的重要組成部分,打上了明顯的功利烙印。華人在信奉神鬼中最為普遍的功利要求,無外乎求吉避兇、祈福消災、袪病驅邪,這可以說是華人們永恒的追求了。華人酬神娛鬼,這種信仰行為的功利性還突出表現在對所有神鬼的獻祭上,不管是殺牲、擺供、燒香、敬酒、演戲,表面上說是敬神鬼,其實質是討好、獻媚、或買通、取悅神鬼。在祭祀神鬼時的所有投入,其目的歸根結底就是為了換取神鬼滿足崇拜者的實際要求,也就是說,希望滿足人們在物質生活上或精神生活上的索求。供品以及戲曲可以看作是人與神鬼打交道的公關手段,有利于建立牢固的情感紐帶,人只有把自己和所崇拜的對象聯系在一起,才能實現人與神鬼的會通。在新馬一帶,神靈在戲劇演出場域中的存在,除了作為演出的觀眾之外,還經常依托于巫師或者演員而在場。
在馬來西亞華人的宗教觀念里,華語戲曲通常作為具有某些神圣象征意義的符號而存在,它架通了現實與精神世界的橋梁。通過華語戲曲演劇活動這一可見的屏幕,我們可以看到隱藏在宗教背后許多容易讓人忽視的東西,而這些正是我們了解華人社會的必不可少的內容,即通過華語戲曲的酬神娛鬼娛人功能,我們可以洞察華人個體情感與集體表象之間的復雜關聯,看到華人的道德滿足、社會性的窘迫以及審美好惡等。在這方面,格爾茲的巴里島系列民族志研究已經給我們做出了典范,他所采用的“深描”實踐,是在反思民族志寫作傳統的基礎上進行的。如果我們把文化研究的這種方法及種種觀念引到戲曲研究中來,那么,無疑為戲曲研究打開了一個新天地,特別是為我們揭示華語戲曲在異質文化土壤里的諸多演劇活動的內在本質提供一個科學、獨特的視角。
二、從酬神到娛人和狂歡
華語戲曲在馬來西亞的普遍存在,其社會文化功能,除了突出地表現在宗教語境下的酬神娛神悅鬼,還明顯地體現在世俗語境下的多功能整合。考察華語戲曲的世俗功能,最重要的在于“娛人”。華語戲曲隨著早期華僑先民的腳步,越來越深地融進馬來西亞這個居住國的現實生活,其中一個頗為重要的原因是出于華族對娛樂的渴望與追求。“作為一個民族,中國人具有一種強烈的做戲的本能。可以說,戲劇是中國人唯一的一個全民性的公共娛樂,戲劇之于中國人,就好比運動之于英國人,或斗牛之于西班牙人一樣……”有中國人聚居的地方就有戲劇的存在。海外華人自覺的文化傳播,使華語戲曲獲得了更為廣大的生存空間。在馬來西亞,華語戲曲的生命也因此被延伸、維持了一百多年之久。
在馬來西亞華人社會諸多的傳統節日中,廟會和中元節的儀典在娛樂性方面表現最為突出。柔佛州的柔佛古廟每年三月初三的廟會以及檳城的中元盛會是最為典型的。馬來西亞是個工商型國家,華族在社會生活中的根本要義是發展經濟,所以大大小小的神誕演戲都具有中國南北廟會的幾個功能,即宗教功能、文化娛樂功能及商業功能,這是馬來西亞華語戲曲演出活動的特別之處。柔佛的新山是潮州人大量聚居的地區,潮汕一帶的地方文化傳統隨移民的腳步在這里扎下了深根,也為以華語戲曲為代表的表演藝術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每年的三月初三,由柔佛潮州八邑會館主辦的柔佛古廟的廟會,是潮州傳統文化薈萃的中心,其演出包括潮劇欣賞、潮州折子戲、潮州大鑼鼓、潮州木偶劇、潮音演唱、潮州兒童歌舞,廿四節令鼓、中華武術、舞龍舞獅、華樂演奏等,可謂多姿多彩,盛況空前。華人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選擇娛樂的項目,不同的人都可以參與,盡情享受取樂。華語戲曲的娛人功能得到了全方位的體現。
檳城的中元盛會也充分體現了華語戲曲的娛人功能。每年中元節前后一個月的時間里,檳城二百多個街區都有相關的系列活動,有的依托華人寺廟而舉行,有的不依托寺廟而在街區附近的廣場或空地舉行。中元節的主要活動是祭祀,在酬神娛神悅鬼的過程中,華人也迎來了一年中最熱鬧、最歡慶的時光,神、鬼、人都盡情地娛樂。馬來西亞檳城中元節的這種娛樂性在包括中國本土以及東南亞其他國家在內,都是最鼎盛的。如果柔佛古廟的廟會是潮州傳統文化的全方面展示,那么,在以福建人為主的檳城中元節,堪稱中華傳統文化的遍地開花。其規模之大、節目之多,令人矚目,其中最突出的是華語戲曲的展演。華語戲曲各劇種爭奇斗艷,有潮劇、粵劇、瓊劇、歌仔戲、福建木偶戲、潮州木偶戲等等,可謂華語戲曲的大觀園,真是鼓樂喧天,熱鬧非凡。華語戲曲的娛神娛鬼娛人功能得到了理想的融合。
馬來西亞華語戲曲的演劇活動,體現的是一種狂歡的精神。這種演劇活動,當地華人稱為做大戲、出街戲。俄羅斯學者巴赫金對狂歡節的研究很具權威性,他深入研究了拉伯雷的創作與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民間文化,對中世紀的民間狂歡節文化作了經典性的研究。他強調:“中世紀的戲劇演出形式有相當大一部分傾心于民間廣場的狂歡節文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它的組成部分。”戲劇演出活動具有狂歡精神是顯而易見而且由來已久的。人類學者趙世瑜和劉曉春等人也曾從不同角度研究過中國廟會的狂歡精神。“所謂狂歡精神是指群眾性的文化活動中表現出的突破一般社會規范的非理性精神,它一般體現在傳統的節日或其他慶典中,常常表現為縱欲的、粗放的、顯示人的自然本性的行為方式。”這里所說的“非理性”針對的并不是啟蒙時期與更晚近的非理性意義,而是指情感至上的純粹由感情支配的一些行為方式。這種精神源于古希臘那種行為放蕩不羈、具有狂放顛覆的酒神節。人們普遍認可由狄奧尼索斯崇拜而來的酒神精神,和日常生活規范相比,是對現實生活秩序的顛覆,是對當下文化進化中各種規范性壓迫與束縛的一種本能的反動。世界上許多地區的許多文化活動,都不同程度地被賦予狂歡精神。
馬來西亞華人做大戲所體現的狂歡精神,具有原始性、全民性和反規范性的特征,顯示出華語戲曲在馬來西亞這個國度特殊的生存狀態。華人通過演戲酬神娛人,其原始性首先體現在華語戲曲及其演出戲俗的來源方面;其次還體現在這種群體狂歡是原始狂歡精神的某種延伸和拓展;再者還體現在華族參與者對世界的特殊感受上。全民性是狂歡節的本質特征,華族演劇活動的全民性,體現在華語戲曲的演出活動突破了方言群體的局限;還體現在打破了華人社會的階級、階層和等級的界限。華人社會做大戲,如果從文化特征的層面上審視,那是對馬來西亞現實文化的某種程度的挑戰,特別是對巫統主流文化的挑戰,其反規范性體現在多個方面:如婦女可以無限制或較少受禁忌地參加做大戲等活動;做大戲時所使用的服裝和道具等象征性物品也比較異常怪誕;華人大肆鋪張的表現十分突出;做大戲具有一種顛覆性和破壞性的特點等。
三、文化權的訴求
在馬來西亞華人社會里,華語戲曲經歷了一番艱難的傳承,從馬來西亞傳統性的社會到殖民性社會,華語戲曲始終在華人的公共生活中散發著魅力。當馬來西亞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都向現代化邁進的時候,馬來西亞華人文化也經歷了一場現代化的轉型。在向現代化邁進的社會語境下,華族宗教儀式的變遷,主流文化對華語戲曲的排斥與禁限等,使得華語戲曲不斷遭受生存的詰難,逐漸淡出華人社會。在文化多元化的現代化語境中,如何把握機遇以拓展戲曲藝術的生存空間,以文化自救的方式實現華人文化權的訴求,這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在馬來西亞,華語戲曲的演出一向依托于宗教,并作為宗教儀式的一部分賴以生存。然而,隨著馬來西亞的現代化進程,特別是華人文化的現代化,在華人社會民眾的日常生活領域中,長期傳承下來的、地方性的、華人社區性的宗教儀式發生了一些變遷。變化最大的是儀式的內容,其次是儀式的功能。宗教儀式中離不開酬神娛鬼的表演環節,華語戲曲曾經占據了表演的舞臺,成為人們因循守舊的一種奉獻給神靈的禮物。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華語戲曲這種表演形式逐漸被歌臺所取代;同時,電影也在一定程度上擠兌華語戲曲的市場,華語戲曲面臨著嚴重的現實困境。另外,在功能方面,即便在宗教儀式中依然保留原有的華語戲曲的展演,但是出于華人社會各種現實方面的需要,華語戲曲的演出活動在彰顯其最重要的宗教功能的基礎上又不可避免地生發出一些新的功能,充分顯示出其本土性的一面。
導致華語戲曲從其最重要的生存場域——華人宗教儀式中逐漸淡出的原因,除了向華人社會洶涌而來的新思潮和新型文化娛樂形式以不同的方式瓦解了原本穩固的戲曲觀眾群,特別是娛樂性十足的歌臺的介入誘發了華人觀演模式的轉型,動搖了華人宗教儀式中華語戲曲存在的穩定性,造成了華語戲曲生態的逐漸惡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即華語戲曲自身的困境導致古老的文化娛樂形式陷入了實質性的生存危機。
華語戲曲自身的困境最突出地體現在語言的問題上。在東南亞多元種族、多元文化、多元語言的社會結構中,語言界定戲劇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表現出明顯的復雜性。華語戲曲的概念基點是“華語”,馬來西亞華語戲曲指的是用華語方言演出的、主要來自閩粵的方言劇種,它和泰國華人社會中用泰語演唱潮劇,印尼華人用通俗馬來由語演出中國傳統曲目不一樣,表現出較為純正的馬來西亞華語方言特色。語言是構成現代民族這一“想象的共同體”的最關鍵的因素,也是華人傳統文化和藝術發展遇到的最根本的致命性的問題所在。周寧教授強調:“東南亞華語戲劇的問題不是戲劇,而是華語……在東南亞華語戲劇史上最大的問題或最敏感的話題是本土化與中國化的沖突,這個問題的核心是語言,背景是現代民族主義意識形態。”馬來西亞華人對華語方言傳承的漠視甚至斷裂,導致了華語戲曲的衰弱。當然,華人對華語方言的傳承直接受制于國家的語言教育政策。
在種族問題十分敏感的多元種族、多元文化的國度里,華語戲曲又不可避免地遭到主流意識形態的排斥和禁限。通過禁戲,馬來西亞政府強調的是政治社會權力的法統。禁戲的實質體現了華族意識形態與官方正統意識形態之間沖突的緊張狀態。馬來西亞是個種族矛盾敏感的多元種族的國家,官方經常采取各種法律手段限制各種族內部意識形態的發展和膨脹。對巫統政府而言,各種族都必須從屬于馬來族的統治,在意識形態方面都能掌控于官方的意識形態當中,這是巫統最大的理想,也充分彰顯了官方意識形態的霸權。在馬來西亞市民社會流播的華語戲曲,構成了一種對巫統社會深具威脅的市民社會意識形態或稱民間意識形態。官方利用禁戲的策略,達到官方意識形態對民間意識形態控制的企圖。
正是在這個多元種族多元文化的國家里,文化權的訴求顯得非常重要。對各種族而言,文化的獨特性和差異性是客觀存在的,不同的文化形態在文化世界的秩序中均有獲得各自生存空間的需要與權利。無論遭受怎樣的禁限,華語戲曲始終保持一息血脈,這是華族文化權訴求的勝利。以華語戲曲為代表的一系列華族傳統文化事象,應該在現代轉型的形勢下,在文化權的訴求過程中,既保持其鮮明的文化個性和獨立的品格,又重視改革創新以確保文化自救,這樣才能與馬來族、印族等友族的文化相融合,共同締造馬來西亞的國家文化。
文化權是文化權益的集合。如果說社會是政治的、經濟的,那么,首先應該強調的是社會應該是文化的,是一個以文化權為核心,漸次展開的時間和空間相交織的過程。特別是對象馬來西亞這樣的多元種族、多元文化的國家而言,文化問題顯得尤為突出。“文化權既涵蓋著政府、民族、國家及團體或個人接受、抵制、生產、消費文化的權益,也包括擔當促進推動文化、繼承傳遞文化的義務,只要有人的存在,就有個人與群體文化權的存在與訴求,它既是一切權力或權利的前提與基礎,更是表達或規范其他權力或權利的向度,不存在離開文化的權力或權利,因為任何‘權的表述或要求都是依照文化或憑借文化實現的,也不存在離開權力或權利的文化,因為文化存在,恰恰或者說只能通過權力或權利予以表達,不存在無權益的文化,也沒有無文化的權益,文化與權益不可分,故此,任何文化都是權益的文化,任何權益都是文化的權益。”
在馬來西亞,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主體相對應的文化權是各異的。文化權作為價值尺度與認同閾限,它是區分個體人、群體人乃至民族、國家理念的價值尺度。把文化權這個概念及其評判的方法引進華語戲曲研究,無疑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一百多年來在馬來西亞多元文化土壤里,華族對華語戲曲的堅守是文化權的選擇,不僅體現了華族個體人的價值理念與文化認同,而且也是華族群體人價值尺度的評判和認同的表現,從民族的角度而言,更是民族理念的價值尺度。
在華族社會歷史發展的過程中,華語戲曲的功能以及它在各種情勢下的“語境”價值,已經突破了傳統宗教的范圍而在華人社會的各個方面,乃至華人日常生活的世俗化方面呈現出強有力的、多元的穿透力。在現代轉型的過程中,華語戲曲在保持“中華性”的同時,應該處理好傳統和現代的關系,實現自身的革新與豐富,并且著上鮮明的本土色彩,這樣,作為一個頗具代表性的藝術樣式,作為一個顯性的文化事象,華語戲曲才能在馬來西亞華人文化自救的背景下,發揮其應有的積極的作用。
(指導教師:周寧)
導師點評:對于中國來說,戲劇藝術僅僅是藝術,對于全民的社會政治文化生活的影響是有限的。對于東南亞華人,華語戲劇的社會文化功能可能更為寬廣也更為重要。移民社會的生存,面臨著本土與故土、同化與異化的雙重問題:一是同化,如何本土化,在當地獲得合法的政治文化身份,融化到當地社會;二是異化,在多元種族與文化環境中保持自身族群內聚力與文化身份。東南亞華語戲曲演出,經常是民俗節慶祭祀儀式的一部分,酬神娛鬼是馬來西亞華語戲曲最主要的功能,《酬神、娛人與文化權的訴求——多種語境下的馬來西亞華語戲曲》將文化研究的方法與觀念引用到戲曲研究中,考察馬來西亞華語戲曲的宗教文化功能,指出華語戲曲在馬來西亞華人生活中的重要意義,并提出問題:在現代轉型的過程中,華語戲曲在保持“中華性”的同時,應該處理好傳統和現代的關系,實現自身的革新與豐富,在馬來西亞華人文化自救的背景下,發揮其應有的積極的作用。這是一篇在研究領域上有所拓展、研究方法上有所創新、研究問題上有所發現的學術論文,對戲劇學與東南亞區域文化研究、華人移民研究均有重要意義。
[美]明恩溥:《中國人的特性》,匡雁鵬譯,光明日報出版社1998年版。
[蘇]巴赫金:《巴赫金全集》,李兆林、夏忠憲等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趙世瑜:《狂歡與日常:明清以來的廟會與民間社會》,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116頁。
周寧:《東南亞華語戲劇史(上冊)》,廈門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頁。
張云鵬:《文化權:自我認同與他者認同的向度》,社會科學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