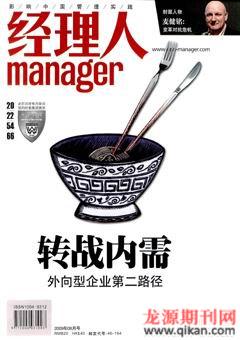劉積仁:穩定成長的關鍵
陳振燁
依靠創新及卓越的運行力,東軟掌控著企業成長的節奏
中國企業終于落回到地面,開始走正常之路。
過去30年,他們走得異常順利,做什么都能賺錢,不僅能賺錢,10%以下的增長或者百分之幾的利潤率,都會覺得太沒勁,太慢,必須要賺快錢。這種心態導致企業對創新產生惰性—不創新都能賺到百分之十幾的利潤,誰還為多掙百分之幾而創新呢?

金融危機讓經濟增長的助推力消失了,創新惰性也隨之被擊碎,不用創新即可賺錢的年代再也不會回來。過去企業有很多選擇,而今天,他們只有兩個選項:活著或死掉。他們被迫開始思考如何創新,如何卓越運行等問題。
日本和歐美經歷的變化,就是我們將來要經歷的。在日本經濟陷入長期停頓,甚至負增長的時候,仍然有很多日本企業獲利,并且持續增長。而這種穩定成長的能力,是絕大多數中國企業所不具備的。
東軟是個例外,在過去18年中,它的成長軌跡很值得我們研讀,它依靠創新及卓越運行,自我掌握著企業成長的節奏,創新浸透到這家企業的各個環節:商業模式、技術研發、國際化進程……是名副其實的穩定成長的推動力,而非口號。
2008年,東軟總收入37.1億元,凈利潤4.91億元,兩項指標的增長分別為10%和18%。東軟集團董事長兼CEO劉積仁對《經理人》說:“雖然遇到金融危機,但2009年上半年的情況,要好于去年同期。”金融危機之下,東軟穩定成長的背后,將給我們帶來什么啟示?
長線戰略
《經理人》:中國經濟幾十年高速增長,使得多數企業習慣了賺快錢,不愿意做長線投資,這種慣性思維今天仍然存在。東軟一直堅持長線戰略,你們從中得到了怎樣的回報?
劉積仁:長線戰略是東軟順利發展到今天的關鍵因素,我們的任何投資都基于長線考慮。東軟從1991年成立,一直到1999年,我們投資了很多基于未來的項目,這些投資是我們今天獲得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也使得我們面對當前的金融危機時感覺很從容。

舉個簡單的例子,我們啟動社會保險系統開發的時候,中國還沒有啟動全面的社會保障系統建設。我們當時判斷,中國不可能永遠沒有社會保障體系,具體哪天到來雖然我們不清楚,但早晚會有。
成功的創新往往都來自于長線投資,短線成功的可能性很小。比如說,現在電動汽車很熱,三五年前做是一回事,今天才開始做是另一回事,沒等你做完,人家產品可能就出來了。
一家可以持續發展的企業,他一定要為未來擔憂,他會思考,現在這種獲利方式,未來可能不會持續。因此,他需要一種新的模式。企業領導者應該用長線戰略去考慮,而非以投機或者短期的心態做事。
《經理人》:根據企業的實際情況不同,長線戰略的適用范圍也將受到限制,在你看來,能保證長線戰略順利執行,并且得到良好收效的關鍵是什么?
劉積仁:長線戰略也意味著給企業帶來更多風險和成本。我們在做長線創新項目時,會為這些項目做適當的“保險”,讓企業不會因為這個風險或失誤徹底失敗。1999年以前,我們做了很多長線項目的投資,之所以敢投入,就是因為我們做好了“保險”。當時我們的國際業務做得不錯,從這部分收入里,拿出1/3投資這些長期的項目,成功當然很好,不成功也對我們造成不了太大傷害。
事實上,我們很幸運,投一個成功一個,第一個是做超級電子檔案系統(SEAS),投了幾百萬,賺回幾千萬;之后做房地產交易管理系統,做電信、電力等行業,都賺錢了。這使得我們對創新越來越有激情。如果因為創新產生的風險,而導致企業死亡,這說明企業還沒有為創新而準備好。
創新不懼風險
《經理人》:企業都知道創新的重要性,對于剛剛“亡羊補牢”的企業來說,他們尚不具備這些能力,東軟在創新能力和創新系統的構建上,都已非常成熟,你們的經驗是什么?
劉積仁:首先要把握好市場的需求,也就是了解未來的市場,做出基本判斷。我們不僅要有創新的理念,還要有一系列創新的策略,使得你的創新結果與別人有所不同。舉個例子,我們的CT機成功打入美國市場,一臺幾百萬元,這個意義,就相當于中國的汽車賣到美國一樣。我們的做法是:先做一個泌尿科的軟件,然后將這個軟件捆綁到CT設備上,再賣給泌尿專科醫院,從而打開了美國的市場。
CT的主要使用者是醫院的放射科,很多公司都在做CT的創新,但是,開發泌尿科的影像輔助診斷軟件,東軟是第一家。我們通過這種創新,制造出市場的差異化,在細分市場里找到機會。另外,在未來的汽車輔助駕駛領域,東軟現在有700人在做技術研發。我們可以做到什么?我們能用比別人更省錢、更快的速度,達到和別人同樣的水平,或者比他們還要好。總結起來就是:了解市場需求,然后制定一個好的創新路線,核心的是有創造性的團隊和人才。
《經理人》:不是每個創新都能獲得成功,對于創新的風險和失敗,你是怎么考慮的?
劉積仁:首先你要認為它值得創新;第二要有好的策略;第三,真有風險也就認了。任何創新都有風險,反過來講,要是擔心風險,就沒有什么創新可言。這么多年走過來,我的感悟是,創新時要想得到大家一致贊成,不太可能,往往反對的人比贊成的還要多。
作為企業領導者,要有勇氣支持創新,也就是說,你要想到可能的失敗,而失敗就證明你做錯了—因為很多人反對過,你還堅持。我們做醫療設備的時候,很多人都反對,因為東軟是做軟件的,把軟件與制造結合,創造一個賣軟件的載體,他們不認為能做成。當時有個跨國公司的負責人到我們公司參觀,我們給他介紹東軟在做CT,他說了一句話,“我不覺得軟件公司能做成這事,如果能成功,軟件公司也去做汽車吧。”他的話很刺激人。但是,要做這些創新,就要承擔相應的風險,要有勇氣挑戰它。事實證明我們最后成功了。
加快服務轉移
《經理人》:去年東軟的凈利潤率大概在18%左右,這個凈利率在行業內屬于什么水平?今年上半年的業績如何?
劉積仁:從今年上半年看,我們肯定好于去年。18%的凈利潤在軟件服務行業,應該是很不錯的,印度企業大部分也都在百分之十幾的水平。但與英特爾百分之二十幾的水平,還有一定差距。
《經理人》:要把凈利潤率再提高的話,應該從哪些方面去突破?
劉積仁:首先要有更卓越的運行能力。東軟的商業模式與其他企業有很大不同,我們還有醫療設備、網絡安全等產品,這些產品的市場份額還不夠大,未來肯定會發生變化;其次是內部的管理和創新;第三是擴大規模,如果規模再翻三到五倍的話,我們的利潤率也會隨著規模效應而變化。
《經理人》:在金融危機之下,很多企業都調整業務模式、企業戰略,東軟有什么改變?
劉積仁:如果說有大的、概念上的調整,就是向服務轉移,我們過去一直在加快服務業務的步伐。服務的收入會越來越高。比如,東軟在醫療服務每年增長都在30%左右,我們賣一臺醫療設備,可以收取一定比率的服務費。有點像賣電梯的,裝了電梯,每年要交保養費。東軟最開始就定位于大的社會基礎行業,像社保、電力、電信、交通、金融等,它們的運行都需要東軟提供服務支持。
敢于超越技術
《經理人》:“關注公司是否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完全超越了技術本身,沒有長遠的眼光,就不會有真正的安全,也不會有真正的技術價值的實現”。我們該如何理解這句話的深意?
劉積仁:當技術變為價值的時候,影響的因素已經遠遠超過了技術。比如,你的市場策略,整體戰略的安排,時機的選擇等等。
消費者對產品會越來越挑剔,他們挑剔是因為市場上同類產品越來越多,假如你要買一個手機,你可能會猶豫半天,搞不清楚哪個更好。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有像iPhone這樣的產品脫穎而出。這就是創新。而iPhone的成功并不完全靠技術,你會發現,有的手機跟iPhone很像,但卻沒人買。這其實已經“超越技術”了。
行與止的智慧
《經理人》:管理大師大前研一曾經評價,說你很擅長中國哲學,“當行則行,當止則止”,過去十多年里,東軟有很多進入其他領域的機會,比如房地產,如何判斷什么該做,什么不該做,你是怎么把握的?
劉積仁:東軟有可能成為世界一流的IT解決方案與服務供應商,但我們沒有信心可以成為中國一流的房地產商。一個企業,不能看到別人賺錢就想去做,如果連自己擅長的都沒賺到錢,不擅長的事情能夠賺錢的可能性更小。這個時代,已經不是可以隨隨便便賺錢的時代了,應該專注一點。
東軟剛成立的時候,大家都在說,要做中國的微軟,做中國的ORACLE,那時候做軟件產品最賺錢,而東軟卻從產品轉型去做服務,現在大家都認為服務是未來,但那時候很多人不理解。我們做國際外包業務比較早,當時的說法:外包是低級勞動,創新才是高級勞動,東軟因為選擇外包業務遇到很多壓力,政府官員說你們應該做創新型企業,競爭對手說東軟沒什么技術,所以做外包。
其實,他們并不知道東軟在做什么,我們做的第一個軟件外包是技術出口,賣我博士論文的理論,這是東軟的第一桶金,我記得當時賣了30萬美元。基于這個理論,我們又開發了一系列軟件產品。對外包服務我們很堅持,上個世紀90年代互聯網很火,大家一哄而上,但我們卻始終沒動。曾經有個韓國的合作伙伴,本來是做醫療設備的,看到網絡比較好,就把錢投進去了,結果死掉了。
《經理人》:在觀察最近一些企業的商業行為中,您認為哪一件事情做得比較明智?
劉積仁:就說中國企業收購悍馬這件事,不論是繼續經營這個品牌,還是再賣掉,我覺得,這家企業首先要知道自己的定位是什么,需要冷靜思考,未來自己要成為一種什么樣的企業,然后再據此進行戰略的部署。
附文:
劉積仁的并購原則
前不久,東軟欲并購大連華信,引起業內振動,但最后關頭,并購被終止。劉積仁表示,東軟會繼續尋找新的并購對象。“我們的并購原則是,被并購方感覺到很有必要。我們不是買一個不得不賣給我的公司,而是買一個高高興興想賣給我們的。賣公司的是股東們,但公司未來要靠那些員工。要讓他們覺得與東軟合作,對他們未來的生活和家庭會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