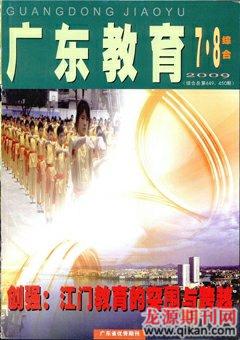裹著烏煙的火焰
沈文新
七十年代:孔老二、“五七干校”、哥德巴赫猜想、恢復高考、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反潮流、張鐵生、工農兵學員、一顆紅心兩手準備……七十年代:孔老二、“五七干校”、哥德巴赫猜想、恢復高考、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反潮流、張鐵生、工農兵學員、一顆紅心兩手準備……
“往事并不如煙。”在我看來,像恢復高考這樣的往事,應該是一截截濕木頭上燃出的火,始終搖曳著被烏煙裹著的熾熱的火焰。比如我,這心里就一直有一截濕柴燃燒在那個年代的冬天。
1977年的冬天,我剛滿15歲,已經高中畢業回鄉務農。因為是“黑五類”子女,我要以一個成年勞力的身份,整日在冬修水渠的工地上用雞公車推著石頭,從天剛麻麻亮推到天又麻麻黑。每天回到家里,懶得洗澡或洗腳就一覺睡去,沒有夢,甚至連呻吟也沒有。但是有一天,聽到恢復高考的消息時,我卻在精疲力竭的黃昏中哼著歌兒小跑回家,又在自家小窗前的寒風中站到雞叫頭遍。現在想來,那時的我,仿佛看見梵高的“星夜”就在頭頂。我像一棵火焰般的白楊,張望星空,而星空涌流起巨大的漩渦。是社會的巨變讓我興奮得有些昏眩了,還是壓抑太久的渴望在打開閘門之后涌向遠方?我不知道。
第二天上午,我仍然到工地上推著石頭。有個老頭說:“知青們都去高考了,你是不是不考呢?”我急切地說:“考!”他彎下腰盯著我的臉看了又看:“你行嗎?腦殼沒發暈吧?你政審過得了關嗎?”我愣了一下,知道自己是右派的子女,但我又想起父親前不久的一封信,他在信中難掩喜悅地說,很快就會得到平反昭雪了。而且有知青告訴過我,這高考是“自愿報名,嚴格考試,擇優錄取”,現在已不是論階級成分的時候了。即使要政審,巴掌上的老繭是工農兵上大學的最好條件。于是我舉起巴掌自審了一下,得出結論:我有兩手老繭,應該合格!忽然,大隊書記來了,我靈機一動,用兩手捂住肚子,非常痛苦地說:“我肚子好痛,要請個假去看醫生。”書記詭秘地一笑,出乎意料地說了聲:“去吧!”我立即給他行了個九十度的鞠躬禮,直奔一里路遠的衛生院。
高考考場設在衛生院背后的小學里。當我氣喘吁吁地趕到考場時,看見許多人像我一樣從四面八方跑來,我狂喜地松了一口氣。但當報名之后要進考場時,我腦子里忽然一片空白,像個局外人似的,對許多人趕考感慨不已。以至于許多年后,每想起那情境,我都覺得那也是梵高的杰作,《麥田上空的烏鴉》。考場是金黃的麥田,在傾斜的天空下,我們這狂奔而來的考生,有哪一個不像奮飛的烏鴉呢?其實,現在想來,當時的考生更像周濤筆下的鞏乃斯馬,在冬夜的雪原上奔馳,在夏日的暴雨中狂奔。前者釋放出壓抑太久的渴望,后者揮灑著獲得自由的激情。我意識到,這無疑是一個歷史的拐點,新的一切才剛剛開始。我對自己說:不怕,這次考不好,還有下次呢。
1978年的春天,我在代課,高考又到了。不幸的是,我鼻炎發作,校長恩準我去公社的衛生院急救。感謝上帝,那考場就在醫院的背后,讓我得到機會一邊“急救”一邊考試。考后有點兒欣慰,感覺不少題都不是太難呢。后來盡管落榜且又不知考了多少分,我堅決地拒絕了父親平反昭雪后可安排子女的機會,并且堅定地認為,走了高考的大道,才是走了金光的大道。
1979年春節剛過,讀書的念頭讓我耐不住了。正月十五的傍晚,我離家,走過屋前的池塘,聽到隊長和幾個鄰居說:“他這一去,回來只有一條路好走:投水自盡。池塘是沒有加鍋蓋的。他不再是生產隊里的社員了。”我于是朝池塘惡恨恨地呸了一口,揚起頭走入不遠處的茶樹林,轉彎遠去。我去縣文教局局長家里,請他給我開個條子到臨近公社的一所高中插班。局長居然毫不猶豫地同意了我的要求:“難得呢,好好去讀吧!”我欣喜若狂地溜回家來,雞叫時到屋前秧田里扯了可掙一天工分的秧,就兩腿泥巴地挑了一個老木箱悄悄離去。我聽見80歲老外婆顫動的喊聲從里屋傳來,我沒有停留,只小聲應了一聲:“外婆你保重,我走了。”我在心里發誓:我不會回來了,即使投水,我也要投到外面的大江大海里去,那里才是我葬身的地方。
可恨蒼天啊,插班兩個多月時,學校在頃刻間化為一堆廢墟。一場史無前例的龍卷風,夾著昏天黑地的大暴雨,差點刮走了我的全部夢想。大禮堂沒了,學校沒了,有什么辦法呢?師生們仍然在狂風暴雨下的殘垣斷壁中,挪動著高考復習的腳步:堅持學習!堅持學習!餓了,喝幾捧冷水;再餓了,吃一把油菜或青草,默記著資料和題目……這一年高考,我以三分之差而落榜。而現在想來,我仍然感到欣慰。正是這時,命運讓我強烈地感到,普天之下,還有千千萬萬個青年跟我一樣,他們都在與命運抗爭,我又有什么理由退縮、悲嘆呢?
第二年,我終于從這條險象環生的高考之路走出去了,走遠了,以至為同輩甚至后輩樹立起一個既光輝又可怕的榜樣。此后,我所在的十里八村,一個又一個像我一樣的青年,決意要跳出農門,于是學我,要在高考的考場上走出去,于是復讀了一年又一年。但可憐那個年代的青年人啊,只有張鐵生交白卷的榜樣,有什么準備呢?有什么東西可考呢?除了極少數的幸運者考出去,他們有的最終考倒在病床上,有的考進了精神病院里。這教我心里的一截濕柴又如何不永遠燃燒在那個年代的冬天呢?
好在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
自從恢復高考之后,我們就經常聽到人們津津樂道于某人家貧,但孩子考上了大學;某村的讀書風氣好啊,一村子就考上了那么多大學生。孩子考上大學的家長,不論其地位如何卑微,家庭如何貧困,總會得到鄉鄰親友的羨慕和尊重。而小平倡導的“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風尚,便在這種羨慕和尊重的日子中深入人心了。于是人們相信,中華傳統的貴族之氣算是得到了復活,得到了拯救。
1977年以前,在廣大的農村,許多人無法上學,永遠埋首于土地;而能上學的,沒有大學可考,即便高中畢業,最多也不過到達縣城,不知外面還有更遼闊的世界。但在1977年冬天之后,許多人忽然之間便發現了一條通往外部世界的路,這條路人人可走,就在腳下,靠的是自己,這便使老百姓重建起一種寫著“公平”的理想和信仰。
今天,面對“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高考景觀,有的人憤怒于這橋的狹窄,叫喊著要趕快撤橋,有的人空談于這橋的未來,虛妄地等待重建,可現實畢竟是現實。他們想不到,這獨木橋正如足球場上的球門,因為每個人都想把自己腳下的球踢進門去,所以才培育了一種最大強度的競爭意識——獨木橋孕育了這競爭的時代。
考試起始于隋朝,成形于唐代,盛行于明清,但考試自身的功能古今一律。譬如考試的評價功能、選擇功能、診斷功能、德育功能等,在教育中,特別是在學校的教育中,不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都不可缺失。考試在十年浩劫中缺失了,教育或學校就亂了,人才就出不來了。1977年的恢復高考,其實是在重建一種教育的秩序和理想。有了這種教育的理想和秩序,我們的教育才步入正軌,培育人才的列車才加速前進,走過輝煌的三十二年。在人類文明的長河中,這高考也許算不了什么,它只是一串浪花,免不了撞上礁石;在我心里,它只是一截濕柴上燃出的火,免不了裹著烏煙。但浪花只要顯示著河流的生命,木頭只要始終搖曳著熾熱的火焰,也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