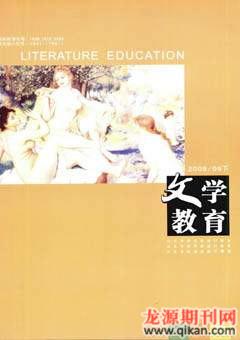論葉梅土家族文化小說的情感關照
黃 萍 楊 齊
90年代以來,葉梅發表了如《撒憂的龍船河》、《花樹花樹》、《回到恩施》、《五月飛蛾》、《山上有洞》、《最后的土司》等一系列以恩施境內清江和長江三峽流域的土家人生活為背景的中篇小說。在這些小說中,她用詩意的筆調描寫了土家人的現實生活和歷史變遷,敘述了大量土家人的歷史傳說、英雄故事、現實斗爭以及與漢族等兄弟民族的交往,展現了土家人獨特的生存狀態、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精神。可以說,這些作品“很大程度上構成了土家族民族精神與民族性格的雕像或土家族民族、歷史、文化的亞文本”①。本文試從作家情感關照的角度對其作品進行解讀。
一.情感關照的源起
情感作為文學藝術的永恒元素,很早就被人類發現。《毛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朗吉努斯在《論崇高》中說:“我要滿懷信心地宣告,沒有任何東西像真情的流露得當那樣能夠導致崇高;這種真情如醉如狂,涌現出來,聽來猶如神的聲音。”可見,情感與文學是密不可分的。沒有真實的情感,就不會有好的文學作品。葉梅所創作的土家族文化小說,就是情感與文學緊密聯系的代表。
土家族生活在長江三峽流域的崇山峻嶺之中,是古代巴人的后裔。鄂西獨特的地域生活背景與歷史文化鑄就了土家族強悍勇武、多情重義、豁達豪放、堅韌耐勞、忠厚耿直的民族品格和文化品性。土家人繼承了巴人“重巫信鬼”的宗教習俗,其巫教文化也相對發達。葉梅是從恩施走出去的作家,她成長在土家族的文化母體之中,她的成長歷程深深地烙上了土家族歷史文化與現實生存狀態的烙印,她的情感已經與這片土地、這片土地上生存的土家人、以及這片土地的歷史、文化、民俗等方方面面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不可分割。這種不可割舍的情感,不自覺地便融入了作家的創作過程之中。她將自己的創作深深根植于對土家族歷史文化與現實生活的之中,以深沉、理性的情感來思考歷史,以抒情、詩意的筆觸來描繪自然,以細膩、溫婉的風格來描寫人物,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出了土家人的民族性格和文化精神。
二.情感關照的體現
情感是民族心理的重要內容。葉梅從小生長在鄂西山區,蜿蜒狂野的龍船河、神秘蒼茫的野三關、古樸自然的吊腳樓,勇武剛烈的土家漢、熱情專一的山妹子,都傾注了她自然而濃郁的情感。在她的視野里,“那山、那水,一根竹管,一朵山花,一泓泉水,都化作了一種情緒;那船夫,那山漢,那村姑,那阿太,不再是時髦的符號,而是作家心血、機智和情感的流淌。”②
一是對自然景觀的情感關照。從葉梅的小說描寫中我們可以看出,土家族生活的環境是艱苦的,卻也有著讓人難以忘懷的美。她在《撒憂的龍船河》中這樣描寫龍船河:
那河面二十里,起源于龍船寨頭一處無名山洞,沸騰泉水在苔蘚密布的石洞之外積成深潭,繼而跌宕出三道百丈懸崖,蜿蜒九灘十八彎,依次經過苦竹、夫妻、老鷹三峽,最后匯入長江。那河看是纖細實際奇險刁鉆,河上礁石如水怪獠牙猙獰參差不齊,水流變幻莫測,時而深沉回旋織出串串漩渦,時而奔騰狂躁如一束束雪青的箭簇。③
而《回到恩施》中的野三關是這樣的:
恩施一帶的山巒可以說奇妙無窮,如果現在的人們對湘西的張家界有所認識的話,那么不妨以張家界為參照做一些比較,處在鄂西的野三關更為渾厚蒼茫更為神秘粗野,山間的小徑總是若有若無,不時被糾纏不清的藤蔓所阻礙,當你好不容易鉆出一片密林,面前不是豁然開朗,相反倒是一面筆直陡峭的石壁或是一道洶涌的小溪。④
這些自然景觀,無不真實地展現出了恩施土家族惡劣的自然生存環境。正是這樣的環境,才造就了土家人在改造自然中無畏的勇氣、樂觀的態度和不屈的精神。當然,恩施土家人的生活環境除了神秘險峻,也有溫婉如畫的一面,如《廝守》中的“清江”:
端的好所在。一明兩暗三間瓦房背靠青山,面對綠水,竹林環繞,門前一塊平整的場壩,又栽種些柑桔葡萄,異香襲人,蝴蝶蜜蜂亂飛。眺目四望,山川寥廓,零星炊煙如云似霧,卻是相去甚遠。
靜謐之中,尚有峽谷波濤奔涌,激起潺潺水聲。門前就是一條江。
那江名字好美——清江。
寥寥數語,清江的秀美、土家人生活的恬淡自然變展現在了我們眼前,令人神往。這種看似信手拈來的描寫,實則是源于作家對這片土地,對這些山水的了若指掌和深深熱愛。
二是對人文景觀的情感關照。在《撒憂的龍船河》中,龍船河上的“豌豆角”、在陡峭巖壁上天人合一的“裸體纖夫”,《黑蓼竹》中的“咚咚喹”,還有不時在山谷間飄蕩的《龍船調》……都是一幅幅反映土家人生存狀態的人文景觀。這些人文景觀,在葉梅的筆下卻是那樣的讓人難忘。土家人是勇敢的。在《撒憂的龍船河》中,秦老大一家三代都生長在龍船河邊,他們駕著“豌豆角”在奇險刁鉆、桀驁不馴的龍船河上行船謀生,在這條時時有生命危險的河流上,他們不僅要有戰勝自然的勇氣,更要掌握好在峽江上往來自如的“走豌豆角”本領,從秦老大一家三代身上,我們不難看出土家人挑戰自然、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勇氣和能力。土家人是多情的。《五月飛蛾》中的二妹對愛情的堅守和敢于爭取,《最后的土司》中的伍娘用生命的舞蹈來詮釋對愛情的追求,《回到恩施》中的譚青秀對愛情的大膽與主動,《撒憂的龍船河》中巴茶在土家女兒會上大膽追求秦老大……這些熾熱而純潔的情感描寫,無不展現了作家對土家兒女熱情剛烈、多情重義的精神品質的禮贊。
三是對民俗風情的情感關照。相傳巴人祖先依靠神力取得了權力,逢山開路遇水搭橋,定居在這片山清水秀充滿靈性的土地上,死后化為白虎,所以土家人信奉鬼神,以白虎為圖騰,形成了獨特的風俗文化。土家族民俗活動較多,如跳喪(撒爾嗬)、女兒會、舍巴日、哭嫁等等。葉梅的《撒憂的龍船河》中有這樣的描述:
跳喪跳了幾千年。
土家人對于知天命而善終的亡靈從不用悲傷的眼淚,顯然知道除非兇死者將會長久徘徊于兩岸之間,一切善終的人只是從這道門坎跨入了另一道門坎,因此只有熱烈歡樂的歌舞才適于送行,尤其重要的是在亡人上路之前撫平他生前的傷痛,驅趕開在人世間幾十年里的憂愁,讓他煥然一新輕松無比地上路。這是一樁極大的樂事。⑤
讀《撒憂的龍船河》,我們能夠深深感受到土家人豁達的生死觀。從《最后的土司》中我們可以了解到,春分時節“舍巴日”是一年中最隆重的祭祀,作家用濃墨重彩的筆觸細細描繪,那滾雷似的三道鼓,梯瑪的八寶銅鈴舞,眾人“舍巴日”的吶喊,火焰般燃燒的舞蹈令人感受到土家人獨特的民俗風情。《黑蓼竹》中的“咚咚喹”奏起時,時而如翠鳥啼叫,時而如錦雞在紛飛的白雪中踏走,時而如江河奔涌于峽谷……每當“咚咚喹”響起,便會引起吳先生心中那濃得化不開的鄉愁和對竹女的無限相思。這些民俗文化生動地展現在葉梅的土家族文化小說之中,無不體現出土家人精神世界的悲愴和剛烈。
三.情感關照的憂思
土家族是我國一個歷史悠久的少數民族。數千年來,土家族不僅在艱苦卓絕的惡劣自然環境中不斷發展進步,鑄就了勇敢剛強的民族性格,而且還構建起了獨特的民族歷史文化。葉梅作為從小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土家族女作家,她對這片土地,對這片土地上的父老鄉親有著無法割舍的深厚情誼。對這片土地上的民族文化的變遷,葉梅也有著獨特的思考,其中有守望,也有批判;有發掘,也有憂思。
土家文化與外來文化的沖突,首先發生在《最后的土司》中。小說通過講述土司覃堯、外鄉人李安與伍娘三人的恩怨情仇,從而深刻揭示了外來漢族文化與封閉自足的土家文化的矛盾沖突。而在《山上有洞》中,作家運用電影蒙太奇及交錯敘述的手法,將土司戰爭、紅色革命以及當下土家青年進城打工奇妙地組合在一起,展現了近三百年土家人的生存命運與時代演變。而在《五月飛蛾》中,城市化、現代化如明亮的火焰招引和誘惑著像“二妹”這樣的鄉村青年,他們如撲火的飛蛾義無反顧地涌入城市以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進入城市之后才發現這里并不是外來闖天下者的天堂,拜金主義、道德滑坡等現象已經難以逆轉。鑒于現代文明的嚴重缺失,葉梅希望通過自己的小說創作為人類的精神建構貢獻一份微薄之力。土家人剛烈勇武、多情重義、豁達坦蕩等民族性格與文化精神,正是葉梅發掘來尋找救治現代文明弊端的某些有用的活性資源。
讀葉梅的小說,我們不僅能感受到土家人獨特的生存環境和民俗民風,推崇自然、豪放豁達的生命意識,更能感受到在土家族文化與外來文化的沖突中葉梅對本民族文化的鐘情與堅守,她已經將情感關照的觸角伸展到了土家族文化的歷史與現實之中,也延伸到了對整個社會和整個民族的現代文明的思索之中。從這個意義上說,葉梅土家族文化小說的情感關照,對于挖掘土家族優秀的民俗文化價值,探索治療現代文明的弊病,有著十分深遠的意義。
※ 說明:本文系2007年湖北省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民族文化研究項目古代巴文化與鄂西民族文學研究、2009年湖北省教育廳人文社科研究項目鄂西民族文學的巴楚文化解讀及其發展策略探討(項目編號2009y096)、2009年湖北省教育廳人文社科研究項目當代鄂西南小說與民俗文化研究(項目編號2009y097)成果。
參考文獻:
①吳道毅:《尋索土家族文化的秘密——論葉梅的土家族文化小說》,《民族文學》,2003年第5期;
②張守仁《鄂西無處不是情——關于葉梅的小說》,《最后的土司》第247頁-248頁,長江文藝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
③《最后的土司》第4頁,長江文藝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
④《最后的土司》第211頁,長江文藝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
⑤《最后的土司》第9頁,長江文藝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
黃萍,湖北民族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教授;楊齊,甘肅定西師范高等專科學校中文系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