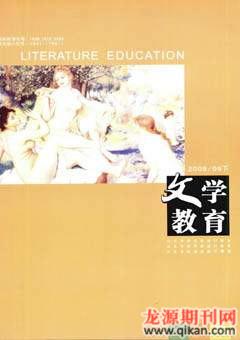嬰寧與子君之比照
李利民 李窗影
一
嬰寧是蒲松齡筆下的女性形象,子君是魯迅筆下的女性形象。在兩個人物身上,分別注入了兩位偉大作家對愛情的思索和向往。兩個女性的時代和命運雖說頗不相同,但在她們身上卻顯示著共同的愛情傾向——對浪漫情調的關注。有趣的是,兩位作家都將自己筆下女主人的愛情命運與她們對待花的態度關合在一起。
嬰寧純潔活潑,巧笑倩兮。她的浪漫個性可以說是從花蕊里涵潤出來的。她從小就生活在嬌花嘉木的山谷之中。她的小村落處在叢花亂樹中;她的門前皆絲柳,墻內桃杏尤繁,間以修竹,野鳥格磔其中;門內夾道紅花,片片墜階上,豆棚花架滿庭中;窗外海棠枝朵,探入室中。她的伴侶小榮,也愛花,這種真情在不經意的舉止間無可置疑地展露了出來:“由東而西,執杏花一朵,俯首自簪。舉頭見生,遂不復簪,含笑拈花而入。”她們兩個小精靈之間,談的也通常是花,如她拜會王子服之后,顧婢(小榮)曰:“視碧桃花開未。”嬰寧在花兒的陪襯中滋長,她的甜美,就是花兒釀出的蜜漿;她的巧笑,就是花兒綻放的容顏。
嬰寧與王子服的愛情歷程就是浪漫之旅。他們首次相遇頗富情調。在一個上元漫游的日子里,“有女郎攜婢,拈梅花一枝,容華絕代,笑容可掬。……遺花地上,笑語自去。生(王子服)拾花悵然,神魂喪失,怏怏遂返。”這位女郎就是嬰寧,梅花雅韻與絕世容華相映成趣,展現著勾魂攝魄的風姿,攝取了王子服的神魂。
嬰寧與王子服的再次見面,是在嬰寧的家。在這里,絲柳桃杏,修竹野鳥,豆棚瓜架,紅花夾道,海棠入戶,清雅浪漫之趣,沁入王子服的心脾。第二天,王子服向嬰寧傾訴衷情是在嬰寧家的后花園:“細草鋪氈,楊花糝徑;有草舍三楹,花木四合其所。(王子服)穿花小步,聞樹頭蘇蘇有聲,仰視,則嬰寧在上。”嬰寧呆在花園中,花草彌望尚嫌不足,還趴到了花樹上。其愛花若此。接著,王子服以上元節嬰寧所拈梅花為媒介向嬰寧表達情意。可以說,他們從以花相識,走向了以花相愛,敷衍了一曲“花為媒”。
更為難得的是,嬰寧與王子服成婚以后,愛花之癖,益甚于前。她為得奇花異草,尋遍四鄉八黨,遇到嘉卉,竊典金釵也要購來。不久,就像那位走到哪里就將哪里變成清雅的竹園的王徽之一樣,王子服家也被她美化成了花的世界。
再看看子君。她與涓生戀愛時,原是頗講究浪漫情調的。涓生心里刻印著當初她那使自己生動起來的形象:她“帶著笑渦的蒼白的臉,蒼白的瘦的臂膊,布的有條紋的衫子,玄色的裙。她又帶了窗外的半枯的槐樹的新葉來,使我看見,還有掛在鐵似的老干上的一房一房的紫白色的藤花。”這是一幅多么清純浪漫的畫面。
然而結婚以后,“她并不愛花,我(涓生)在廟會時買來的兩盆小草花,四天不澆,枯死在壁角了,我又沒有照顧一切的閑暇。然而她愛動物,也許是從官太太那里傳染的罷……”
嬰寧和子君對待花的不同態度,導致了她們不同的愛情婚姻命運,嬰寧幸福美滿,子君卻在無愛中走入了無碑的墳墓。
二
浪漫是一種雅致,嬰寧愛花,她的笑就像花一樣的燦爛,“笑處嫣然,狂而不損其媚,人皆樂之”,因為有花一般的雅致,狂笑也顯出嫵媚,叫旁人見了喜歡。
浪漫是一種熱情,嬰寧愛花,她的笑像花一樣的熱烈,感染著周圍的人,“滿室婦女,為之粲然”。
浪漫是一種巧慧,嬰寧欣賞花的精美,她不僅容貌如花,而且心靈手巧,“操女紅精巧絕倫”,就像《繡枕》里的張媽所說:“那頭面長得俊的小姐,一定也是聰明靈巧的。”(凌叔華《繡枕》)
浪漫是一種純潔善良,嬰寧愛花,有著花兒般的純凈柔婉。她同情“明月夜,短松岡”的老母孤魂,于是鄭重其事地請求王子服將老母與老父合葬。她的柔婉,使罪婢感到依賴,使婆婆拋開前嫌,變得豁達:“奴婢小過,恐遭鞭楚,輒求詣母共話;罪婢投見,恒得免”。
浪漫是一種純真。嬰寧愛花,性情如花一般的貞潔,她以臨近西家的一架木香樹為背景,懲治邪淫,捍衛自己愛情的忠貞。
嬰寧愛花,她以浪漫純潔的性情贏得了幸福的婚姻生活。她面對丈夫傾訴在夫家受到的感情待遇:“今日察姑及郎,皆過愛而無異心”,婆婆和郎君都喜愛她。她的嬰兒,“抱在懷中,不畏生人,見人輒笑,亦大有母風云”,就像開在她胸間的一朵小花。她的婚姻生活呈現著一派和諧溫馨的氣氛。
然而,浪漫情調在子君身上卻沒有得到堅持。
子君是五四時期得風氣之先的女性,追求愛情的自由。她與涓生戀愛時愛花,與涓生談著的也是浪漫的話題,諸如男女平等、泰戈爾、雪萊,連同她那“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的勇敢的愛情宣言,都曾使涓生驟然生動起來。
不幸的是,庸俗成了浪漫的殺手,婚姻成了愛情的墳墓。
浪漫是一種爛漫色調,失掉了它,生活便失去光彩。婚后,子君不再愛花,她任憑涓生買來的花枯死。“然而,她愛動物,也許是從官太太那里傳染的罷,不一月,我們的眷屬便驟然加得很多,四只小油雞,在小院子里和房主人的十多只在一同走。但她們卻認識雞的相貌,各知道哪一只是自家的。還有一只花白的叭兒狗,從廟會買來,記得似乎原有名字,子君卻給它另取了一個,叫做阿隨。我就叫他阿隨,但我不喜歡這名字。”“傍晚回來,常見她包藏著不快活的顏色……幸而探聽出來了,也還是和那小官太太的暗斗,導火線便是兩家的小油雞。”“(子君)管了家務便連談天的工夫也沒有,何況讀書和散步。”她不再向槐樹葉和藤花訴求情調,而是仿效官太太養寵物;她不再意識到“我是我自己的”,而是覺得“阿隨”應該受她控制;她不再談男女平等的理想,而是掌握著識別油雞以及與官太太吵架的能耐。
浪漫是一種心靈的解放,有了它,心靈就有余力從愚昧走向自覺。“子君的功業,仿佛就完全建立在這吃飯中。吃了籌錢,籌來吃飯,還要喂阿隨,飼油雞;她似乎將先前所知道的全都忘掉了,也不想到我的構思就常常為了這催促吃飯而打斷。即使在坐中給看一點怒色,他總是不改變,仍然毫無感觸似的大嚼起來。”子君丟掉了浪漫,也便失掉了自我反省的余力,言行自然也就變得粗俗和蒙昧起來。
浪漫是生活的減壓器和潤滑劑。子君丟掉了浪漫,外界的壓力一旦掩來,她的精神力量便頃刻被摧毀。“我真不料這樣微細的小事情,竟會給堅決的、無畏的子君以這么顯著的變化。”當生活的艱辛和涓生的失業向她壓迫過來時,她變得脆弱、沉默、冷漠、感傷。
浪漫是對庸俗的強勁反作用力,子君失掉了浪漫,陷入庸俗的泥潭不能自拔。“只是吃飯卻依然給我苦惱。菜冷是無妨的,然而竟不夠;有時連飯也不夠,雖然我因為終日坐在家里用腦,飯量已經比先前要減少得多。這是先去喂了阿隨了,有時還并那近來連自己也輕易不吃的羊肉。她說,阿隨實在瘦得太可憐,房東太太還因此嗤笑我們了,她受不住這樣的奚落。”因為深深陷進了庸俗的泥潭,視線模糊,心智昏聵,維護狗的虛榮已經勝過了維護丈夫的身體。
子君忘掉了浪漫,她與涓生之間的愛情失去了色彩和生命力,不久便在無愛的人間走盡了自己悲哀的人生。
三
嬰寧、子君,二位女性所處的時代不同,所經歷的愛情命運也不同,但是,她們的不同命運卻顯示著共同的意旨——浪漫是愛情的防腐劑,浪漫的愛情婚姻是美妙的、富于生機和色彩的。
其實,這是一個永恒的愛情主題。《紅樓夢》第五十九回中賈寶玉的幾句話,曾經引起了多少人的心靈共振,他說:“女孩兒未出嫁是顆無價寶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變出許多不好的毛病兒來,再老了,更不是珠子,竟是魚眼睛了。分明一個人,怎么變出三樣來。”我們且看春燕引用寶玉這話時對它的理解:“這話雖是混帳話,想起來真不錯。別人不知道,只說我媽和姨媽他老姐兒兩個,如今越老了越把錢看的真了。”(曹雪芹《紅樓夢》第五十九回)在賈寶玉看來,凡女兒個個是好的,女人個個是壞的。由女兒變為女人的轉捩點便是嫁漢子,作風便是由清純浪漫變為渾濁庸俗。其實,在女人身上,浪漫的喪失和庸俗的滋生并不具有宿命性。浪漫是對自己心靈的欣賞和堅持,庸俗則是對世俗環境的沉溺和依附。只要具備了生活的基本條件,生活的壓力與浪漫的喪失就并無必然的對應關系。婚前,子君愛花,她成為了一位“我是我自己的”主人;婚時,她賣掉首飾添置家資,為的是繼續做愛情自由的主人;結婚之后,她“也逐日活潑起來”,但“并不愛花”,而是學著官太太養叭兒狗和小油雞,可以說是賣了首飾,買來了對花的冷漠。這時的子君,是自甘選擇了庸俗,她沒有成為自身的主人,而是成了環境的奴隸。然而,嬰寧不僅婚前愛花,就是在婚后,她也竊典金釵,求購嘉花異卉,用浪漫的心靈美化環境,真正成了自己和環境的主人。嬰寧真乃奇女子,她的典釵購花,巾幗罕見;然而,她幸福美滿的愛情婚姻生活,亦可謂巾幗罕見。
李利民,男,中國文學博士,武漢工程大學外語學院副教授;李窗影,女,武漢洪山高中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