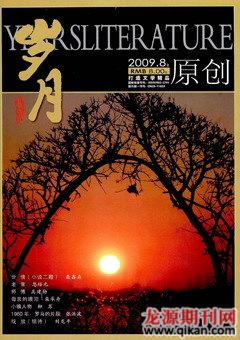中國網絡詩歌前沿佳作評賞
簡 明
王征珂的詩歌,高度體現了詩人繁入簡出的語言智慧和高度概括能力。王征珂的詩歌充分而巧妙地運用了文字的減法功能,無論是《烏托邦》、《龜兒子》,還是《我們的愛情》;也無論表達智性、構篇智性,還是詩人的情感智性,無不顯示出他深厚的文化底蘊、扎實的與生活相對應的藝術表現力,以及對生命、對漢語表達功能的挖掘潛能。總之,王征珂以智者的面貌出現,以智者的口吻說話,以智者的手段玩弄文字游戲,是比較得心應手的。王征珂詩歌給了他智者的印證和人格識別符號。盡管他有些懷才不遇情結——這是非詩年代的文化常見病;盡管他有些玩世不恭——這是非詩年代詩人的常規武器。
常規武器實際上是一種“日常操守”或生存之道,它不像潛規則,被少數人奉行,而讓多數人不恥或“找不到北”:常規武器是“陽光”下的戰術,是“國際公約”下的領土,是“血緣傳承”下的倫理道德。比如男人和女人:女人的常規武器是舌頭,男人的常規武器是拳頭。比如飛禽走獸:鷹的常規武器是飛,豹的常規武器是跑,豬的常規武器是,懶得飛也懶得跑。
英國詩人柯勒律治說:“詩是一種以獲得智力上的愉快為目的的藝術品。”王征珂這組詩,以隱喻與智趣構成,節奏輕松自然,立意別有用心,味道與眾不同。比如《我們的愛情》,看似游戲口吻,細品則妙趣橫生:我們的愛情/尼姑正在上山/我們的愛情/和尚正在化緣/遇到了芳香的主人/桃花桃花長著人面/。
王征珂詩歌在游戲之間,藏有極強的隱喻性。隱喻為西方美學概念,智趣乃中國詩學理論獨有。明朝高啟說:詩之要有三:格、意、趣。格以辨其體,意以達其情,趣以臻其妙(《獨庵集序》)。
《龜兒子》的詩題,就是一個旗幟鮮明的譏諷,就是一個鞭撻和唾棄的象征:這塊石頭腆著/官僚主義的肚皮/它在斯的花天/和斯的草地之間/又吹胡子又瞪牛眼/好像我欠它/八百兩雪花銀/當我騎上它/原來它也會/變成一個龜兒子。又如《烏托邦》的立意深藏不露,是一首胸懷天下的“大詩”;看似荒誕,其實內力暗涌:而雪水就是奶水/在那潔白的胸脯上/匍匐著一個乞丐/紙張太容易破碎/而我太容易感傷/我的日子就像/野狗一樣“汪汪”/。美可以直觀感受,自嘲與反諷,辛辣的幽默,進退自如的風趣,則需要滲入大智大悟和膽識。
網絡真是一個奇妙無比的游戲平臺,它解決了大眾文化語境下,詩歌傳播、互動、反饋等問題卻缺乏有效的過濾機能,魚龍混雜,如同假面舞會,你盡可扮作上帝、牧師、軍官、水手、乞丐、貴婦或者妓女。舞臺是公共的,狂歡是隨心所欲的。曲盡人散時,也許妓女搖身一變,成了上帝;也許上帝淪落成了妓女。一切皆有可能,這就是游戲的魅力。
游戲精神是詩歌的第二重天,這絕非虛張聲勢,或標新立異;詩歌是傳統精神的繼承者。這是第一重天;同時,詩歌又是傳統精神的破壞者,這是第二重天,兩者是辯證統一的。李白的“白發三千丈,緣愁似個長”,憑空而來的“白發三千丈”,極度奇妙的夸張。李白的身度,據他在《上韓荊州書》中自我介紹:“長不足七尺”,而這三千丈的白發,是內心愁緒的象征。“北方有佳人,一笑傾人城,二笑傾人國”,同樣奇妙的夸張。游戲精神不單指在語言傳統邏輯上的大逆不道,更重要的是指精神境界上的大逆不道。
“目及其物,以心擊之”(王昌齡)。詩人的真實,詩人眼中的真實,是更高意義上的真實——真實是最容易辨析、認同和引發共鳴的。
王征珂的詩
烏托邦
我想起了那些遠去的
風景楊柳總是披著
朦朧細雨的衣服
而雪水就是奶水
在那潔白的胸脯上
匍匐著一個乞丐
紙張太容易破碎
而我太容易感傷
我的日子就像
野狗一樣“汪汪”
一個戀月癖患者
趁夜深人靜
偷運滿天白銀
運往烏托邦
龜兒子
這塊石頭腆著
官僚主義的肚皮
它在斯的花天
和斯的草地之間
又吹胡子又瞪牛眼
好像我欠它
八百兩雪花銀
當我騎上它
原來它也會
變成一個龜兒子
我們的愛情
我們的愛情
尼姑正在上山
忘記了庵中的叮囑
把一團雪光含在口里
我們的愛情
和尚正在化緣
遇到了芳香的主人
桃花桃花長著人面
我們的愛情
鵝毛在加速堆積
鵝毛大雪紛飛
但不是傷心的哭泣
我們的愛情
白晝穿著迎風的枝椏
我們的愛情
黑夜穿著窗外的白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