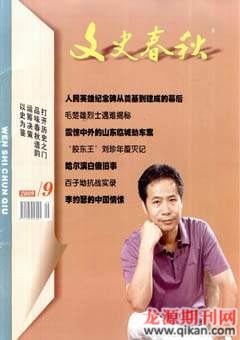海南讀史雜記
張森奉
去年金秋,我到海南各處游覽,深深為海島的椰風綠韻、碧海藍天以及特區的高樓大廈所吸引,期間走訪了一些名勝古跡,頗有感觸,遂寫雜記數則,作為紀念。
蘇公祠里想蘇軾
在海口游五公祠時,發現與此緊緊相連的還有蘇公祠,不禁興致勃勃。相傳蘇軾(字子瞻,號東坡)被貶來海南后,曾在此寄宿,誦讀詩書,指導居民開鑿雙泉,命名為“浮粟泉”,題泉上亭名“洞酌亭”。此處南宋時就留下了“東坡讀書處”的遺跡,元代改為“東坡書院”。院內修祠,供東坡畫像,陳列蘇東坡在海南的事跡,名“蘇公祠”。
《瓊臺記事錄》中說:“宋蘇文忠公之謫儋耳,講學明道,教化日興。瓊州人文之盛,實自公啟之。”蘇軾在海南作出的最大貢獻是傳播文化。可見一個人做了好事,人民是不會忘記他的。
我曾通讀蘇軾在海南時所作的詩文,感到他在這里所作的詩,都較以前少了銳氣,少了朝氣,也少了才氣。原因無他,這是處于高壓威懾及一貶再貶的打擊下才會如此的。
他在海南所作的詩中,常流露生活的愁苦凄慘、處境的孤獨寂寞,即使有的詩顯露出豁達樂觀的情趣,也使人感到是笑中含淚。人們常說宋詩不如唐詩。蘇軾是大文豪,才華與抱負決非不如李白、杜甫與元稹、自居易,只是宋朝文禁嚴厲、文字獄多,蘇軾就曾因寫詩險蒙“叛逆”之名而定死罪,以后又屢遭貶謫。
他曾寫詩形容自己的外貌與心情,說:“心衰面改瘦崢嶸……畏人默坐成癡鈍。”(《侄安節遠來,夜坐》)流放到遙遠的海南后出不了好詩,并不奇怪。只是,這太可惜,令人慨嘆。
蘇軾當年貶謫在海南昌化(今儋州市中和鎮),傳說蘇軾與兒子在桄榔樹中蓋了一間茅屋居住,稱之為“桄榔庵”。元代在此建東坡祠,明清兩代重建并修繕過,并名之謂“東坡書院”。
儋州市位于海南島西北面,如今屬洋浦自由經濟開發區。我在四川時,就聽說四川的眉山縣與儋州市結成友好縣市,相互促進經濟發展,四川人前往儋州投資辦實業的不少。當年蘇軾被謫貶流放的偏僻之地,如今已面目一新,成為舉世矚目的自由經濟開發區了。如此情形,估計蘇公當年是難以想像的吧。
我因不滿足于海口蘇公祠的陳陋空乏,很想去儋州看看,可惜行程安排匆促,未能如愿,深以為憾。
海瑞墓前談海瑞
海瑞戲從“文革”后,似已被冷落在一邊了。這些年,海瑞幾乎被遺忘了,但到了海南,卻又不能不想起海瑞,因為海瑞是海南人,他的墓就在海南。
海瑞墓坐落在海口市秀美區濱涯村南側。“北有包青天,南有海青天”,去瞻仰的人都是懷著對這位清官、好官的崇敬心情去憑吊的。
海瑞(1514—1587),字汝賢,號剛峰,生于明正德九年,卒于明萬歷十五年。海南瓊山府城朱桔里人,回族。其祖父海俅明代從軍,自廣東番禺遷徙來海南,落籍于此。
海瑞一生廉潔奉公,史載他死時行囊中僅存俸金八兩及舊衣數件。皇帝封典海瑞為二品官,其棺柩從南京運回瓊州時,白衣冠送者夾道,祭奠者百里不絕,家家繪像祭之,可見人們對這位敢于為民請命的清官多么愛戴。
但海瑞一生并不順遂。他36歲時中鄉試成舉人,進京會試,兩次均不第。45歲才擢升為浙江淳安縣知府,推行清丈、均儒,吏治有好名聲。嘉靖四十五年,他52歲時任戶部主事,上《治安疏》,批評世宗皇帝迷信道教,不理朝政等事,次年二月被詔逮下錦衣衛獄,后轉往刑部獄。幸好十二月世宗嘉靖皇帝病故,頒遺詔,獲恩釋免職。
隆慶三年,他任應天巡撫,疏浚吳淞江,簡化稅制,壓制豪強,平反冤獄,革新吏治,做了不少實事好事。可是在57歲時又受排擠,被革職回家鄉瓊山,閑居整整15年。直到72歲那年,才又被朝廷起用,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他嚴懲貪污,得罪的人太多,因此累遭彈劾,兩年后病逝于任上。在封建時代,清官好官難做,海瑞的一生是相當坎坷的。
海瑞戲自清末后在京劇中就有,京劇名須生馬連良的《大紅袍》是保留節目,曾在解放前后亮相。“文革”中,研究明史的專家吳晗因一出《海瑞罷官》遭到批判,后竟喪生;馬連良1961年初演出了《海瑞罷官》,在“文革”中也喪生,這使得海瑞成為人人皆知的歷史人物。正因如此,海口的海瑞墓在“十年內亂”中遭到了浩劫。
海瑞墓入口處,有“海瑞陳列室”,這五個字是廖沫沙親筆題寫的。我問一位陳列室的工作人員:“海瑞如今這個墓是真的嗎?”
回答:“當然是真的,墓碑就是最好的物證。”
我早就注意到這塊劫后猶存的墓碑了。墓碑上有“萬歷十七年己丑歲二月二十二日午時吉旦敬建”。碑上古跡斑斑,確是400年前留下的古碑。
但我還是忍不住問:“‘文革時期,墓破壞了沒有?”
“當然嘍!這墓被砸毀,墳被刨開過!”
“發現遺骸嗎?”
“有頭發、骨骸等物,但都被毀了!”
我沒有再說什么。這里確是海瑞的真冢,但曾被刨墳暴尸骨,隔了多年才又重新修建起來。說是真墓,已無海公真骸,夫復何言!
“海瑞陳列館”里有海瑞畫像。他身著大紅袍,戴烏紗帽,左手持朝笏,正襟端坐著。他是一個白眉白須、高顴長臉的瘦削老者,一臉清正廉潔之氣,看了令人肅然起敬。
我站在海瑞像側,請同行者為我拍一張照片留念。
馮子材不應是諷刺對象
我很喜歡海南的通什市。這里氣候宜人,鮮花盛開,檳榔映翠,市容整潔。到通什后,我們往北到牙蓄嶺參觀“海南省民族博物館”。在它的歷史展廳里,收藏著各朝代的海南歷史文物。在這里面,我發現了馮子材的有關資料。
馮子材(1818—1903),清末將領,廣東欽州(今屬廣西)人。他行伍出身,早年曾隨張國梁鎮壓太平軍,升至提督。1884年,法國侵略軍進犯滇桂邊境,兩廣總督張之洞起用馮子材。
當時,馮子材年已古稀,以廣東高、雷、欽、廉四府團練督辦參加抗戰。次年二月,任廣西關外軍務幫辦。在當地人民支持下,他率部在鎮南關(今友誼關)、諒山大敗法軍,不可一世的法軍司令尼格里在此役中受重傷,聞風喪膽。老將馮子材因此成為清末愛國將領中的佼佼者。只可嘆清朝腐敗透頂,打了勝仗仍由李鴻章出面與法國訂了喪權辱國的條約。
我以前并不知道馮子材曾在海南駐防并有政績。通過這次參觀,看到了一些有關馮子材在海南活動的情況和資料,雖然不多,但可以看出,他在海南的開發中是起過作用的。這使我想到了馮子材當年率領包括海南黎族士兵在內的粵軍大戰法軍的情況。馮子材因治軍有方,令粵軍面貌一新,士氣大振,作戰驍勇,為人稱道。
只是在這次參觀中,女講解員講到馮子材時,使用了諷刺的貶義詞,將他說成是一個可笑的、“吹大牛”的、想治好海南卻實現不了諾言的清廷武官,對他的抗法功績卻一字未提。
參觀出來后,出于一種責任感,我對那位講解員善意地建議:“你全部過程講得都非常好,就是關于馮子材的評價,是否提請館里研究一下,無論如何要肯定他是一位清末抗法的愛國將領!”講解員點了點頭。
我想,以后這個博物館在講解到馮子材這個歷史人物時,或許會從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角度,來改變一下解說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