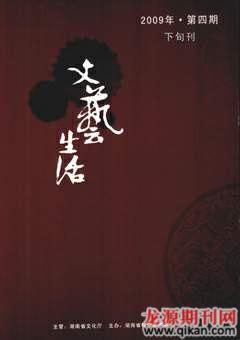詩歌中的人造物象“華清宮”
陳一鳴
摘要:《毛詩序》里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有怨而發,不平則鳴。如不得志的屈原政治上失意,就轉向自然的懷抱以求安慰。像王維的“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李白的“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等不一而足。作為詩歌中的意象便成了作者表達情志的具象載體。本文從詩歌中人造物象類意象、人虛構物意象、行為類意象來比較鑒賞。
中圖分類號:I207.22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5312(2009)12-0039-01
人造物象中常常包蘊著文化功能,如中國詩歌中的“怨怒文化”就會激起我們去感悟。下面的人造物象的兩首“華清宮”就寄托了作者怨恨之情。
“四郊飛雪暗云端,惟此宮中落旋干。綠樹碧簾相掩映,無人知道外邊寒。”(吳融)
“草遮回磴絕鳴鸞,云樹深深碧殿寒。明月自來還自去,更無人倚玉闌干。”(崔櫓)
一提到華清宮,人們很自然地就想到唐代詩人杜牧(公元803—約852年)的名詩《過華清宮絕句》:“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唐玄宗、楊貴妃追求奢侈生活,為吃到新鮮荔枝,派使者從遙遠的四川馳馬進貢。駿馬飛馳,不是使者送國家情報,而是進貢荔枝。我們從這里看到作者鮮明的傾向性,華清宮的奢侈讓世人難以描摹,可以說華清宮是與帝王的奢侈生活聯系在一起的。唐明皇、楊貴妃這兩個歷史人物,一直是歷代文人議論的對象,則是他們奢侈生活的重要見證,成為詩人們關注的焦點。唐代李涉的《題溫泉》,寫出了盛時之象,“能使時平四十春,開元圣主得賢臣。當時姚宋并燕許,盡是驪山從駕人”。唐玄宗時太平盛世四十年,曾經興旺一時,姚崇、宋璟、燕國公張說、許國公蘇颋都經常跟皇帝出巡,多么熱鬧。
這里的兩首《華清宮》詩,從題目看,題材是相同的。但其題詠的角度、所用的手法、所表現的主題并不相同,這就使兩首詩各有特色。
從思想內容來比較鑒賞,我們會發現這兩首詩的不同點如下:
第一,詩歌感情基調不同。唐代詩人吳融,字子華,越州山陰(今浙江紹興)人,生卒年不詳。吳融的詩歌基本上屬于晚唐溫庭筠、李商隱一派,多流連光景、艷情酬答之吟唱,很少觸及重大社會主題,前人評為“靡麗有余,而雅重不足”。吳融的詩諷刺意味特強,諷刺統治者一味沉湎于宮中之樂,只顧自己貪圖安逸的生活,不問民生疾苦,不問國家命運,以致讓安祿山們拉隊伍打進來,斷送了繁榮的朝政。詩人對這段歷史進行了思索,對統治者奢侈生活的丑惡現象進行了鮮明的譏諷,表達了詩人憤恨的感情。
崔櫓的《華清宮》流露了感傷的情調。面對眼前只見月色清輝,卻不見玉人倩影的宮殿,憂愁之感襲上心頭,正如他在另一首同題詩寫的那樣:“門橫金鎖悄無人,落月秋聲渭水濱。紅葉下山寒寂寂,濕云如夢雨如塵。”秋山空寂,門戶緊鎖,宮殿無人,落月悄然,秋水無聲。紅葉紛飛,烏云潮濕,雨線飄散,給人以寂寞感。再也看不到唐帝國的興盛繁榮,如那繁忙的磴道,悅耳的鳴鸞,然而白天不見,夜里也是為此,讓人深感神傷。
第二,作品取材角度不同。吳融詩歌取材于興盛之時的華清宮,在《華清宮》為我們描寫這樣的一幅畫面:郊外綿綿不斷地飄著紛紛揚揚的雪花,云端依然灰暗陰沉,這雪花只有飄落在華清宮中,馬上風干,蹤影不見,宮中與外面,似乎是兩個世界。綠樹參差,與宮室垂下的碧簾色彩相映,加上地有溫泉,熱氣騰騰,全無一絲寒意,顯現出一派春的氣息。華清宮宮內宮外暖寒氣息形成強烈反差。由此可見,華清宮環境多么宜人,統治者生活多么開心。
崔櫓詩歌取材于天寶之亂以后的華清宮。華清宮中的唐朝統治者因為驕奢淫逸,不治理國家,導致安祿山、史思明起兵造反,堂堂大唐頃刻間土崩瓦解。華清宮自然也難逃衰落厄運——昔日磴道(石頭修的登山之道)熱鬧非凡,今日御駕匿跡,磴道冷清,已雜草遮沒,更不用說聽到皇上輦車的鸞鈴聲了。此情此景,失去昔日的生機,白日夜里,物是人去,樓閣玉闌依舊,無人倚憑,給人以寒冷的氣氛。
從作品的藝術手法上看,我們發現它們都使用了對比修辭格。
吳融的詩在對比時,一、四句寫宮外,二、三句寫宮內,這樣構思跟常人不一樣。詩人將華清宮的宮外之況與宮內之景進行對比。寫宮外暗云壓城,雪花如卷,天寒地凍,草木枯瑟;寫宮內只見雪飄,不見雪堆,樹林蔥郁,碧簾垂地,暖意融融,統治者生活悠閑,毫無覺察外面的寒冷,毫無覺察安史之謀。
崔櫓的詩運用對比修辭格來寫今昔華清宮中的人和景,一、二句寫白晝之景,昔日御駕氣派宏大,而如今朝代衰敗,道路雜草叢生。由于宮中空室無人,樹木高大茂密。運用夸張手法來寫“云樹深深碧殿寒”,層層綠樹環抱,各種花卉相擁,皇宮仍是一片碧綠景象,但是依然使人感到陰森、寒冷、恐怖。除了對比修辭外,詩人還運用擬人手法來寫“明月自來還自去”,給這個昔日繁盛之宮涂上凄冷之色,強烈地刺激讀者的視覺有了的印象和感受。
詩歌讀得多了,我們常常會看到長亭、灞陵(橋)、舟、湖、鏡、燈(燭、蠟、炬)等人造物象。如果記住著名文藝理論家劉勰的名言:“情在詞外曰隱,狀溢目前曰秀。”再去鑒賞它們,我們就可以“在詞外”揣摩其“情”, 從詩歌的“隱秀”之境,回味作品高妙卓絕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