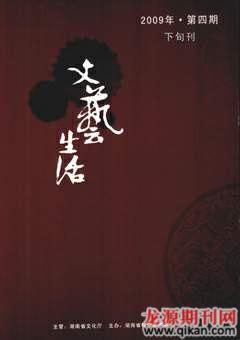“問題與主義”之爭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張 翠
摘要:“五四”運動時期,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者和以李大釗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者圍繞“問題與主義”進行了一場規模不大但影響深遠的爭論。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視角審視“問題與主義”之爭,有助于我們更加客觀地把握論爭的真相。這次論爭不僅切中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時代課題,而且初步揭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涵,并對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產生了重大影響。
關鍵詞:胡適 李大釗 “問題與主義”之爭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中圖分類號:K261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5312(2009)12-0024-02
一、“問題與主義”之爭的起因與經過
“五四”運動前后,西方各種思潮和主義紛紛傳入中國,興起了一股“主義熱”。時人張口主義,閉口主義,而對現實存在的關于國計民生和民族生死存亡的“火燒眉毛”的問題卻聽而不聞,視而不見。尤其令胡適看不順眼的是當時安福系首領、眾議院議長王揖唐也懸起了研究社會主義的招牌,大談民生主義和社會主義。
胡適憂于輿論界“空談主義”的偏向,也急于中國的很多“火燒眉毛”的問題鮮為人談。于是在1919年7月20日出版的《每周評論》第31號發表了《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胡適在引言中說:“現在輿論界大危險,就是偏向紙上的學說,不去實地考察中國今日的社會需要究竟是什么東西。”文中提到在宣傳“主義”時,不要滿足于“紙上的學說”,而要“考察中國今日的社會需要究竟是什么”,“細心考察社會的實在情形”,“懂得現時社會的需要”等等。而且把“細心考察社會的實在情形”作為“輿論家的第一天職”。
胡適的文章發表后,時任《國民公報》編輯的藍公武(志先)發表了《問題與主義》一文。藍公武沒有細讀胡適的文章,雖然提出了反駁,但偏離論題,缺乏必要的說服力。他在文章的結尾說:“要研究種種主義,主義的研究和鼓吹,是解決問題的最重要最切實的第一步。”盡管如此,胡適仍在《每周評論》第33號予以轉載,并在文章前寫道:“知非先生的議論,很有許多地方可以補正我的原作。”后來還收入《胡適文存》1集第2卷。
李大釗是在出京的時候讀的胡文,并以《再論問題與主義》為題整理了他的感想,發表在《每周評論》第35號上。他提出:我覺得“問題”與“主義”有不能分離的關系,解決問題就離不開主義,而有了主義,才能更好地解決問題。而且“也承認我們最近發表的言論,偏于紙上空談的多,涉及實際問題的少,以后誓向實際的方面去作。這是讀先生那篇論文后發生的覺悟。”
為了回應李大釗藍公武的觀點,胡適先后寫了《三論問題與主義》(8月24日)和《四論問題與主義》(8月31日)以及《新思潮的意義》(11月1日)。在這3篇文章中,胡適全面系統的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后因《每周評論》被當局查封,“問題與主義”之爭也就結束。
二、切中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時代課題
任何“主義”都產生于特定的情境,外來的“主義”傳入中國以后必須本土化,才能在中國的土地上生根發芽,這是由文化傳播的一般規律決定的。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中,胡適一開頭就引述了他此前的議論,并再次強調:“一切主義都是某時某地的有心人,對于那時那地的社會需要的救濟方法。”因此,若不去“實地研究我們現在的社會需要”,空談“主義”,特別是空談“外來進口的”和“偏向紙上的”主義,不僅無濟于事,且有弊端。“現在的輿論界的大危險,就是偏向紙上的學說,不去實地考察中國今日的社會需要究竟是什么東西”。
在《三論問題與主義》中,胡適強調“先從研究中國社會上、政治上種種具體問題下手”,在后來的討論中也堅持要先認識某種主義“發生的時勢情形和社會政治的狀態是個什么樣子”,通過比較,然后可以判斷那種主義“在何國何時是適用的,在何國何時是不適用的”。“這樣輸入的主義對于活問題的解釋與解決,一個個都有來歷可考,都有效果可尋,……也許可以免去現在許多一知半解、半生不熟、生吞活剝的主義的弊害”。
李大釗認為解決中國問題不能脫離對中國實際問題的考察和研究,要通過對主義的不同“運用”來解決,即“在別的資本主義盛行的國家,他們可以用社會主義作工具去打倒資本階級;在我們這不事生產的官僚強盜橫行的國家,我們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驅除這一般不勞而生的官僚強盜。一個社會主義者“為使他的主義在世界上發生一些影響,必須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于環繞著他的實境”。
當時在中國傳播的馬克思主義作為外來“主義”的一種,同樣存在著文化傳播中遇到的一般問題。馬克思主義是產生于歐洲資本主義社會的西方文化,西方文化與中國本土文化在很多方面存在差異,因此,馬克思主義就面臨著如何轉化為中國形式,如何與中國國情相結合的問題。“問題與主義”之爭有意或無意地切中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時代課題,對早期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有一定的啟迪作用。
三、初步揭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涵
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就是要處理好主義與問題的關系,即馬克思主義一般原理和中國實際的關系。如何學習馬克思主義,學習馬克思主義的那些東西,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怎樣結合等,這些都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要解決的問題,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題中之義。
胡適和李大釗都肯定了主義與問題是不可分的。“主義”要解決社會問題就必須聯系社會現實,研究解決社會問題也少不了學習主義。胡適認為“中國應該趕緊解決的問題,真多得很”,而且“都是火燒眉毛的緊急問題”。他還希望中國的輿論家,把一切“主義”擺在腦背后,做參考資料,不要掛在嘴上做招牌。胡適在呼吁解決社會問題的同時也肯定“一切主義,一切學理,都該研究”,同時主義和學理“只可認作一些假設的見解,不可認作天經地義的信條;只可用作參考印證的材料,不可奉為金科玉律的宗教”。“主義本來都是具體問題的具體解決法,但是一種問題的解決法,在大同小異的別國、別時代,往往可以借來作參考材料”,但反對下什么藥都可以“參考西洋先進國的歷史和學說”。
李大釗認為“問題”與“主義”有不能分離的關系,任何“主義”都有“理想與實用兩方面”。他說:“一個社會問題的解決,必然靠著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運動。”“我們要想解決一個問題,應設法使他成了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問題。要想使一個社會問題,成了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問題,應該使這社會上可以共同解決這個那個社會問題的多數人,先有一個共同趨向的理想主義。”“所以我們的社會運動,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實際的問題,一方面也要宣傳理想的主義。這是交相為用的,這是并行不悖的。”“大凡一個主義,都有理想與實際兩方面。”“一個社會主義者,為使他的主義在世界上發生一些影響,必須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于環繞著他的實境。所以現代的社會主義,包含著許多把他的精神變作實際的形式使合于現在需要的企圖。”
藍公武認為“問題”和“主義”二者“不能截然區別”,不過是“同一事件”的不同方面,即“問題有一貫的中心,是問題之中有主義;主義常待研究解決,是主義之中有問題”。但他又說:“主義是一件事,實行的方法,又是一件事,其間雖有聯屬的關系,卻不是必然不可分離的”。“方法與主義不過是目標與路徑的關系”。藍公武的觀點基本與李大釗一致,但其論述不嚴謹,有的甚至自相矛盾。
四、對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影響
“問題與主義”之爭中,雙方的觀點都得到了彼此的善意回應,特別是胡適的觀點得到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善意回應,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在爭論中吸收了胡適的部分觀點,關注中國實際問題,開始了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的最初探索。
陳獨秀是早期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重要起手之一,雖然沒有直接參加“問題與主義”之爭,但其后他也發表了關于問題與主義的見解,在他的字里行間可以清晰地看到胡適的痕跡。陳獨秀指出“與其高談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不如去做勞動者教育和解放底實際運動;與其空談女子解放,不如切切實實謀女子底教育和職業”。又在《敬告廣州青年》一文中說:“我希望諸君切切實實研究社會實際問題底解決方法,勿藏在空空的什么主義什么理想里面造逋逃藪安樂窩”。而“我們改造社會,是要在實際上把他的弊病一點一滴、一椿一件、一層一層漸漸的消滅去,不是用一個根本改造底方法,能夠叫他立時消滅的”。
“問題與主義”之爭對青年時期的毛澤東深有影響。他曾不止一次地說,陳獨秀與胡適在他心目中是取代康、梁的人物,陳獨秀對他的影響“超過任何其他人”。1919年9月1日,毛澤東起草了“問題研究會章程”,在這個《章程》中,毛澤東列出問題研究會首批研究的71個問題。毛澤東在問題研究會的章程中,不僅列出了諸多需要研究的問題,而且毛澤東還特別提出:“問題之研究,須以學理為根據。因此在各種問題研究之先,須為各種主義之研究”,“問題之研究,有須實地調查者,須實地調查之”,[13]這個章程明顯受到“問題與主義”之爭的影響。毛澤東還在接編的《新湖南》周刊上,貫徹上述“研究問題”的精神。
中中共早期領導人也意識到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際結合的重要性。如早期理論家瞿秋白在為自編論文集寫的自序中說,自1923年回國之后,一直在陳獨秀通知領導之下,致力于“應用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情境的工作”。“革命的理論永不能和革命的實踐相離。然而應用馬克思主義于中國國情的工作,斷不可一日或緩。”此論斷是將中國第一代馬克思主義者倡導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思想與實踐的全面總結。
雖然在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理想主義因素遠遠大于對中國革命具體道路的探索,尚不具備理論聯系實際的明確意識,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必要性的認識還很模糊,但通過“問題與主義”這場論爭,早期馬克思主義者認識到自身的不足,考慮如何使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進行有機結合,并開始了艱辛而曲折的探索。
參考文獻:
[1]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胡適文集第2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2]耿云志.胡適論爭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
[3]李大釗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艾丹.“問題與主義”之爭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的歷史作用.大慶師范學院學報.2007(6).
[5]胡適.三論問題與主義.胡適文集第2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6]李大釗.再論問題與主義.李大釗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7]藍公武.問題與主義.國民公報.1919-07-24.
[8]三聯書店.陳獨秀文章選編.北京:三聯書店.1984年版.
[9]任建樹.陳獨秀著作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0]斯諾.西行漫記.北京:三聯書店.1980年版.
[1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室.毛澤東早期文稿.長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