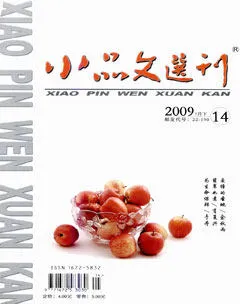時尚有點“壞”
孫君飛
一位老人對我說,現在的街頭充斥著“壞孩子”。
什么樣的“壞孩子”?
老人回答:“你看,他們的頭發紅的紅,綠的綠;衣服不好好穿,打著補丁,后來竟連肚臍和小屁股都露出來了!”
我不由樂了:這是時尚。老人有點明白,可她的表情還是不容易接受。
時尚有點壞,這是一個老人的感受。她從過去走來,而且現在還深受某種傳統觀念的影響,所以她感到一種陌生的怪異和不安,排斥眼前流行的“扎眼”的時尚。其實,不單老人這樣想,在某種時尚顯身之初,多數人都會這樣想,而且常常是:時尚不是有點壞,而是太壞了。
在過去,穿褲子曾經是歐美國家男性的權利,女性如果膽敢穿褲子,還招搖過市,等待她的將是警察的拘捕,因為穿褲子的女人看起來屬于“壞女人”。當時,女性只能穿束腰胸衣及撐裙。而這樣容易導致女性的骨盆變形,有死于難產的危險,由此可見有時候固守傳統比當“壞孩子”還要糟糕。
終于在150多年前,一個名叫艾米麗亞·簡克斯的女性設計出了一款適合女性穿著的褲子,該款褲子具有土耳其風味,可謂時尚前衛。但沒有第二個人敢穿著這樣的褲子上街,簡克斯被社會各界謾罵為下流放蕩、傷風敗俗的女巫。直到1932年,美國影星瑪蓮·笛特瑞還因穿著長褲在巴黎街頭行走,以“有傷風化”罪被抓到警察局。連以時尚著稱的巴黎尚且如此,其他城市豈不要對褲子趕盡殺絕,將其扼殺在萌芽狀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終于讓褲子問題迎刃而解,女性在殘酷的戰爭中只有穿著褲子工作才方便,偽君子、衛道士們終于嘆息一聲,無可奈何地接受了經歷坎坷的褲子。褲子于是風靡世界,成為一種永遠的時尚,再也沒有人認為它反叛和邊緣。
時尚的褲子在我國出現的時候,也曾經被看做是“壞東西”。我們打開了國門,西方的時尚逐漸涌入。當時最“扎眼”的大概就是一種形如喇叭的褲子,人們稱做“喇叭褲”。這種褲子在西方已經流行了近十年,成為時尚的尾巴,但在國內卻驚世駭俗,誰穿著這樣的褲子游走街頭,輕則人們覺得他在瞎胡鬧,重則人們為之恐慌不已,皮里陽秋他是流氓阿飛。不少機關單位、廠礦學校都有不準穿奇裝異服的內部規定,“喇叭褲”自然是奇裝異服,穿奇裝異服的家伙自然是輕浮怪異的員工、“壞孩子”,非被掃地出門不可。
在當時,“壞孩子”們是怎么堅持下來的?是怎樣不讓人們再說他們是痞子和危險人物的?是怎樣讓曾經的“壞東西”華麗轉身,引領了更“雷”的時尚潮流的?我無法聽到這方面的口述,也找不到這方面的資料,然而我知道,“喇叭褲”沖擊了國內的服飾文化,它使我們開始采用A字服裝廓形,使中國人的身高標準提高了10厘米左右,無數的“壞孩子”開始崇尚西方人的體形,它甚至影響到年輕人的擇偶觀,越是比自己高的越想追。
“喇叭褲”之后,筒褲、蘿卜褲、老板褲等魚貫而出,直到出現讓有的老人永遠看不慣、想不通的低腰褲、丁字褲。在上世紀90年代末,“喇叭褲”卷土重來,刮了一陣懷舊復古風,人們早已見怪不怪了。似乎總是國外的時尚“壞”得比我們的早,比我們的徹底,我們的“壞孩子”對于人家的“壞孩子”來說是小巫見大巫,多少有些溫良謙恭。
有時候想想,“壞孩子”們倒是很可愛,又可敬的,在創造和引領時尚、改變和創新生活方式方面,他們簡直可以媲美最先吃螃蟹者。既然時尚初現總是顯得有點壞,好人是不會去嘗試冒險的,只有這些與眾不同、“膽大包天”的“壞孩子”才能夠破冰而走,驚艷一舞,擔當所有世俗的罵名,經受所有匪夷所思的考驗,終于成為時尚的先驅和行動者,無意中將人們帶到更開闊更寬容的天地。
我在學校當好學生時,同樣看不慣那些不好好穿衣服的“壞孩子”。老師們也總愛說:漂亮女生一般學習都不怎么樣,在臭美方面倒是很在行。這難道不是一種傲慢的偏見嗎?有時候,我們看到的只是一種被自己扭曲和染色的符號而已,我們忽略了符號背后的那個同樣美好和正常的孩子,只是他們比我們更勇敢,更早接受了美的誘惑,在同一個圓心處走出了更長更特別的半徑。
我的一個高中女同學在學校里第一個染頭發,穿“臭美”的裙子,戴黑框眼鏡,不斷地顛覆父母給她的淑女形象。有一次,她居然弄了一副夸張的假睫毛,看起來既驚人又迷人。老師嘆了一聲:“學壞容易學好難。”后來,我和她有了深入的接觸,吃驚地發現她的內心竟比誰都傳統,她只是美得最勇敢的“乖乖女”,大家只看到了“壞孩子”可恨的一面,卻看不見她可愛的一面。
當然,時尚“壞孩子”更多的是非傳統,他們的生命力在于顛覆舊傳統,創造新風尚,“壞”得特立獨行,“壞”得接近荒誕,“壞”得多元而絕不重復。時尚有點壞,那是時尚的創造總是充滿與眾不同、輕易不被傳統接受的“壞創意”,人們總是認為它嘩眾取寵,卻不知它常常在后來成了更自由的經典,“壞孩子”由于這一點而不失可愛、可敬。
40多年前,在巴黎郊區的一個小鎮,一個7歲的男孩在電視中看到姑娘們穿著鏤空的、嵌著羽毛的時裝,他一下子被迷住了。在無聊的課堂上,他情不自禁畫了一個小屁屁上粘滿羽毛、穿著網眼服、戴著仿鉆首飾的女孩。這個“壞孩子”的杰作讓老師大為震怒,老師把畫貼到他的背上,讓他到各個教室示眾一番。然而這樣的懲罰并沒有讓這個“壞孩子”蒙羞并悔改。“壞孩子”都具有超強的抗挫力,反而讓他意識到自己在時裝設計方面的天賦和勇氣。“壞孩子”長大成人后果真成了時裝設計大師,他就是讓·保羅·戈爾捷(jean-paul gaultier)。
“壞孩子”其實最沒有野心,除了想當一名時裝設計師外,戈爾捷也不想再當什么。他的第一組女裝竟是用垃圾袋做的,如果不是環保越來越重要,很多人會覺得這有點壞,而不會承認他多么有創意,多么豐富優雅。“壞孩子”不是在制造混亂,而是率先走向多元,他的創造力常常非常驚人。當戈爾捷聽說皮爾·卡丹設計了100個時裝樣式時,他就要設計出120個。戈爾捷說:“如果他沒有幽默感就算不上天才,因為幽默表示你看透了一切。當我們看到星星時已經是在120億光年之后,有些在十億年前就已經不存在了,這說明什么都不必較真,什么都不存在,唯一真正存在的,就是現在發生在你我之間的共鳴。所以一切到頭來都非常簡單,就是愛和游戲。”
在“壞孩子”眼里,時尚何嘗不是一種簡單有趣的游戲。“世界上沒有什么應該做,什么不應該做,如何創新才是所有問題的關鍵。”當然,人們常常將創新理解為標新立異。也許,時尚在流行之前總是充滿了游戲人生的“壞主意”,再加上“壞孩子”的身體力行,我們難免對時尚有些偏見,不知道究竟是時尚帶壞了孩子,還是壞孩子帶壞了時尚。
當設計師戈爾捷將裙子穿于長褲之外,內衣當做外衣穿,拿薄紗做成棉花糖般的衣服;當薇薇安·維斯特伍德設計時裝總是極力地強調胸部和臀部,低低的胸配大大的領子,臀部故意用東西墊高,同樣把內衣當外衣穿,甚至將文胸穿在外衣外面,你才會了解這才是正宗、純粹、最厲害彪悍的“壞孩子”,我們的“壞孩子”只是他們的小學生。
但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常常是越“壞”的東西也越流行,對“壞孩子”越寬容的地方也越容易出時尚大師,越有可能成為時尚的風暴中心,“壞”里面也孕育著好。
選自《時代青年》
——探析《爸爸呢?》中父親角色的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