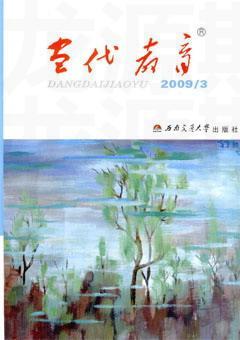鄉土詩情的自然流淌
2009-11-02 10:03:28楊四平
當代教育
2009年3期
楊四平
伴隨著經濟轉型所帶來的全面文化轉型,以精神探索為己任的新詩已被商品經濟的狂潮席卷至社會的最邊緣。物質的膨脹擠壓著人的精神,在這種歷史境遇下,詩人作為人民的牧師,已從傲居于文明金字塔尖上跌落下來,其頭上的神圣光環已黯然失色。有人說,如今寫詩的人比讀詩的人多。在某種意義上,此話確實道出了目前新詩所面臨的尷尬處境。可驚喜的是:還有那么一群繆斯的皈依者,在詩國的園地里虔誠地耕耘著;畢竟還有那么多詩歌在以官方認可或民間自耕的形式存在著。
在當今詩壇,有的詩人一味偏執于個人內心的沉吟自詠,有的在后現代美學中顧影自憐。誠然,詩歌屬于個人,需傳達出個體的生命體驗,并要求把這種內心體驗以藝術的方式形諸筆端。然而詩歌畢竟也屬于社會,這就要求它不能完全背離傳統的人文精神和價值關懷,而且要使其所歌詠的情思為大部分讀者,至少一部分人所能夠欣賞。西班牙畫家畢加索說過:“在繪畫中只有發現。”在詩歌中也是如此,如果一個詩人沒有獨到的發現,決然寫不出好詩。朱自清先生曾說過:“花和光固然是詩,花和光以外也還有詩,那陰暗,潮濕,甚至霉腐的角落兒上,正有著許多未發現的詩。實際的愛固然是詩,假設的愛也是詩。山水田野里固然有詩,燈紅酒釅里固然有詩,任一些顏色,一些聲音,一些味覺,一些觸覺,也都可以有詩。驚心觸目的生活里固然有詩,平淡的日常生活里也有詩。……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