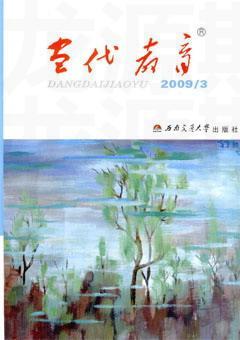心祭
衛 華
今天是母親節,但我卻忘了。做一個職業女性兼家庭主婦,我有太多的事要做,一如我的母親,除了工作,所有的時間和精力都在丈夫和兒女的身上,哪還顧得及其他?然而我的同事卻記得。
“哎呀,今天是母親節,我要早點回去!”她一邊收拾東西一邊說,“去給我的老母親買點禮物,給她們做點好吃的。”
“真的。”其他同事也紛紛附和,開始收拾東西。只有我坐著沒動。
“你——”一個同事欲言又止。
我知道她想說什么。
“我母親去世13年了。我婆婆和繼母都不在這里。”我說。
“我們先走了,拜拜!”揮揮手,他們都走了,只留下我一個人在空蕩蕩的辦公室。
“打個電話吧。”我想,應該撥個電話問候一聲“節日快樂!”
電話通了,那頭聽見了我的祝福,仿佛很高興的樣子,聲音里充滿了幸福和喜悅,打電話的我也很甜蜜的感覺。可是,我也給我的母親打過類似的電話,母親的表現卻沒有她們的好,母親在電話里只是很平淡地說:“快樂。”停一停,又說,“你們都好的吧?好好工作,也別太累了。多熬些骨頭湯給奎兒吃……”母親好像還說了好多話,我已不大記得了。那時,我的兒子才一兩歲,我也正是初為人母,居家過日子還是新手,每次通話,母親總要教導我一番,生怕我處理不好家里的一切,啰啰嗦嗦,哪里像婆婆和繼母這樣善解人意呢?她并不因為兒女記得她的節日而高興和滿足。那時,我曾經因為母親的平淡而有些失望,可是今天我應該是如愿了,怎么反倒有些失落呢?
母親節!
我的母親卻已永遠地離我而去,我能做的,也許只有心祭了。
1
母親原本不該是苦命的,但她的命卻苦得很。
母親出生在一個大地主家庭,家有良田數頃,光使喚丫頭就是六七個;她的叔父還是當時大定縣政府的一個科長,在地方上可以稱為望族的;她的父親是一個很有思想的人,很得鄉里鄉親的尊重。紅軍第一次到畢節,外祖父便悄悄地跟紅軍走了,外祖父在行軍途中得知消息,憂心急慮,加之體力不支,因掉隊被抓住后以“通匪”罪槍斃。外祖母帶著母親兄妹不得不淪落為窮人過上了苦日子。十五歲時,勤勞懂事的母親被外出做生意借宿她家的祖父看中,嫁給了我的父親。那時我的父親還在讀書。母親十七歲生下我的大姐,父親便做了私塾先生,二十一歲生下二姐時,父親被政府叫去做文秘工作,算是參加了革命。父親于是東奔西走,除年三十外,都不在家。“干部家屬”是很受人羨慕的,可“干部干事去了”,家的擔子都壓在了母親的肩上。
“現在是共產黨領導,爹的‘通匪罪是可以平反的。”有一次父親對母親說。母親惶惶地看著父親:“他大舅老實巴交的,我一個婦道人家,你又忙,哪個去找政府呢?”父親不說話,母親也就不說話了。但這卻如一塊石頭壓在母親心上,直到八幾年我參加工作,母親還說:“曉得你外公能不能平反啊?”“他去世了,財產化為灰燼了,平反有什么用?”我覺得沒必要勞神費力,干脆地說。“可那是名譽。”母親喃喃著走開了。
為什么我現在仿佛覺得那時她的眼里噙著淚呢?
父親工作忙,很少回家。母親上要侍奉老的,下要拉扯小的,農活又重,也不能進城看望父親。被祖父祖母逼得緊了,她才會探一次親。不過父親沒時間陪她,她也不過吃幾天的大灶后就回去。她常說,我們姐妹六個是觀音菩薩怕她寂寞派來陪她的,殊不知她為了我們吃了多少苦頭啊。鄰里鄉親因為她盡生女孩瞧不起她,家人親戚因為她盡生女孩冷落她。繁重的體力勞動和沉重的精神壓力使我的母親過早地衰老了,我記得她和我這樣的年齡時,已經像六十歲的老太婆。
母親生在一個富貴的家庭,嫁給一個國家干部,她不該是苦命的,可她童年失父,少年成家,青年持家到六十六歲辭世,艱苦辛勞,沒吃過一頓好飯,沒穿過一件好衣,走得最遠的就是畢節城,玩得最開心的就是看電影。沒有物質生活,更談不上精神享受,實在是苦命得很!
2
母親是大戶人家的女子,因為時代的因素,她的性格也就打上了時代的烙印。
她十五歲嫁到我們家。在我們,還是父母膝前乘歡撒嬌的年齡,可母親已經用她稚嫩的肩膀挑起了一個家。她每天總是天不亮就起床,掃地、添火、煨好洗臉水,準備好早餐,等待家人起床用過早餐后一起上山干活。
那時,家里除祖父祖母外,父親還有一個姐姐,一個妹妹和一個弟弟。祖母在家做飯。祖父農忙時帶著大家干活,農閑時做生意。父親和叔叔讀書,家里的主勞力就是三個娘子軍。從地里回來,姑子們或坐或躺都息了下來,她卻是鍋臺灶后,端菜盛飯,洗碗喂豬,忙個不亦樂乎。
父親的家人是和善的,母親的表現是優秀的,所以,一家人和睦友好,相親相愛,從沒有婆媳不和,姑嫂爭吵的現象。就是鄰里,母親也待他們如家人。所以母親在寨子里,深得長輩的喜愛和同輩晚輩的尊敬。“嘉霖大伯得了個好兒媳婦。”長輩們說。“找個作軍家那樣的,又漂亮又賢惠。”同輩要娶媳婦時總以母親做標準。
母親是典型的孝媳、賢妻、良母,我從沒聽母親抱怨過誰,但以我為人媳、為人妻、為人母的感受來體味,她應該是有許多無奈的吧?
“你家爺爺是最公正的”談起家人,母親總說。爸爸在外工作,叔叔先讀書后當兵,他們都不在家。有時從山上回來,大家都累得不想動,奶奶鞋尖腳小的,要忙一大家人吃的飯,真不容易。母親便常去搭一把手,爺爺就吵兩個姑姑:“你看你們兩個,一回來就曉得自己休息,也不學學作軍媳婦。你們累,她不累?起來幫忙!”有時姑姑們會惱母親,說些小小的氣話,爺爺會說:“知足吧!各人掰著指頭算算,這家里誰起得早,誰睡得晚?”
后來娶了嬸嬸,嬸嬸和叔叔是同學,屬于新女性,是生產隊的記分員,勞動之余,她總是抱著一本書,哼哼唱唱的,或抱著正在織的毛線衣躥躥門。爺爺好像看不慣姑姑們那樣,他就在大家都在的時候說:“幺們,大鍋飯,大家辦,這家里七零八雜的事光靠你家媽和大嫂是做不完的。”
家里的收入都是交爺爺統籌,包括父親和叔叔的工資。女人都是愛美的,姑姑她們時不時找爺爺:爹,我這樣或者那樣破了,拿點錢跟給我買點布來補一補或者重新做。母親是從不主動要的,她常用破布補破衣。“作軍媳婦,你也去扯點布添點衣物嘛。”常常是爺爺在拿錢給姑嬸的時候,主動把錢給母親。
我曾經問過母親:“你得的有她們的多嗎?”
“沒有。”
“你和爸爸對家的貢獻都大,你得的卻少,你不生氣?”
“大家都幫著帶你大姐二姐呢!”母親很坦然。
“人家得幾次你才得一次,其實爺爺奶奶還是有點偏心。”我替母親不服氣。
“愛哭的孩子多得奶吃。我不要他們都想得到給,他們夠好了!”
“那你為什么不要呢?”我想不通。
“不當家不知油鹽貴!當那樣大一個家不容易。”
“你不是因為后家是地主不敢要吧?”我試探。
母親笑笑,不說話。
其實母親哪里只是不要?父親在城里工作,帶回來什么,總是先分給家人,有時分到母親面前時,已經沒有了,母親總是寬容的對父親說:我以前在家吃過的,或者用過的。這樣,父親也就釋懷了。
“你真的吃過用過嗎?”我問母親。
“我才四歲你公公就死了,我們家就被傾了。”她只淡淡地說。
我無話可說。
父親很難回家一次。他每次回家,母親總是像過節一樣,忙前忙后,端茶倒水,盡力招待那些來和父親擺龍門陣的人。末了,飯飽茶足,眾人深夜散去,母親還要為父親端來洗臉水,倒去洗腳水。這個習慣,差不多保持到母親去世。
對家庭的關愛,對家人的體諒,加些許自卑,就構成了我的母親。
3
母親的命運和民族、時代的命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三年自然災害,年成不好,兩個姑姑相繼出嫁了。吃不飽飯,鄉人要么砸鍋賣鐵,要么出外逃荒討飯。
大躍進,伙食是按性別年齡分配的。而事實上,小孩最終吃下肚的,比大人分配到的還要多。許多人活不下去了,臉上沒有了血色,身體卻像發酵的面團般腫脹起來,用手一按,便凹陷下去。
莊稼是集體的,自己也不能栽種。山上的野菜吃完了,野草也吃完了;樹葉吃完了,樹皮也吃完了;人們走投無路,只有吃觀音土了。隔壁的付家,先是男的死了,接著又死了一個小孩。和所有的人家一樣,我們家也分家了。叔叔在部隊,嬸嬸帶著堂姐。循皇帝愛長子,百姓愛幺兒的例,爺爺奶奶和嬸嬸一起過,母親帶著我的三個姐姐和一個哥哥單過。
五個人的飯加起來也不過半斤。母親取回母子五人的飯,把它倒在鍋里,加上幾倍的水,再把好不容易尋來的野菜草梗之類加進去,熬成稀粥,分給她的孩子們。
有時,爺爺奶奶也把他們的飯分一半給母親。
母親的為人很好,有時,食堂的某人會偷偷給母親一點干包谷面,一點沒磨成面的麥子或沒打成漿的黃豆之類。母親把它們帶回家,分一些給爺爺他們,然后勻著吃。麥子之類的東西,母親是舍不得直接吃的。她總是把它們分批埋在家里的一個鍋里,讓她們發芽,長成苗,最大限度的來充饑。
然而災難并不因為人的善良、聰明或者弱小就不降臨到他的頭上。我的三姐終于挺不住饑餓和疾病的折磨夭折了。母親的痛苦是可以想見的。但就在她更加拼命地呵護她的三個兒女的時候,我的哥哥又被腦膜炎帶走了。
“那段時間,媽媽就像傻的一樣。”二姐在和我說到這段日子的時候說,“她拼命地勞動,一閑下來就會發呆,我們晚上有時醒來,會聽見她的啜泣。”
我曾經和母親談到這個話題,其實我擔心她不愿提及,但我卻想知道,因為我不知道我與姐姐她們為什么會相隔這么多歲。母親說這段往事的表情,有些像祥林嫂說她的阿毛。
“他平時都不聽把,所以那天晚上我把他的尿,他不屙,犟,我就輕輕打了他的屁股一下,他只好哭著屙了。躺在被窩里一會兒,我覺得他有些發抖,我趕忙起來叫你奶奶,他們都起來了。那時不過晚上兩三點鐘,要到老街上,要走十多里山路。你爺爺叫我們先摳些灶心土澄水給他喝。可是喝了卻依然抖,我們都沒了主意。到四五點鐘時,看著不行了,我們趕忙打著火把,高一腳低一腳地背著他往老街上趕。我們趕到區衛生院的時候,醫生還沒上班。我只好抱著他在醫院門口等,你爺爺他們去請醫生。醫生趕來,給他打了針,藥都還沒喂完,他就死了。我現在還記得他那時的樣子。他仰著臉無神打氣地問我:‘媽,我是不是要死了?媽媽,我不想死。……唉!”每當這個時候,母親就會說不下去,我也會被她帶得哭起來。
“都怪我,我不硬把他屙尿,也許不會發病;我要是一發現他抖就背他上區衛生院,也許他不會死;我如果把他送到縣醫院,他也許不會死。”母親每次最后都是這樣說的。我知道這不是母親的錯,父親不在家,許多事她都得尊重長輩的意見,而那時黑燈瞎火的,又都是山路,要上區醫院尚且那么難,上縣醫院又談何容易?但我的勸慰是無用的,母親總是把自責永遠地背負在自己的身上。
而失去一雙兒女的母親又患上了十二指腸胃炎,長期的疼痛使她骨瘦如柴。在別人都以為她要死了的情況下被送到縣醫院,又因無人照料,藥物過敏差點送命。要不是醫生發現搶救及時,我們家早就沒了我們后面的四朵金花了。
“她全身僵硬,口吐白沫,眼睛翻白,嚇死人了。”盧阿姨說。
“我只覺得舌頭縮短了,說不倒話。”母親倒不覺得有多緊張,“我死倒不要緊,我就怕她們兩姊妹也活不出來。”
珍惜別人,不在乎自己,這就是我的母親。我從她那兒是不是承襲了一些呢?
4
我的母親不識多少字,但她能出口成章,熟練地引用“論語”、“增廣”和“幼學”等典籍里的詩文。可以說,她的文化素養和對文化的熱愛是許多文化人所不及的。
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女孩子一般不能進入學校。人們普遍認為:女孩最終是要嫁人的,送女孩讀書,就等于把錢丟到水里。可母親卻認定“養兒不讀書,如同養頭豬”。她說服我的爺爺奶奶:“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干部的姑娘字都認不得一個,人家要笑話的。”我的大姐剛到入學年齡,母親便把她送入了課堂。學校離我們家有近十里山路,母親只好讓大姐寄居在親戚家。她總是星期一起早打著電筒把大姐送到學校,星期六再不辭勞苦把大姐接回家來。大姐常回憶母親初次送她入學的情景:
那天天氣很好,涼風習習,田里一片碧綠,稻谷開始灌漿了,地里包谷的紅纓也已經變成了醬色。媽媽有時背著我走,有時牽著我的手走。想到自己就要成為一個小學生,我的心里真的好高興。走到沈家院子的時候,一條縮頭狗突然跑出來咬了媽的腿一口。媽媽的小腿褲管被撕掉了一綹,血流了出來,我被嚇哭了。寨子里的人都跑來看,他們一面幫著媽媽哄我,一邊和媽媽說話,得知媽媽是送我去報名,好多人都進行勸阻。有一個人還說:“才送她讀書你就著狗咬!這不是一個好兆頭。你還要送她去讀書?!”媽媽一邊和大家說話,一邊用主人家端來的飯捏成團,滾過傷口,照習俗把殷紅的飯團丟給了狗,然后用主人家找來的破布纏住傷口后,就又帶著我朝學校走去了。……
因為傷口沒有很好處理,后來就留下了拳頭大的一個黑疤。父親常常指著這黑疤對我們說:“那是一個光榮的記號呢,它表明你們的媽是一個重視文化學習,有長遠眼光,又不重男輕女的人。”但我們感受到的,卻只是媽對我們的愛。
“文化大革命”時期,承載文化的書被焚燒,追求、傳播文化的人被迫害。有一個叫齊華宣的人,被打成了反動學術權威,下放到了我的家鄉,住在生產隊破漏的“社房”里。由于第一次參加勞動時,他把農民們背糞時用來中途息氣的“拐耙”用倒了,誤把月牙形的半圓倒置在地上,把背簍頓在了尖細的拐錐向上,農民們便用一種不屑的眼光來看他,還把他說的“接觸面積越大,重心越穩”的話作為了閑談中的笑料。母親對此卻很有自己的看法,她說:“人無完人,金無足赤。人家在城里讀書做學問,當然不知道拐耙是怎樣用的。我們懂用拐耙的人到了城里,還不是拿著煙桿到電燈上去點火。”她常讓大姐二姐給齊老先生送去一碗粥或一鍋湯。有時姐姐們偷懶不想跑:“你不該自己送去!”母親卻不惱:“幺兒,人家齊爺爺年紀大了,又沒有吃過苦,現在落難,在我們這里人生地不熟的,我們不幫他就沒人幫他了。他是有文化的人,你們去,可以學習點東西……”
大姐加入了學校的“紅衛兵”組織。十五六歲,正是自以為是,盲目追趕潮流的年齡。她的第一個革命行動,就是帶著她的“戰友”們到我家“破四舊”。他們把家里的藏書一股腦兒地搬到庭院里,要將這些“封建文化”、“黃色書籍”付之一炬。奶奶移動著她的小腳,拉著這個,卻又放跑了那個,急得滿臉通紅,氣都喘不勻了。母親放工,遠遠地看見家里煙霧騰騰,以為著火了。她上氣不接下氣地跑了回來,看見那正被火舌舔舐的書堆,氣得不行。她順手從地上抓起一把竹枝,一邊撲打著火苗,一邊高聲吼道:“誰不讓開,我打著他不要怪。”紅衛兵們被她的氣勢鎮住了,都不敢說話,更別說阻攔了。把火撲滅后,她一邊心疼地把書進行著分揀,一邊教訓我大姐:
“你燒書,你以為你能!”
“這些書是你爸爸從外老祖公和公公家背來的。不是好書,他還背來做什么?”
“你們說這些是壞書,你們讀過了嗎?就憑看著破舊就是‘黃色書籍了嗎?”
母親的詰問,把“小將們”弄得瞠目結舌,敗下了陣去。后來看電影,每當有英雄挺身而出的情節時,我就會想起母親撲火救書的場面。那也可以用大義凜然,奮不顧身來形容吧?
我的母親也該是個英雄!她不僅救下了一堆書,還培養了六個有知識文化,又有品德修養的女兒。她對我們進行教育,既能以身作則,又能言傳身教;既有引經據典的理論教育,又有循循善誘的閑談聊天。她嘴里的普通語言,表達的卻是哲人的深刻思想。我們姊妹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走穩一步又一步,不能不感謝我的母親!
5
說到感謝母親,也許我比我的姐妹們都有話可說。
小時候,我覺得母親對我特別的好。因為窮,家里只有逢年過節或有客人來,才吃米飯,蒸臘肉。有客人,我們小孩是不能上飯桌的。但在飯前,母親總會背著別人給我一口飯或一塊肉吃,然后打發我們到屋外的竹林里去玩。
我九歲的時候,父親把我和堂妹帶到了城里讀書,讓奶奶給我們做飯。七十年代,交通還十分不便,我們鄉下人要進城,要么就是兩三點鐘起床,摸黑趕幾里山路到街上,六點鐘以前搶坐新建社的馬拉“轎車”,要么就是八點鐘左右到街上后,一直守在公路邊,等著路過那里的長途客車上偶爾有站位時把你捎上。而更多的時候,則只能走路。從我家到城里,有大約七十里路。因為是農業戶口,我們吃的糧食和蔬菜都必須從家里背來。父親在城里工作,叔叔在部隊服役,爺爺在大躍進時就去世了,可以想見,要把三個人的食物送到城里,是多么的不容易。而擔任運輸工作的,基本上是我的母親。每當看到母親在萬家燈火中,拖著疲憊的雙腿,背著五六十斤重的背簍,氣喘吁吁,滿面通紅,頭發衣背都被汗水浸濕地出現在我們的面前時,我總是感覺很幸福,又很難過。
母親的到來,往往會給我們一些意外的驚喜:一串風干的牛肉;幾小砣粑粑;幾個新包谷,一些新洋芋;一雙手工做的布鞋;一件舊衣服改做的“四季衣”;一束山茶,幾朵牡丹……現在想來,一年四季,恐怕只要是母親喜歡的,擁有的,能想得到的,物質的,精神的,能給我的,她都給了。
八零年參加高考,我以兩分之差名落孫山,父親讓我“滾下鄉去”。是母親用溫暖的胸懷鼓勵了我:“有哪樣了不起的?學走路還要跌倒呢,哪個跌倒的人最后不會走路?”“幾百個人只取一個,大學就那樣好考嗎?今年考不起,明年再來就是了。”她不讓我去生產隊掙工分,要我抓緊時間復習,要我牢牢記住:有志者,事竟成。
八一年我考取師范專科學校,因為是大專,大姐二姐又都是教師,我不想去讀。母親一直沒有表態。一天早晨,她抓了一把包谷,把我叫到雞圈邊,讓我打開雞圈門。圈門一開,雞們蜂擁而出。一些雞拍打著翅膀向遠處跑去,一些雞低著頭在附近覓食,一些則抬著頭一直盯著母親的手。母親不說話,靜靜地站著。我知道母親有話要說,因此沒離開,也不說話。母親突然把手里的包谷撒到地上,雞們便爭先恐后地搶著吃。等跑遠的雞趕來時,地上的包谷已經沒有了。母親看著我,靜默了一會兒,說:“你看到了,機不可失,失不再來。還是去讀吧。”她停頓了一下,又說:“就像這群雞,跑遠了的,我撒包谷的時候,它們來不及跑回來。一直盯著我的手的,我要是不撒,它就要餓肚子。只有那些一邊自己找食,一邊注意著我的雞,才什么都不誤。”我接受了母親的意見,開學便去學校報了名。我的一個同學,情況和我差不多,他堅持不讀。后來連考三年,最終還是進了師專。這樣,原本我倆應該是同步的,而最后調資晉級我都要比她提前三年。
大學畢業,有關系的人家都在找后門留城,我父親只是個一般工作人員,我們家沒有后門可開,我因此整天悶悶不樂。母親開導我:“命里有時終須有,命里無時莫強求。分到哪里都是工作,分到哪里都拿工資。你又何必心焦呢?再心焦也留不了城。”想想母親說得也有道理,我于是坦然地等待著命運的安排。剛好那一年外地大量招聘教師,我們當年的畢業生全部留城,我因此也就有幸留在了城里。
剛參加工作,母親不斷囑咐我要好好教書,要對得起家長,對得起自己的良心。我也以滿腔熱忱投入了工作。我的工作得到了學校、學生和家長的好評,我獲得了縣政府的表彰。我有些沾沾自喜了,有時會在同學朋友聚會時自我吹噓幾句。母親背后批評我“有麝自然香,何必當風揚!你的路還長得很。”我于是學會了踏實、低調地做人。
母親對我們姊妹的婚姻是相當重視的,她要求我們選擇男朋友的標準是:不求當官作府,只要門當戶對;不要風流倜儻,只需勤勞善良。如果沒有相同的生活習慣和處世態度,是不可能和睦相處而又心情愉快的,除非委曲求全!剛成家時,我讓父母親操夠了心。好在后來的家庭生活中我們慢慢地適應,逐漸的磨合。現在,母親的在天之靈可以為我放心了。
感謝母親,是她生養和教育了我,但對于母親,我除了感謝,還有著深深的歉疚。
6
歉疚就像一根針,刺著我的心和靈。我常自責,卻不知道怎樣才能獲得我的心和靈的寬恕。
我們只有姊妹六人,母親很為她的養老送終擔憂。有一次,母親和我閑談,委婉表示希望將來和我生活在一起。我當時只考慮到自己脾氣急躁,怕伺候不好母親,就說:“將來你還是和二姐住吧,她脾氣好。我負責你的生活費。”我不知道母親當時是怎樣想的,但后來她再沒提過這個話題。她去世時,我們大的四姊妹都已成家,她在二姐和四妹家都曾一年半載的呆過,而在我家,最長的一次也不過三天,而且還是我公婆外出,丈夫出差的情況下來給我做伴。我偶去看她,她總要留我和她住上一宿。晚上,尤其是冬天,她總把我的腳擁在懷里,為的是用她的體溫來溫暖我的雙腳。母親啊,你溫暖了我的腳,我卻寒冷了你的心,我是多么的不孝啊!
我們大了,成的成家,就的就業,母親該享點福了。可是,由于二姐的善良和我的無知,母親的晚年很郁悶,甚至可以說有些痛苦。抱養小孩消蝕了她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閑言碎語又消磨著她的精神和意志,而莫名病痛更折磨著她的身體和心智。母親被摧垮了!而母親生病期間,我竟未能從經濟抑或勞力上給與她一些幫助。我孝敬我的公婆,周濟我的學生,捐助災區的難民,施舍路邊的乞丐,可是我卻要負疚我的母親一輩子了!
母親去世的前一年,是她的六十五歲生日。不知怎么回事,二姐和四妹都從外地趕了回來,遠在北京當兵的外甥也回來了。那是母親六十幾年的生日中最熱鬧的一次。二姐的一個朋友還為大家錄了像。那天,母親很高興,臉上露出了燦爛的笑容。濟濟一堂的兒孫一一向她敬酒,恭祝她能“壽比南山,福如東海”。當母親說她什么都不焦了,只愁棺材還沒有著落時,我們竟沒有一個人在意她的話,甚至批評她杞人憂天。可是,這卻成為了我們姊妹共同的遺憾:因為直到母親去世的那一天,她最終還是沒能親眼看到她的棺材。
母親啊,我們姊妹只希望你能安享晚年,卻不曾想你僅六十六歲就撒手人寰。我們縱然買了我們能找得到的最大的棺材來安葬你,那又怎么樣?我們永遠地失去了你了。無論我們怎樣哭泣,無論我們燒多少紙錢,我們都無法喚回你。那一年一度的清明祭掃,成了我們陰陽相隔卻渴望陰陽相聚的唯一方式。撫著你墳頭的草,抓著你幕前的泥,便仿佛摸著你的手,牽著你的衣;點燃裊裊的香,焚燒疊疊的紙,便似乎為你拉開暗夜里的燈,端去熱熱的水。坐在你的墳前,我們和你話家常,告知你我們的喜怒哀樂,也渴望分擔你的冷暖寒熱。可是,母親,你聽到了嗎,你看到了嗎,你感受到了嗎?
沒有,你肯定沒有!要不,你為什么不到我的夢里來,來告訴我你在那邊生活如何,天堂有沒有賣后悔的藥?
母親啊,你知道嗎,歉疚時時刺痛我的心。你把我當作了你的命,我卻無知地改變了你的運。我的錯,我今生是無法彌補了。我只能祈求你的在天之靈原諒我,寬恕我了。
母親啊,你那么愛我,我知道你會原諒我,寬恕我。也許,你根本就沒有計較過我。事實上,永遠不能原諒我,寬恕我的,是我自己——是我的心,是我的靈!
今天是母親節,再過二十天,就是母親十三周年的祭日。我想,我現在,祭日那天,乃至以后,唯一能做的,就是心祭了。唯有心祭,能表達我對母親的感謝,唯有心祭,能表達我對母親的歉意,也唯有心祭,能表達我對母親的思念和愛意。但愿我的心祭,能為神人理解,幫助我的母親在天國生活得更美麗!
母親,您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