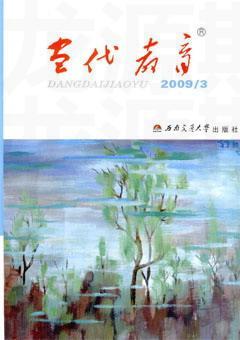童年的元宵節(外1章)
吳 建
北宋文學家歐陽修在《生查子》中寫道:“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后。今年元夜時,月與燈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濕春衫袖。”這是寫元宵節的作品中極具代表性的作品。然而我童年時的元宵節既看不到“花市燈如晝”的美景,也沒有“淚濕春衫袖”的傷感,有的只是難以忘懷的狂歡。
那時,每到元宵節,我們小孩子便央求大人為我們扎“燈籠”。我的父親是村里扎燈籠的高手,尤其擅長扎“兔兒燈”。元宵節的早上,父親喂完豬,將院子打掃得干干凈凈,就坐在院場上給我們姐弟幾個扎兔兒燈。我們則替他做“小工”,拿竹篾、硬紙,找鐵釘、蠟燭。有時候我們自己也學著做,做的當然是最簡單的燈,如四四方方的箱子燈,棱角分明的三角燈。
元宵節的晚上,我們吃完糯米圓子,便趕到隊里的打谷場上“溜燈”。打谷場上早已聚滿了前來溜燈、觀賞燈的孩子和大人們。那些大大小小、五顏六色的兔兒燈、金魚燈、狗兒燈以及孩子們自制的三角燈、五星燈、箱子燈……把個小小的打谷場照得璀璨奪目。從遠處望去,真似浩繁星光,也像漁火點點。蠟燭在燈籠里綻放著亮麗,歡樂和幸福也映現在每一張小臉上面。我提著那憨態可掬的兔兒燈,在小伙伴們的驚嘆和羨慕的目光中炫耀著走來走去,心里洋溢著前所未有的歡愉。
在場上溜了一會兒燈,我把兔兒燈交給姐姐,就去和小伙伴扔火把、放哨火。扔火把必須是男孩,因為男孩有力氣,火把兒扔得高。在我的家鄉有這樣的說法,元宵夜誰的火把扔得高,誰家今年地里的收成就高。用作火把的是家里刷鍋用剩的高梁把兒或者是掃地掃禿了的笤帚把兒。大人們把它們廢棄了,可小孩子們卻留了個心眼兒,將它們精心收藏起來,來年元宵節作火把兒扔。為了使火把兒易燃、耐燒,我們還將火把在生產隊里的拖拉機柴油箱上反復地、使勁地蹭,謂之“揩油”。我們點燃手中的火把,一邊扔一邊唱著兒歌:“火把兒,流流星,一棵麥子收一升。火把兒,金銀燈,照得糧囤滿滿的。火把兒,光明燈,照得年年好收成……”我們舉著火炬似的火把在田野里奔跑,再用力拋向天空。火把在鄉間的麥田上此起彼落,遠看如夏季的流螢。
火把快要燃完時,我們又用剩余的火把頭兒點著了路邊河岸上枯萎的野草和灌木叢,俗稱“放哨火”。枯朽的野草和灌木最易燃了,剎那間,田野上火光熊熊。莊稼人豐收富足的宏愿和對風調雨順的企盼,在火光中熠熠生輝。我們一邊放火一邊唱著兒歌:“正月半,放哨火,放了哨火野草沒,野草沒了稻麥長,沉甸甸的稻麥笑彎了腰……”唱完了兒歌,我們又吟誦起剛剛從課本上學到的白居易的詩:“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正月十五,這個時節,春的腳步越來越近,冰凍的土地開始融化。枯黃的野草在哨火中化為灰燼,那春風就有了些許暖意。過不多久,沉睡了一冬的萬物便在春風的撫慰下蘇醒、生長,呈現出一片勃勃生機。
童年的元宵節是那種樸實本真的快樂,像小河里的水潺潺地流著,彌久地散發著青草綠禾的芳香;仿佛一杯茶,細細品咂,清香淡雅,讓人頻頻回味。而今的元宵節,早已沒人扔火把、放哨火了。鄉間的兒童只有圍在電視機前看元宵晚會取樂的份了。然而,不管到什么時候,元宵節的火光都會永遠地存在,歲月就在那火花里燃著。
小村夏夜
當暑熱褪去,習習涼風穿過田野,夾著泥土的芳香,拂過河面,擷取水草淡淡的腥味,掠過樹叢,攜帶鳥兒甜蜜的歌唱來到小村,小村的夏夜便降臨了。
剛從莊稼地里收工回來、被曬得黝黑的漢子從井里打來一吊桶水,當頭倒下,將渾身上下沖了個遍。在家里忙完了家務活、被汗水浸得水靈的女人把早已做好的飯菜擺上了院子里的方桌上,然后解下圍裙,拍拍身上的灰塵,走到院外扯開尖細的嗓子大喊:“伢兒,你在哪兒啊?快回家吃飯呀。”這樣一連喊了三五聲,才聽到遠處河邊樹林間傳來稚嫩的童音:“我在這兒呢,就回家。”不一會兒,一個光著腚、赤著腳的頑童滿頭大汗地溜進院子里,撲到飯桌邊搛了一些腌菜放在黏稠的糝粥碗里,捧起碗又去找小伙伴野玩,大人們免不了要斥責幾句:“死伢子,吃飯都不安分。”
如水的月光漫過鱗次櫛比的小屋,把銀輝灑在各家各戶的院子里。家家升起用麥殼、稻草燃起的煙霧,驅趕著蚊蟲。男人照例要喝一點老酒。那窖藏了一冬一春的米酒此刻在飯桌上飄溢著醇香。女人自然要炒一碟花生米給男人做下酒的菜。吃飯時,男人邊呷著酒邊給女人講述地里莊稼的長勢,女人則邊啖粥邊告訴男人家中的老母雞下了幾個蛋,娃兒的衣服又磨破了幾個洞……飯后的小憩是小村男人女人最溫情最浪漫的時刻。月光在微風的多情撫摸下,顯得格外溫柔、恬靜。男人喝得微醉,臉色酡紅,他瞇縫著眼瞧著對面只穿一件汗衫的女人那鼓鼓的胸脯。女人被盯得不好意思了,臉頰上飛起兩片紅云。她一邊收拾桌子,一邊嗔道:“老不正經的,今晚你又喝多了……還不快去把伢子找回來洗澡。”男人嘿嘿一笑,站起身在女人的胸前重重地抹了一把,亮亮地應了一聲“哎”,就趿著拖鞋“吧噠,吧噠”地向院外跑去。
村頭的大槐樹下是小村人夏夜納涼的最好去處。輕風像一壺老酒,把這棵大槐樹灌得醉意朦朧,細小的枝葉擺來擺去,像邁著小醉的步子走在回家路上的一個旅人。吃過晚飯,用熱水除去一身疲憊的人們手搖著大蒲扇、拎著板凳,坐在粗得要兩人才能合抱的樹根周圍,各種新聞便在嘰嘰呱呱的談論中傳遞開來:某地洪水淹死了多少人,某某處某家的鴨子下了一個奇異的蛋,某某姑娘和某某小伙子定了親……只有孩子們,對大人世界里的東西不感興趣,他們在人群中穿梭往來,或捉迷藏,或追趕從河面上、蘆葦叢中飛來的螢火蟲……突然,“嗯、嗯”從不遠處傳來兩聲干咳,是村中輩份最高的李大爺來了。他光著上身,古銅色的臉龐上溝壑縱橫。見他到來,大槐樹下倏忽寂然無聲,人們都自愿讓開一條道,請李大爺坐在樹根最高處。孩子們也不追逐嬉戲了,都圍攏到李大爺身邊,纏著他講故事。李大爺年幼時讀過私塾,肚中有些墨水。他接過別人遞給他的煙袋,點燃一鍋煙,愜意地吸上兩口,就拉開嗓門給大家講“薛仁貴征西”、“牛郎織女”、“白蛇傳”等古老的民間故事。李大爺講故事的水平幾乎稱得上“一流”,用“聲情并茂”這個詞來形容一點兒也不過分。講到高潮時,孩子們便大聲叫好,而講到傷心處,男人女人中就有嘆氣抹眼淚的,而且往往一連幾天都不開心。
夜深了,月兒更明亮了,淡淡的霧氣在四處飄浮。夜色中,所有的景色都在融融的朦朧中微笑。被精彩的故事熏得醉醺醺的人們困了。最先離開的當然是李大爺,他在人們尊敬的目光中飄然而去。而后,大人們領著不甘心又無可奈何的孩子各自離去。只有幾個貪涼而不愿回家的年輕后生往大板凳上一躺,手中的蒲扇滑落,酣然睡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