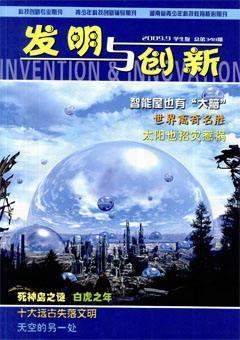科學家巧思種種
王莊林
科學家的特質是好奇與思考。由于好奇,他們不斷地提出問題,再用科學方法解決這些問題,而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發展出各種巧妙的思考方式。
科學方法的步驟
科學家是一群用科學方法解決科學問題的人。所謂的科學方法,包括以下4個步驟。
觀察——觀察是借助一種或多種感官和儀器從環境中獲得資訊的歷程。各種問題都來自觀察,觀察的結果可能是定性的或定量的,定性的觀察不包含數字,定量的觀察則包含數字與單位。
假設與推論——假設是科學家對觀察結果提出的解釋。一個觀察到的現象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假設,它們可能是正確的,也可能是錯誤的。推論是指以現有的信息為基礎,運用邏輯思考推導出的結論,它們可能是正確的,也可能是錯誤的。
預測——科學家根據假設與推論,再運用想象力對可能發展的結果做出猜測,稱為預測。預測可能是正確的,也可能是錯誤的。
實驗與驗證——科學家用觀察或進行實驗來搜集新的訊息,以決定假設是否恰當,預測是否正確。換言之,科學家從觀察或實驗得到的新訊息,來判斷假設與預測的正確性。
宏觀思考
我國古人大都相信“天圓地方”,認為腳下的大地是方形的。西方的古人也認為,人類是生活在一個平面的大地上。只有極少數科學家懷疑這個觀念的正確性,出生于公元前276年的埃及學者埃律吐新尼斯,是第一位用科學方法成功解答這個問題的學者。
觀察——埃律吐新尼斯聽說在夏至,即每年白晝最長的那一天的正午,在錫尼的井中可以看到太陽在井底閃耀。根據這個傳說,他推論夏至當天正午,太陽一定在錫尼市的正上方,這樣它才能從錫尼市的井底閃耀。如果太陽是在正上方,那么直立的柱子便不會有影子。
然而在夏至當天正午,從他居住的亞力山卓城的深井中,他卻看不到太陽的倒影在井底閃耀,而且直立的長柱也會出現影子。他非常小心地量出陽光與柱子的夾角是7.12°,大約是360°的1/50。
由于好奇心的驅策。一年之后,埃律吐新尼斯前往距離亞力山卓城800公里的錫尼市,查看有關太陽在井底閃耀的傳言是否屬實。在夏至那天正午,他低頭往錫尼市的深井一看,果然看到太陽的倒影在井底閃耀,同時直立的長柱沒有影子。
假設與推論——如果人類居住生息的大地是一個廣大的平面,則在夏至那天的正午,太陽光直射而下時,在大地上的任何城市,直立的柱子都不會有影子。
埃律吐新尼斯在夏至正午,觀察到在錫尼市的直立柱子沒有影子,但在亞力山卓城直立柱子卻有明顯的影子。因此他推論,大地不是平的,地面可能是彎曲的,換言之,大地可能是個球體。
預測——埃律吐新尼斯根據觀察的結果,推論大地可能是個球體。如果把亞力山卓城及錫尼市的兩根直立的柱子想象成兩條直線,把這兩條直線向地下延伸,它們應會在地球的中心相交,且交角與亞力山卓城的柱子和夏至正午時陽光的夾角應該相同,都是7.12°。于是埃律吐新尼斯用以下比例式,算出地球的圓周大約是4萬公里。
地球的圓周:亞力山卓城至錫尼市的距離=360°:7.12°地球的圓周=(亞力山卓城至錫尼市的距離)=(800公里)×(50)=40000公里
驗證——每年夏至正午,埃律吐新尼斯都到不同的地點,觀察并測量直立長柱的影子,并用前文所述的方式估算地球的圓周,結果在不同地點算出的值都非常接近,約為4萬公里。由于經過錫尼市不同方向的圓周都約為4萬公里,因此,埃律吐新尼斯確信地球是個圓周4萬公里的圓球。
然而,古代的人無法驗證埃律吐新尼斯的假設與推測正確與否。直到1519年9月,葡萄牙貴族麥哲倫率領一支由5艘大船、200多名水手組成的艦隊,從西班牙出發,橫渡大西洋到達美洲,穿過美洲南端的海峽進入太平洋,又穿越印度洋,繞過好望角,在1522年9月回到西班牙,第1次用實際行動證實地球是圓的。
到了20世紀,科學家利用人造衛星觀察到地球是個球體,并且實際測量得到經過地球兩極的周長是40,008公里,與埃律吐新尼斯在公元前3世紀以思考方法算出的結果完全一致。
先前提到,埃律吐新尼斯從觀察800公里之內的現象,把思考的范圍擴大到整個地球及部分太陽系。他利用宏觀思考能力,不僅推論出地球是圓的,還準確計算出地球的圓周。
后來,他繼續用宏觀思考正確畫出尼羅河的流經路線。編制一套包含閏年的歷法,并且利用月蝕資料估算出地球與月亮,以及地球與太陽之間的距離!
定量思考
古代希臘哲學家認為世上一切物質都是由4種元素——土、水、火及空氣,以不同的比例組成的。他們相信,每種元素都是兩個性質的組合,例如水是濕與冷的元素,土是干與冷的元素。他們認為如果用千的性質取代水中濕的性質,水就能轉變成土。
直到18世紀,歐洲許多科學家仍然相信這個觀念。他們用玻璃器具裝水,在長時間加熱之后,發現水中有泥狀白色沉淀物生成。于是用這個實驗結果,推論古希臘人提出的概念“水能變成土”是正確的。
法國著名化學家拉瓦錫也對這個問題極感興趣。為了尋求答案,他決定設計實驗,仔細觀察水經過長時間加熱生成沉淀的現象,用科學方法尋找問題的正確答案。
觀察——拉瓦錫先把水蒸餾了8次,再把這些水和蒸餾瓶分別稱重,接著把蒸餾水放入已稱重的瓶中,加熱驅除其中的空氣后,以玻璃塞密封,再重新進行稱量。然后加熱至攝氏六七十度,蒸餾水產生的水蒸氣會在蒸餾裝置上端冷凝,又回到蒸餾瓶中,因此在實驗過程中,水蒸氣并不會逸出蒸熘裝置外。
拉瓦錫從1768年10月24日開始實驗,使水溫保持在60℃~70℃之間。一個多月之后,水開始混濁,到了12月中,已有白色沉淀物生成,這些沉淀物隨著時間越來越多。直到1769年2月1日,拉瓦錫才把熱源關閉,讓蒸餾瓶裝置、蒸餾水及白色沉淀物自然降溫至室溫,再分別量稱它們的重量。他發現水的重量并未改變,但蒸餾裝置重量減輕了,減輕的重量等于沉淀物的重量。
假設與推論——在101天的實驗過程中,水的重量并沒有改變,因此,拉瓦錫推論“水不會變成土”。實驗結果又顯示,實驗后蒸餾裝置的重量加上實驗過程中生成沉淀物重量,等于實驗前蒸餾裝置的重量,因此,拉瓦錫推論沉淀物來自蒸餾裝置。換言之,實驗過程中產生沉淀物,是蒸餾裝置中一部分玻璃溶解所產生的。
預測——拉瓦錫認為實驗產生的沉淀物來自玻璃,預測這沉淀物的所有元素都應包含在蒸餾裝置的玻璃中。
實驗與驗證——拉瓦錫的朋友、瑞典化學家舍勒,分析了這個沉淀物的成分與玻璃的成分,發現玻璃果然包含沉淀物中所有的元素。這實驗結果證實,沉淀物是來自玻璃,而不是水變成的“土”,因此,拉瓦錫的推論“水不會變成土”是正確的。
在18世紀,受煉金術的影響,化學家只注意定性的事物,也就是什么物質與什么物質反應后,會產生什么,很少有化學家從事定量的觀察與思考。而且多數科學家相信德國化學家貝歇爾和施塔爾共同提出的燃素學說。
先前提到的實驗使拉瓦錫堅信,精確測定重量是發現真理的基本法則,因此,他自行開發高精確度的大型天秤,并使用這個天秤測量肉眼可見的生成物,也測量肉眼看不到的物質。具體的方法就是,在完全密閉的裝置中進行實驗,精確地測量反應前、后各種反應物與生成物的重量,并且用定量思考改正過去錯誤的理論與學說。
從1769年2月~1777年9月,他用前述的方式不斷地在完全密閉的裝置中從事燃燒反應,在反應前與反應后,準確測量所有反應物與生成物的重量,并用定量思考徹底推翻燃素論,代之以自己創立的氧化學說。此外,他從過去所有定量實驗的結果歸納出“質量守恒定律”:在化學反應中,反應前、后物質的總重量應是相等的。
拉瓦錫的定量思考,使化學這門科學由物質的定性研究進入到定量研究的新階段,拉瓦錫也因此被尊稱為近代“化學之父”。
- 發明與創新·中學生的其它文章
- 癌魔,消失!
- 多功能防塵掃帚等
- 道德課等
- 大學食堂師傅的無敵自傳
- 僅有“刻苦”是不夠的等
- 生命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