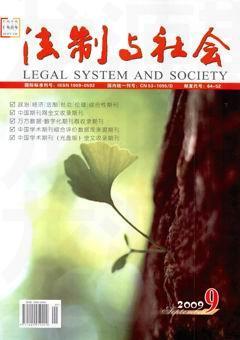刑法是否需要增加“醉酒駕駛機動車危害公共安全罪”
陳玉和
摘要近期酒后駕車肇事受到社會廣泛關注,有人建議修改刑法,增加新罪名。文章結合成都孫偉銘案,指出現行刑法規定已經起到維持社會秩序的機能,現行的法律法規對交通肇事行為的規范比較完善,刑法不需要增加與交通肇事相關的新罪名。
關鍵詞酒后駕車 量刑 新罪名
中圖分類號:D91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0592(2009)09-331-02
近期成都孫偉銘和南京張明寶酒后駕車撞人案引起了強烈的民憤,在聲討醉駕者后,一些人開始試圖通過修改刑法以加大對醉酒者的打擊力度。濟南的六名律師和成都的兩名律師以法律人特有的敏感性,憂心匆匆地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上書,建議在刑法修訂案中增加“醉酒駕駛機動車危害公共安全罪”,稱“只要酒后駕車,酒精含量達到醉酒的標準,就應該構成犯罪”,并強調“不以嚴重后果為構成要件”。
上書人主張增加“醉酒駕駛機動車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理由是:1.酒后駕駛發生的重大交通事故案件層出不窮;2.《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處罰較輕;3.刑法中規定的交通肇事罪處罰力度不夠。
筆者認為,現有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對酒后駕駛和醉酒后駕駛有明確規定,加之刑法有危害公共安全罪和交通肇事罪作保障的情況下,不宜增加“醉酒駕駛機動車危害公共安全罪”。
一、現行刑法規定已起到維持社會秩序的機能
社會上的人是很復雜的,并非都能循規蹈矩,因而在人類共同社會生活中,擾亂社會秩序、危害共同生活安全的有害行為自然難免發生。為了防止危害社會秩序的行為,刑法將一定的危害行為規定為犯罪,并規定了相應的法定刑。人們據此可以確定什么行為是適法,什么行為是違法犯罪,而規范自己的行為,社會秩序因而可得以維持。維持社會秩序當然不僅依靠刑法,其他法律以及道德、習慣等各種社會規范也擔負著這種機能。
1979年刑法對交通肇事罪作出了比較明確的規定:從事交通運輸的人員違反規章制度,因而發生重大事故,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惡劣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非交通運輸人員犯前款罪的,依照前款規定處罰。與1979年刑法相比,1997年刑法提高了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按照三個等級設置量刑幅度,最高可判15年。對于過失犯罪,應當是罰當其罪了,并無可譴責之處。應當說,我國刑法對交通肇事的規定,無論是從維持社會秩序方面,還是懲罰與教育和保護社會法益等方面都十分明確,起到了保障法的作用。
二、現有法律對交通肇事行為的規定比較完善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條對酒后駕駛和醉酒后駕駛的處罰已經有明確的規定。需要注意的是,對酒后駕車和醉酒后駕車造成嚴重后果的應當追究駕駛者的刑事責任,這是由刑法作為保障法的特殊性質決定的。詳言之,對一般酒后駕車或醉酒駕車的,只需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處罰即可,但如果上述行為造成嚴重的社會后果,則根據刑法的相關規定定罪量刑。
我國現行刑法第133條規定了交通肇事罪,法定刑設為三個層級,十分清楚。最高人民法院在2000年就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頒布了司法解釋,其中對酒后駕駛有明確的規定:酒后駕駛機動車輛造成一人以上重傷的,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所以,對于醉酒入刑的問題也已經有法可依。
現行刑法已經有“以危險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刑法第214條和215條明確規定了以危險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其最高法定刑是死刑。該罪是一個獨立的罪名,其要義是:1.其他危險方法,是指放火、決水、爆炸、投毒之外的,但與上述危儉方法相當的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方法。這里的其他危險方法包括兩層含義:一是其他危險方法,是指放火、決水、爆炸、投毒以外的危險方法;二是其他危險方法應理解為與放火、決水、爆炸、投毒的危險性相當的、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方法,即這種危險方法一經實施就可能造成或造成不特定多數人的傷亡或重大公私財產的毀損。2.主觀方面表現為故意。實踐中這種案件除少數對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持希望態度,由直接故意構成外,大多持放任態度,屬于間接故意。成都孫偉銘案和南京張明寶案即屬于間接故意,其醉酒駕車的危險性在客觀上與放火、決水、爆炸、投毒的危險性并無區別,應當以危險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對其定罪量刑,而不適用交通肇事罪。如果酒后駕車,以危險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符合本罪犯罪構成要件的,則以本罪定罪量刑。
這里需要對成都孫偉銘案作簡要分析。在8月11日上海市律協刑事法律研究委員會組織召開交通肇事熱點法律問題研討會上,多數與會律師認為,成都孫偉銘案的定性存在問題,將酒后駕車認定為故意犯罪失之武斷。筆者認為,成都中院對該案定性準確,量刑恰當。其理由是:1.主觀上,孫偉銘作為具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的人,明知必須取得駕駛執照后才能駕駛機動車輛,但其卻無視公共安全,長期無駕駛證駕駛機動車輛并多次違反交通法規,反映出其對交通安全法規以及他人生命、健康或財產安全的蔑視。事故發生后,孫偉銘沒有積極實施救助,繼續逃逸。上述事實充分證明,孫偉銘無視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健康和財產安全,明知會發生嚴重后果卻沒有將車停下來,仍放任危害結果的發生,其主觀故意非常明顯。2.客觀上,孫偉銘醉酒后駕車行駛在車輛、人群密集之處,其行為已對公共安全構成直接威脅;孫偉銘在發生追尾的交通事故后,仍繼續駕車高速(下轉第335頁)(上接第331頁)逃逸,后沖過絕對禁止超越的道路中心黃色雙實線,以超過限定速度一倍以上的車速沖向相向行駛的多輛車輛,造成4死1重傷,公私財產損失達數萬元的嚴重后果。根據我國刑法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對孫偉銘以“以危險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來定罪量刑是完全正確的。從本案可以看出,犯罪過程的細節不僅對量刑有影響,有時對整個案件的定性也有決定作用。
必須明確的是,現行刑法第18條第4款明確規定,醉酒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該規定至少有兩條含義:一是不因醉酒者的認識能力和控制能力可能降低而因此與其他犯罪人有所區別;二是醉酒者犯罪應當依照犯罪構成,追究其相應的刑事責任。因此,對醉酒者的犯罪行為作刑法上的評價時,依據的是刑法的犯罪構成,而不是依據犯罪主體是否為醉酒者。
三、刑法中增加交通肇事新罪名無實際作用
有輿論認為,現行刑法不足以威懾打擊酒后駕車、飆車等惡性違法事件,應將“醉酒駕車、飆車危害公共安全罪”寫入刑法。筆者認為,這完全沒有必要。早在20多年前就有類似的案例。1982年1月10日,北京天安門廣場上人來人往。突然一輛轎車猛地沖向人群。所過之處,有人被碾入車底,有人被騰空撞出。事件共造成5人死亡19人受傷。當時在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工作的周道鸞主審此案。當年的罪名還不規范,法官一致認定,肇事者的行為危害了公共安全,最后的罪名是“以駕車撞人的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致人重傷死亡罪”。1997年刑法修改時,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1997年刑法“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中的“危險方法”包括任何危險方法,醉酒駕車、飆車等行為當然涵蓋其中。如果查證了主觀狀態屬于間接故意,即可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刑法設立本罪的旨意就在于,隨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不斷發展,犯罪分子會變換新手法,出現新的犯罪形式,刑法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把所有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危險方法羅列出來。如果在刑法中增加“醉酒駕駛機動車危害公共安全罪”,以后出現吸毒后駕車危害公共安全、夢游者駕車危害公共安全也單列新罪名。如此這樣,刑法會很不穩定,有失其威嚴性。
值得討論的是,在8月11日的研討會上,絕大部分與會者還認為醉酒駕駛應當入刑。筆者對此觀點不敢茍同,其理由是:1.犯罪的本質特征是社會危害性,如果醉酒駕駛沒有造成嚴重后果,自然對社會的現實危害性就比較小,因此醉酒駕駛犯罪化缺乏法理依據;2.刑法是其它部門法的保障法,只有在其它法律法規對醉酒駕駛無法調整時,刑法才能將其予以犯罪化;3.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已經對酒后駕車致人重傷的行為入刑了。
需要強調的是,我國現有法律法規對醉酒駕駛已有明確的規定,目前主要的問題不是立法問題,而是在現有法律框架下嚴格執法。我國的酒文化淵源流長,應酬已成為商場和官場社會交際的潛規則;同時交通主管部門的執法不嚴和選擇性執法在客觀上助長了交通肇事。成都交通肇事案中孫偉銘在短短半年時間里就有10余次違章記錄;南京張明寶醉駕案,當事司機在案發前更是有多達80余次違章。他們都是在案發后才得以繩之以法,案發前這么多不良記錄為何就沒有被處理呢?這些問題不解決,即使立再多法律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由醉酒駕駛帶來的問題。
綜上所述,我國現有法律法規對醉酒駕車已經有清晰的規定,我們不能因為某種社會現象在一定時期被廣泛關注,或者引起了民憤就要修改刑法,增加新罪名,這既不符合刑法本身的需要,也不符合刑法謙抑性的國際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