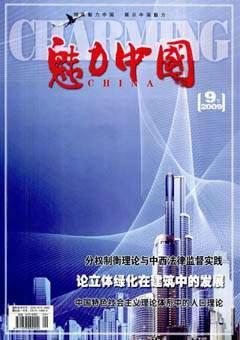檢察監督權立法現狀的考量及路徑選擇
王 瑛
一、現有檢察監督權立法體系的考量
第一,上位法不明與下位法缺失。憲法雖然規定了檢察機關是法律監督機關,但是并未明確規定檢察機關職權的性質與內容。這導致依憲制定的《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受其原則性、概括性所限,不能對檢察機關檢察監督權做出翔實的規定。
第二,立法條文散亂,缺乏系統性。現有有關檢察機關具體職權的規定主要散見于《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監獄法》、《人民警察法》等法律之中。另外,最高院、最高檢的法律解釋中也散落著零星的檢察監督權的權能。由于沒有《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的統領,各訴訟法規定的監督權能失衡。
第三,立法體系多有空白,漏洞百出。第一,分監督權能有法無據。檢察監督權有憲法授權卻無條文依據。第二,使監督權有原則性無可操作性。部分檢察監督權被原則性的授予了檢察機關卻少有被行使。第三,察監督有權力無拘束力。部分檢察監督權的有行使的路徑,但沒有相應的法律結果,導致檢察監督權沒有權威,收效甚微。
由于立法現狀的主要缺陷在于尚未形成較為完善的立法體系,因此產生的弊端顯而易見:檢察監督權的法律淵源遭疑,察監督權的權威性受損。
《憲法》作為檢察監督權最根本的形式法律淵源過于原則;《人民檢察院組織法》作為最重要的形式法律淵源卻立法滯后;其他訴訟法部門檢察監督權立法空白,檢察監督權的具體范圍只能利用人民檢察院出臺的相關文件和解釋加以規制,或者直接在檢察理論上的尋求支持和突破,因而其形式法律淵源備受爭議,直接導致部分權能不為被監督機關所接受。再則,因制度設計的缺陷,部分監督權能的行使程序及法律后果尚未制定,無法律拘束力更降低了監督的權威性。
二、檢察監督權立法的路徑選擇
(一)分權制衡精神下的改良主義
以完善修復的態度鞏固檢察監督權的立法權威,必須堅持以權力制衡權力的精神理念來來指導立法。我國的政治體制是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行政機關、審判機關以及檢察機關,后三者機關應向人民代表大會負責,可以說,這其中體現權力制衡的精神是毋庸置疑的。并不是只有西方“三權分立”的思想才是最徹底的制衡精神。我們不能把制衡學說等同于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權分立。“前者是由一種政治、法律思想發展而成的理論學說 ,后者則是運用這一理論學說所確立的國家政治體制。1而“將分權制衡理論與我國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職能聯系起來加以探討,對于充實我國檢察制度的基礎理論,對于正確界定我國檢察權的性質,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2筆者認為,分權制衡理論才是檢察監督權最深層次的法律淵源,在現有立法框架內以強化制衡為目標健全薄弱環節,彌補不足之短才是鞏固監督權權威最直接的途徑。
從立法形式的角度看,必須建立檢察監督權的多維立法體系。亟需對立法金字塔最上層的《人民檢察院組織法》進行大刀闊斧的修改,使其成為下位法的設置監督權能的合法依據,同時,促進同階位法律的早做修改,將監督權能規范到各訴訟法等領域以及其他法律部門。各部門之間的權能設置、行使程序相互呼應。建立統一于《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的、多層次的的立法體系,完善檢察監督權各階位、各方位的形式法律淵源。
從法理的角度看,必須完善檢察監督權的制度設計,細化程序規則、明確法律后果。“法律規范是評價人們行為是否合法的標準,是指引人們的行為、預測未來行為及其后果的尺度,同時也是制裁違法行為的依據。”3檢察監督權必然規制法律后果才能成為法律規范被加以遵守。
以分權制衡的態度,從現有立法的薄弱之處入手進行立法改良,才能真正為檢察監督權的各項權能正本清源。
(二)有限監督原則下的擴張之路
有學者說,“檢察制度在過去恢復重建三十年是在訴求法治和司法改革語境下檢察制度全面發展的三十年。”4今天,檢察制度的發展仍然在這個語境之下。只是改革的重點落在了強化法律監督的問題上。曹建明指出“檢察監督全面強化對訴訟活動的法律監督。加強法律監督的薄弱環節。強化刑罰執行和監管活動監督,高度重視對民事審判、行政訴訟活動的監督, 依法監督糾正裁判不公、侵害人民群眾正當權益等問題。增強人民群眾對司法的信心。”
隨著分權制衡理論的強化以及司法改革的推進,檢察監督權的擴張是一個必然趨勢。以何種立法形式、立法內容來確立更多的檢察監督權權能成為立法體系的發展課題。
但過猶不及,檢察機關的權力過大,造成控、辯、審三方的訴訟法律關系失去平衡,有悖于分權制衡原理和訴訟公正原則。《憲法》所規定的各司其職、獨立審判等原則同時制約著檢察監督權的擴張,檢察監督是一種程序性的監督機制,它并不是要凌駕于審判機構或偵查機構之上,對于其監督權能的限制必須不違背審判獨立原則以及不與偵查職能相沖突。因此,以有限監督原則為約束合理擴張檢察監督權成為新出路。
例如,以限監督為原則,學者提出的一些檢察監督權能——提請違憲審查權6、執法督促權、偵查取證權等等監督權能應該予以否定。
提請違憲審查權賦予其對所有立法、司法、執法的法律監督本身就是違背憲法各司其職以及權力制衡的精神,而且將專門的監督混同于一般的法律監督,是對監督權的無限擴張,也就無所謂是檢察監督還是一般意義上的法律監督。而對于行政部門適用法律的監督,筆者認為檢察機關沒有必要事必躬親,也沒有能力監督涉及社會管理方方面面的行政行為。只有當行政行為進入了訴訟程序,檢察機關才對行政行為進行審查監督。
有學者支持賦予檢察機關一定的偵查取證權,甚至是代位偵查權7。它可以在立案監督、偵查監督無法取得實效的前提下行使偵查取證的權力,它可以在民行審判監督程序中為查明案件事實而行使偵查取證權。筆者認為該項權能違背了有限監督的原則,對此持否定態度。在審判機關的視角下,“檢察院對法院的民事審判活動實施法律監督,其實質就是以檢察權(或監督權)對法院的審判權進行干預,目的是通過這種干預影響法院的裁判(要求法院撤銷其原判,重新改判)。”8的確如此,這就是檢察監督的目的,但檢察監督權必須遵循有限監督的原則,檢察機關職能扮演抗訴程序的啟動者的角色,不能參與案件的實體審查,不能代表任何一方當事人陳述觀點進行辯論,只履行程序性的職能,比如在民行抗訴中宣讀抗訴書。有限監督原則下的檢察監督權不能與審判獨立相悖。因此,必須否定對于案件實體調查取證的權力。當然,檢察機關代表國家提起民行的公益訴訟不能排除其調查取證的權力。為擺脫檢察機關對偵查監督后續制約措施乏力的弊端而賦予其偵查權,是飲鴆止渴。檢察機關不能違背憲法越俎代庖,只有探索新型警檢模式,確立“檢察引導偵查”的新思路,才是可取之道。
三、四步位漸進式立法體系漸進式的構想
(一)改良上位法
完備的立法體系必然是由主要法律所統領的網狀立體的立法系統。這是一個自上而下發展的立法金字塔,最上端的立法出于最高階位,是最為重要的法律淵源。因此是完善上位法是第一步。必須修改滯后的《人民檢察院組織法》,規定檢察監督權的范圍包括應對刑事訴訟、民事訴訟、行政訴訟三大訴訟活動的監督,同時明確監督范圍包括庭審活動監督、審判監督程序、以及執行監督以及其他權能的兜底條款。同時,確立有限監督的原則,指引監督權立體的科學發展。如此,各訴訟法可以與之相銜接。
(二)完善“主體法”
在前面的闡述中,筆者利用“三分法”將檢察監督權分成了三個方面,最終目的在于首先將以公訴權為中心的檢察監督權加以完善。檢察機關參與刑事訴訟的過程,其監督權能的設置相對完備,以此為其他訴訟法的參照物最適合不過。將刑事訴訟程序從立案監督、批捕審查監督、庭審監督、程序內抗訴監督和執行監督,加以梳理,明確各項監督權能的行使規程,在刑訴法中加以規定,將檢察監督權立法的一個質的飛躍。同時,在民事訴訟法以及行政訴訟法中逐步完善審判監督機制,積極擴張檢察監督權的權能,填補立法空白,規定與刑訴法相呼應的檢察監督權,包括有限的調查取證權、調閱卷宗權、民行審判過程的監督權、對民行裁判執行的監督權。
(三)完備“輻射法”
其他相關的法律如《監獄法》《人民警察法》等等作為主體法的輻射法,必須設置相應的檢察監督權能,以及規定有相應權能的行使程序,以提供檢察監督權行使的方法和途徑。只有輻射法更完備,立法體系的網狀結構才會更加堅不可摧,更具權威性。
(四)細化下位法
原則性的法律設置權能,規范程序。但到實務操作中必然被轉化為操作流程,因此以下位法或司法解釋、文件形式規范檢察監督權的流程為細化上位法和主體法的重要手段,也使得檢察監督權更具可行性,推動監督權立法體系的進一步發展。
(作者單位:杭州市江干區人民檢察院)
1 曾龍躍:《制衡學說與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職能 》,孫謙、劉立憲.主編:《檢察論叢》,第一卷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版,P64
2 石少俠:《論我國檢察權的性質:定位于法律監督權的檢察權 》,《法制與社會發展 》, 2005(3),P98
3 張文顯主編:《法理學》,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P10
4 何勤華 張進德:《中國檢察制度三十年》,《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08(08),P3
5 曹建明:《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檢察事業新局面》,《求是雜志》,2008(18),P13
6 “對一切違反憲法精神和法律規定的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地方性法規和司法解釋,檢察機關都應當有向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提請審查的權力。”——張智輝:《檢察權研究》,中國檢察出版社,2007年版,P327
7 劉晴 趙靖:《檢察科學權配置問題研究》,《西南大學學報》,2008(7),P106
8 黃松有:《檢察監督與審判獨立》,《法學研究》,2000(4),P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