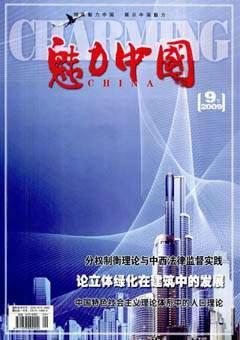社會計劃與市場自由的張力探討
劉穎婷
摘要:面對20世紀西方自由民主文化危機,眾多學者提出了諸多有關西方國家未來圖景的構想,尤以哈耶克與曼海姆的爭鋒論述突出。本文擬對兩者提出的不同的自由民主危機解決方案作比較分析,對其思想的異同作唯實論的描述,以期為現代社會有關社會計劃與市場自由的張力方案提供借鑒意義。
關鍵詞:計劃 自由
20世紀初西方自由民主文化遭遇危機,自由主義政策岌岌可危,極權主義與社會主義運動風起云涌。部分國家如德國、意大利等公開實行法西斯主義政權,而英國等傳統自由民主國家中的國家社會主義思潮亦日占上風。于是,如何處理社會計劃與市場自由的張力成為當時政界與學界共同關注的焦點。
哈耶克作為新自由主義的提倡者,主張古典自由主義,贊同自由競爭體制下政府適度的服務活動;但堅決反對當時盛行的國家社會主義思想,認為其實質上會導致民主國家極權政體的建立。而同樣富于社會道德關懷的德國學者曼海姆,卻為當時的自由民主危機指明了另一條道路。在他看來,現代社會的技術與結構基礎已經改變,必須實行民主控制以實行為自由而計劃的終極目標。哈耶克與曼海姆針鋒相對的言論,可被看成當時不同學術論點爭論的縮影。盡管80年代英國等西方自由民主國家紛紛改變全面福利政策,重返市場從而得以成功擺脫社會危機。但時至今日,現代福利大國仍在同經濟效率和市場自由與社會調節和社會權利之間頑強的張力進行持續不斷的斗爭(Martinelli and Smelser, 1990)。因此,哈耶克與曼海姆之爭對于我們今天仍然具有頗豐的思考價值。
哈耶克由于其經濟學家背景,對西方民主危機的剖析主要從市場經濟的衰落開始。他認為自由民主危機的原因在于自由主義政策的自我毀滅。實際上,哈耶克并不否定計劃本身,他認為從合理計劃事情的意義上而言,每個人不是宿命論者便是計劃者。但他堅決反對為單一目標而進行的集中式管理。但哈耶克無奈的看到,人們并沒有給國家立法活動以足夠空間,就意欲完全拋棄自由主義政策另尋出路。他認為現代社會流行的國家社會主義不過是一群對自由熱愛的人錯誤信仰的烏托邦思想,它只可能給人們帶來專制。在他看來,社會主義作為集體主義的一個變種,意味著人們以計劃為手段實行所謂的“社會共同目標”。而從個人主義哲學立場出發,不可能存在著一個體現全社會公民不同需求的完整的倫理準則,其結果只可能是聽從于某一特權集團的需求。所謂的“新自由主義”只是消除貧富差距的代名詞,所謂的“平等”只是毫無意義的“較大平等”而非極權主義者提倡的“絕對平等”。哈耶克認為私有制是自由的保障,不能因為追求經濟上的絕對保障而放棄個人自由。“沒有經濟自由,就沒有個人與政治自由”。同時,“有意識的控制的可能性只限于存在真正一致的領域中,而在一些領域中必須聽任事情自由發展,這就是民主的代價”。(哈耶克,1993:70)質言之,哈耶克從個人主義角度出發,主張符合法治概念的適度政府活動,以充分發揮自由競爭制度機制的作用。
與此相反,曼海姆將20世紀自由民主文化的危機歸因于現代社會技術與結構基礎的改變。他認為社會結構的危機歸根到底是人的危機,只有平衡個體的理性、道德力量與非理性力量,才可能使自由民主國家避免極權主義的后果。大眾民主化趨勢不可避免的導致理性思維發展低下的人同樣可以走上政治舞臺,從而導致可怕的消極民主現象。而建立在高度分化結構上的現代社會愈益難以承受非理性情緒的沖擊。從發生學上考慮,曼海姆認為現代社會結構的二重性是非理性因素增長的根本原因:一方面受體現在生產和交換技巧之中的計算和妥協的方式支配,另一方面出于外交政策或為統治權而展開內外斗爭乃至訴諸暴力。由于理性與非理性分布的不均衡,大部分人不得不聽從于社會精英的命令,這為非理性暴亂提供了條件。正基于此,曼海姆認為必須實行民主控制。他強調計劃本身并不意味著一致,亦可能導致多樣性,所以計劃是否為獨裁取決于計劃者的意志。他相信西方自由民主思想足以保證計劃水平上的自由。由此可見,曼海姆本身并不反對自由。相反,他強調為自由而計劃意味著公社控制下的計劃結合新的自由的保障措施。
由此可見,兩位學者是從不同側面出發對西方民主危機進行剖析,因此其對自由民主危機的理解及解決思路便出現了難以彌合的鴻溝。哈耶克著重批判了曼海姆有關“對民主政策的控制能夠保證民主的本質”(曼海姆,1940:340)的觀點。“當議會無法對授權機構的目標實行控制時,它不能進行指導,充其量只能選出實際上擁有絕對權力的那些人,整個制度將趨向于全民公決的獨裁制。”(哈耶克,1993:70)從“誰計劃計劃者”的實際操作層面考慮,我們亦可以看出兩者的分歧。哈耶克意識到計劃社會中必然出現“計劃者”的身份,這顯然有悖于自由主義原則,因此極力反對絕對權威出現。而曼海姆在這一點上未置可否,“這一問題既具有宗教寂靜無為的意義,同時也有唯實論的政治之意。”(曼海姆,2002:61)從這一意義上,我們不難看出曼海姆有關“為自由而計劃”圖景的烏托邦色彩;相比之下,哈耶克有關民主危機的解決議案更符合于西方傳統自由民主思想,因而亦最終在現實社會中得以實踐。
當然,哈耶克與曼海姆的學術分歧并不如我們想像中那么大,透過兩者對于“計劃”“自由”等概念的界定,我們可以看到其思想內在的關聯。兩者實際上都批判集中管理意義上的“計劃”與自由放任意義上的“自由”。哈耶克主張自由競爭體制不能放棄適度的政府管理,他所允許的“計劃”是“為競爭而實施的計劃”;曼海姆主張計劃水平上的自由,他所理解的計劃是“保障初始形式自由的計劃”。因此,雖然兩人所支持的“計劃”與“自由”的內涵理解及強調的重心并不一致,但從根本上而言,他們都提倡“計劃”與“自由”的合理結合。
參考文獻:
[1][英]費里德里希·奧古斯特·哈耶克著,王明毅、馮興元等譯 通往奴役之路[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2][德]卡爾·曼海姆著,張旅平譯,重建時代的人與社會[M]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
[3]Martinelli, Alberto and Neil Smelser. Economy and Society:Overviews in Economic Society. London:Sage,1990.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社會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