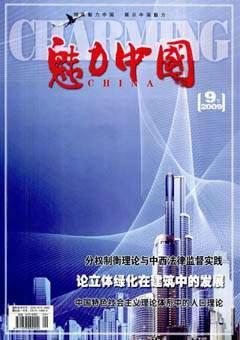語文課堂與情境創設
魯 敏
情境教學,指在教學過程中為了達到既定的教學目的,從教學需要出發,引入、制造或創設與教學內容相適應的具體場景或氛圍,引起學生的情感體驗,使學生在情境中動情,在情境中共鳴,潛意識地進入學習狀態,幫助學生迅速而準確的理解教學內容。它具有以美為突破口,以情為紐帶,以思為核心,以學生活動為途徑等鮮明的特色,對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創新思維及創新人格有著獨特的作用,已經成為中學語文教學中教學創新的主要手段。劉勰在他的《文心雕龍》中就有“情以物遷,辭以情發”的提法;清代王國維在《人間辭話》中也留下“景非獨為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的論述;現代教育家葉圣陶老先生的《二十韻》中也有“作者胸有境,入境始與親”的名言。這些精辟的論述為我們點明了文與道、境與情、潛心會文與入境悟神,語言文字訓練與情感意志陶冶之間的辯證統一的關系,成為我們情境教學的依據。怎樣才能激活課堂,營造出生動活潑的教學氛圍呢?關鍵在于教師要結合課文內容,拓展教學思路,善于創設各種情境,從而吸引學生的注意力,調動學生積極健康的情感體驗,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使學習活動成為學生主動進行的快樂的事情。創設富有情感色彩的課堂情境有那些途徑呢?在教學實踐中,我從以下兩方面進行嘗試。
一、再現人物特定情境,引導學生感知
如果把人作為一種一般具體形象物來考察,他就有以四肢、軀體為要素構成的身材感,以五官為要素構成的容貌感,以妝飾為要素構成的服飾感。而人,不只是“一般具體形象物”,他有思想、有語言、有動作。他的動作能給人動作感,他的語言能給人語言感,甚至他的心理活動也能給人一種心理直感。如果把特定情境考慮進去,我們對人物感知還遠不止這些,它還能引導我們的感官產生從感覺到知覺,從表象到意象的理性飛躍。 ?? ?
1.人總是生活在一定時代的社會情境之中的,他的妝飾容貌、言行舉止、心理思想,都是他對社會具體情境的反應。所以,我們對人的感知要“情境化”。《林黛玉進賈府》中的林黛玉,外貌給人一種柔靜美,人見人愛,更是外祖母的“心肝兒肉”,然而,她進到賈府為何“步步留心,時時在意”,“惟恐被人恥笑了他去”?如果我們創設語文教學情景,通過影視或者表演把這段情境再現出來,我們所感知到的就不只是“如姣花照水,似弱柳扶風”的林黛玉,還能感到她對具體情境的反應。不難看出,這種反應集中為兩點:一是自尊,二是自憐。盡管林黛玉來到的是外祖母家,外祖母家給她的也是很親情化的接待,但她不可能有十足的“回家”的感覺,她仍然覺得自己是個“客人”。所以,家庭變故,以及對賈府周圍人際關系的直覺反應,必然生出寄人籬下之感。注意到這兩點,林黛玉的形象特點便會在我們腦海中浮現出來。
2.人的一切言行舉止、神情面貌都是人的心理的直觀顯現,都是人的意識對周圍世界的反映。所以,我們對人的感知要“心理學化”。《祝福》中的祥林嫂,痛失愛子阿毛之后,對人反復訴說“我真傻,真的”這樣一句話。教學情境中的“此情此境”讓我們把這有聲語言的話題意義置于問題之外,進而引導我們從這有聲語言進入到她那無形的內心世界,看到她那一顆飽受傷害、屢遭打擊、精神幾乎崩潰的心在跳動。
3.我們還應看到,作為“社會的人”,他的一切社會行為都是一種理念行為、目的行為,都是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客觀顯現。所以,我們對人的感知還應“理念化”。《項鏈》中的路瓦栽夫人,她的人生悲劇絕不是借項鏈丟項鏈這樣一個偶然事件造成的。丟項鏈是偶然的,但偶然中包含著必然。她為何要去借項鏈,從她人生理念看,妝飾是一種身份,富貴是一種幸福,舞會上出盡風頭更是一種榮耀。為此妝飾自己,這是目的。如果我們利用課本劇形式創設教學情境,把路瓦栽夫人搬上“舞臺”,那么一個羨慕虛榮、追求奢華享樂的瑪蒂爾德就會深深刻印在我們腦海中。不難看出,瑪蒂爾德的悲劇是她人生理念的悲劇。
總而言之,再現人物特定情境,是讓教材提供的人物形象在特定環境中活躍起來,情境教學就是通過這些活躍在特定環境中的人物給人直接感知,從而達到教學目的。
二、創設景物情境,引導學生體會
景物情境一般是指作為觀賞對象的景致和事物。它包羅萬象,山河湖海、亭閣臺樹、竹木花卉、鳥獸蟲魚,都可納入我們創設的教學情境中。這些景物通過它的形式要素形狀、質地、顏色、聲音等作用于人的感官,在人的腦海中形成形狀感、質地感、顏色感,聲音感等等。而且,我們在情境教學中發現:當我們把這些客觀景物放置到一定的“形象場”中時,這些客觀景物就會變成有內涵、有情感、有靈性的東西。我們再看它時,就感覺它不只是有外觀的形、質、色、聲,還有深刻的內涵和躍動的靈性。
1.聯想與景物情境有關的人事,引發對歷史和人生的感悟和思考。 《土地》一文,作者借助文字把我們帶入或鳥瞰或平視或觸摸土地的特定情景之中。假設我們因文選境,僅僅帶領學生立于“萬里平疇”,手捧“泥土”,卻不能引導學生進入與“此情此境”有關的歷史人事的特定環境中,學生“思想的野馬”是很難馳騁到“很遠很遠的地方”的。他們除了抒發“啊!肥沃的土地,遼闊的原野,我熱愛你”的贊嘆外,還能說什么呢?假若我們能告訴他們:這里,黃世仁曾強占過民女,劉文采曾鞭打過農夫;這里,曾燃起過秋收起義的烈火,曾拋灑過抗日勇士的熱血。這樣他們的目光會變得深邃起來,懂得:原來“土地也是這般深沉”。
2.觸發他們對與景物情境審美體驗,加深他們對眼前景物的審美和品味。《雨中登泰山》一文,泰山青松蒼翠挺拔,生機勃勃,各具情態,表現出獨特的自然美。但是,凝神一想,我們對眼前景物青松的美感似乎還不止這些,還有一種神韻體味未透的感覺。這時,我們不妨想一想,作者納青松于筆端,應該與他特定的思想情懷有關。作者那種由心儀泰山自然勝景、人文景觀而孕育激發的撲向自然、親擁泰山的情志和精神已經在“雨中登泰山”中表現得淋漓盡致了。一位善于體察自然的文壇老將,又以他敢于在風雨中攀登十八盤的親自體驗,面對著一棵棵“扎根于懸崖縫隙”、“和狂風烏云游戲”的泰山蒼松,怎能不鐘情于這些“泰山的主人”呢?所以在作者眼中,泰山不僅表現出一種獨特的自然美,更表現出所有泰山人的精神美。
3.引導他們由景物情境而聯想宇宙人生,引發他們對人與自然關系的審視和感悟。人類和自然宇宙緊密相聯,宇宙自然以其博大胸懷涵納人類萬物。《風景談》一文說得好:“自然是偉大的”,“然而人類更偉大”,“人類的高貴精神的輻射,填補了自然界的貧乏”,“人創造了第二自然”。我們都很欣賞大作家的藝術表現力。二三十棵桃樹,半盤磨石,幾尺斷碣,還有喬麥和大豆玉米,作者就用這些隨處可見的東西描繪出一幅人與自然的最和諧的圖畫。大自然以它特有的綠陰和溫馨蔭蔽著這些可愛的青年,就像母親擁抱著嬰兒。誰能不為之感動呢?
(作者單位:華東師范大學河南省永城市實驗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