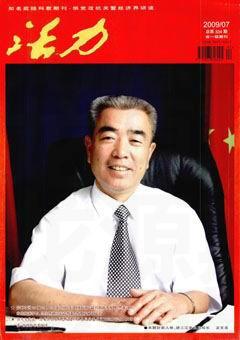上海地區外來勞動力流動特征及因素分析
田亞男
多數實證研究文獻一般運用工資和就業前景的作用來解釋勞動力遷移的模式,目前針對于具體地區的勞動力遷移的文獻不多,主要原因是缺乏數據。Bojas指出 ,移動不僅對工資水平做出反應,而且也可能因為不同地區之間勞動技能水平的差異,學習技能也成為勞動力遷移的目的。相對平均化的工資水平可能吸引勞動技能較低的勞動者,而擁有較高技能的勞動者會選擇收入差異較大的地區作為目的地,因為那里有更高的勞動技能回報。根據上海地區的特點,目前可以影響外來勞動力流動因素主要包括:
一、工資調整對于勞動力流動的高度激勵作用
對于上海來說,工資率的增長對于吸引勞動力流入具有顯著的積極效應。上海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上海市統計局發出《關于公布上海市2008年度職工平均工資及增長率的通知》中顯示,2008年度全市職工平均工資為39 502元,月平均工資為3 292元,比上年增長13.8%。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進城的外來勞動力(被稱為“農民工”,或“民工”)從事著與城鎮原來的上海工人(通常被稱為“職工”)迥然不同的工作。他們幾乎占據了許多的非熟練工種:建筑工人和維修工、餐館服務員和辦公樓的保潔員,乃至家庭里的保姆。并且平均來說,掙得低的多的工資水平。
傳統的工資差別理論注意到了技能差異導致的工資差別,但往往忽視技能差異也可能導致職業差異——高技能的從事“白領”工作,低技能的從事“藍領”工作。這種職業差異往往被看成一種“職業歧視”,或者“文化障礙”等經濟理性無法解釋的因素。通過分析表明,這種職業差異具有經濟理性。
二、在勞動力流動的過程中,低技能的勞動者群體容易受到結構性失業的沖擊
與任何現代經濟社會一樣,中國城市經濟也存在著勞動力的異質性的現實。造成勞動力異質性的最主要的因素是勞動力之間人力資本稟賦的差異。勞動力就業前受到的教育程度的高低,就業后技術培訓和工作經驗積累都是產生這種差異的直接來源。
傳統理論與中國現實的矛盾表現在一個關鍵在于假設了勞動力是從事相同的職業,而同一職業的邊際生產率一般來說的確是遞減的。然而,當勞動力從事不同的職業,那么,不同職業之間的相互影響就需要考慮進來。其實,經濟學的傳統理論也認為,勞動分工可以提高生產率。在我們這里,讓不同技能的人從事不同的職業,就可以體現勞動分工的效應。而“民工進城”促成了讓不同技能的人進行重新分工的機會,由此可能提高了生產率,從而部分抵消了勞動力數量增加而導致的邊際生產率遞減——這相當于一種技術進步。也就是說,勞動力流動通過促進流入地區的勞動分工而提高當地的生產率,進而造成地區工資差距的擴大。正如我們一再強調的,這是一個有利的沖擊——不僅有效率(這是傳統經濟學也可以得到的結論),還是公平的,因為是“帕累托改進”。
特別在經濟危機的影響下,失業率高于以往水平,采用什么樣的調整會引起勞動力流入的增加呢?唯一的解釋就是從不同技能的勞動者的流動來考慮。具有相對較高流動性的一般為高技能勞動者,他們對于就業比較有信心,對失業率敏感程度不高。在高水平工資以及較高對于技能回報的吸引下,流向目的地。而在勞動者中比重較高的那些技能較低的勞動者往往會考慮到自身的競爭力、遷移的成本以及尋找工作的不確定性(找不到可以補償成本的理想工作),加之失業率較高,也意味著勞動力市場需求彈性和流動性較低,這對于尋求工作的低技能勞動者并不具有十分的吸引力。這就造成即使他們面臨較高的失業率,也不傾向于到一個需求層次較高的地區去,反而會減少向外的流動。
三、通過調控勞動力市場的需求影響勞動力的流動性
在中國發達的城鎮地區,特別是象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區別一個工人是外來“民工”和當地“職工”的方法出人意料的簡單——觀察他(她)從事的職業。即使是在同一個企業里,這一差別也是明顯的。例如,在某著名高校中,其后勤部門的經理都是具有本地城市戶口的“職工”,而負責各種具體的體力勞動和服務工作的(也許不包括網絡維修這種需要較高技能的職業)都是外地“民工”。同樣在這個高校,你可以看到在許多嶄新的大樓旁邊,有一些簡易的棚屋,里面居住的不用說都是身為“打工仔”的農民。他們當中的婦女則有幸能進入大樓里面,從事保潔等工作。
城市經濟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兩種體制部門。一種是政府控制部門,一種是市場主導部門。這兩種部門在勞動力就業和工資制定方面都存在著明顯的制度性差異。政府控制部門所吸收的就業者主要來自城市勞動力,在招收外來勞動力方面會受到一定的限制。政府控制部門中的就業者一般都享有長期的,甚至終身的就業保障。部門內部的工資受到統一的控制,職工之間的收入差距較小,個人人力資本的報酬得不到應有的補償。職工的一般工資水平具有剛性的特點。與此相反,市場主導部門對外來勞動力的就業不采取歧視的做法,按照市場法則招收和使用勞動力。對就業職工不實行終身雇傭制,企業和職工都可以根據雇傭合同保留著解雇和辭職的自由和權力。企業有充分的制定工資的自主權利,根據職工的勞動生產率和貢獻的大小實行有差別的工資水平。
近期內,應當采取一些措施,減少對外來勞動力和勞動力輸出地區的不公平對待,例如,為外來勞動力提供保險,逐步享受當地居民的一些福利、實現國民待遇,向勞動力輸出地轉移利潤稅收、以平衡經濟利益的失調。
總體上,就上海地區目前的形勢而言,勞動力的凈流入水平與工資率正相關,與失業率負相關。但是高工資地區面臨整體較高的流動性,即高的流入和流出而不是高的流入和低的流出。高失業率不僅限制了勞動力的流入。而且也限制了勞動力從經濟條件惡化地區的流出。如果未來較長一段時間內遭受負面的經濟沖擊,即產出下降、失業上升或者工資下降,則可以考慮通過勞動力的流動性來吸收這種不利影響。一方面,惡化的勞動力市場條件促使勞動力從該地區離開,前往工資較高、前景好的地區;另一方面,低的工資水平和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也將吸引新的投資者,新興企業能夠創造就業,緩和地區的就業形勢,同時提高平均工資水平。□
(編輯/李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