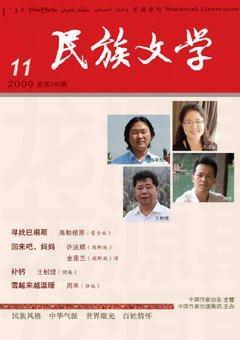和平街的滄桑
潘恒濟(京族)
小小的街道,寬不過五米,兩旁的房子多是二三層的樓房。走在邊城東興的和平街上,給人有一種逼仄之感。再看看街道兩旁那些斑斑駁駁的“古董”民宅,一種歷史的滄桑感油然而生。
然而,和平街卻有著一段輝煌的歷史。
改革開放之初,東興鎮基本上還是老模樣。和平街背靠北侖河,隔岸便是越南,有著得天獨厚的邊境貿易環境。一車車銷往越南、泰國、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的上海、浙江來的布匹,一車車南寧來的啤酒、油毛氈,一車車廣州來的日用百貨,一車車佛山瓷磚……擠滿了和平街。和平街上,搬動貨物的人群肩碰肩,來來往往,大呼小叫,從早到晚忙個不停。一段時間,古老的東興鎮竟云集著七八 萬人。東興鎮家家戶戶成了旅社。在和平街,只要拿出一張席子,扔一個枕頭放在屋檐下、樓梯底,一夜便有人給你10元。要知道,改革開放之初,10元錢可是一個不小的數目啊!看著那些擠擠壓壓的人群,望著那一批批進進出出的貨物,不禁令人聯想起東興那段有著“小香港”之稱的歷史。
那是20世紀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初期,由于抗日戰爭的戰事影響,許多大大小小的商客云集東興。北侖河上十來噸以至數十噸的木帆船來來往往,就停泊在和平街的后面。諸如北海、合浦、靈山、西場的大米、黃麻、桐油、葛薯就是通過這些帆船,一船船運到東興來,又銷往各地去。而當時國內短缺的火油、火柴、鐵釘、鐵線等則由越南(當時屬法國統治)運進東興來。東興成了國內外貨物的集散地,交通發達,人口激增,商業興旺,一片繁華景象。
入夜,一擔擔魚生粥、艇仔粥、及第粥、云吞面、湯圓、水餃、豬腳扣肉糯米飯……走街串巷,隨街叫賣。伴著一聲聲拖長聲尾的叫賣聲,還敲起一聲聲“得得得”的竹板聲。小時候每聽到叫賣聲和竹板聲,心里便癢癢的,嘴巴也饞饞的。那些賭紙牌,打麻將的有錢人家,聽到叫賣聲后,便從三樓放下一個吊籃來:“一碗豬腳扣肉糯米飯,一碗云吞面,一碗魚生粥……”叫賣的按需供應,吊籃扯上去,不一會兒碗和錢又從吊籃放下來,叫賣的便各人收了錢和碗,挑起擔子又一聲聲走街串巷叫賣去了。
和平街初稱仲愷街,是東興最繁華的一條街道。它集吃喝玩樂于一街。短短的百多米小街全是小吃、酒樓、旅社、飯店、咖啡店、賭場。其中最著名的有陳偉記的臘味,金菊園的熟食,“沙蟲王”的咖啡,“合意來”的豉油雞和雞飯。陳偉記的臘味,尤其是雞腎和鴨腎,既香又脆,別有一番風味。金菊園的湯粉,韌而且滑,濃而不膩。“沙蟲王”姓甚名甚,少有人知,人人都叫他“沙蟲王”。“沙蟲王”的咖啡,咖啡籽是他親手炒制的,咖啡粉也是他親手磨研的,制作的工序特別細致,味道特香特濃,口感極好。“沙蟲王”賣咖啡有個特點:他只允許客人一點點地慢慢品嘗,不允許客人大口大口地喝。一次,有位客人要了一杯咖啡,三口兩口便喝完了,說:“再來一杯。”“沙蟲王”見了,就對一個小伙計說,這位客人口渴,你給他倒一大口盅開水。小伙計把一大口盅開水送到客人面前,客人愕然,呆呆地看著那位小伙計。小伙計便對那位客人耳語:“老板不喜歡你這樣喝他的咖啡。”“合意來”的老板姓廖,外號叫“短命鬼”。“合意來”這個招牌,正體現出廖老板的脾氣和稟性。他的豉油雞和雞飯,特別爽滑香甜鮮美。他的雞飯,小小的一碗,一般人至少吃上四五碗才能填飽肚子。可廖老板的雞飯,一個客人只賣一小碗,頂多是兩小碗,要是你再要第三碗,他就對你說:“哈,你識食,別人不識食么?不賣!”他賣豉油雞也是如此,你來買,他先問:“多少個人?”“三個。”嚓!一刀下去,就是那么多,如果你說要多一點,或者指指點點,要這要那。他又是那句話:“哈!你識食,別人不識食么?不賣!”即使當時你憋了一肚子氣,過后你卻忍受不了他的豉油雞和雞飯的誘惑,還是乖乖地來買他的。
正是他這種脾性,他的店名才叫“合意來”;正是他的這種脾性,人們給他外號叫“短命鬼”。然而,我覺得不管是“沙蟲王”也好,“短命鬼”也好,他們都是深諳經營之道的高手。咖啡只有慢慢品嘗才能品出它的真正味道。雞飯就是不讓你吃膩,就是讓你吃得正是嘴饞的時候而止。這正如說書和寫章回小說一樣,關鍵時刻來一句“要知道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你就不得不繼續追下去了。而更重要的是他們對自己高質量的產品充滿自信,皇帝女兒不愁嫁,他才敢于“短命”!也正是因為這樣,他們為當時仲愷街的繁華打出了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和一幅絕妙的廣告。
當然,當年仲愷街最亮麗的一道風景線,應該算坐落在今天和平街的64、66、68號四間的樓房(其中68號是雙鋪面)的“二品樓”。“二品樓”集吃喝玩樂于一身。可以說是仲愷街的一個縮影。它既是旅社,又是酒樓,既是茶樓,又是青樓。“二品樓”一字兒四間鋪面,三層,在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初期,算是宏偉的了。一層右邊為物資庫房、賬房先生住房及一個柜臺。左邊三間大廳早上經營早餐,咖啡、牛奶及早點。中午和下午則經營飯菜及酒席。餐廳臨江,隔岸便是越南的芒街。沿江樹木青翠,江水碧透,異國風光盡收眼底。清風徐來,把酒臨風,別有一番情趣。因此,中、晚兩餐多為大商賈及社會名流所包。晚上則作茶樓之用。供應多為名茶、咖啡、牛奶、雪糕、阿華田。餅點極其豐富,因此,大多也為有錢人所占。“二品樓”之西南隔著兩個鋪面有一賭場,商賈、名流、九流三教云集。賭場再向西南一百來米,便是通往芒街的一座鐵橋。只要持有“過界紙”(相當于現在的邊境出入證)便可隨便來往,因此,走私煙土(鴉片)的,販賣金葉的,多會于此,“二品樓”的生意因而特別火爆。
“二品樓”的廚師多是從廣州聘請,菜肴、糕點極受客人歡迎。尤其中秋月餅,更是聲名遠播。“二品樓”每年的中秋月餅,除銷往防城、欽州以至南寧之外,還遠銷越南的芒街、海防、河內,因此,這些地方甚至東南亞一些國家的商賈無一不知道東興有座“二品樓”的。
時間流逝,歷史遠去。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的東興,已從原來只有0.86平方公里的小鎮發展成為今天占地近8平方公里的縣級市。七八十多米寬的街道,縱橫交錯。歐式、法式、越式、中西合璧式的建筑分布其間,豪華、飄逸、古典、優雅,各領風騷。街道商店琳瑯滿目,高級賓館星羅棋布。新舊兩區,有如新舊兩個世界。新區蒸蒸日上,欣欣向榮的發展,已把當年繁華一時的和平街擠到了一個靜寂、冷落的角落。
漫步在和平街狹窄的街道上,仰望一間間青苔滿布、斑斑駁駁的古老建筑,不禁令人感嘆:滄海桑田啊!信步走進和平街66號,啊,這不是當年繁華一時的“二品樓”所在么?陰暗的廳里,沒有一張椅子、桌子,幾個租住的外來工,就坐在一條幾乎腐朽的木條上,樓板已經脫落,零零落落,一片狼藉,一種衰落感襲上心頭,特別不是滋味。世事滄桑,“二品樓”的形象也隨著房屋的幾度易主而遠去了。
然而,我想,新的取代舊的,進步淘汰落后,這大概也是一種歷史必然吧!不過,歷史發生過的事情,人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沒有過去哪里有現在?沒有歷史,何來的今天?今天過去,也會成為歷史,歷史的發展也會產生新的今天。和平街,給人們留下的豈止是邊城的滄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