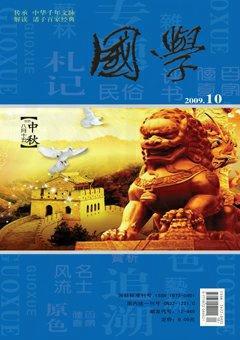史說漢字:方正流長
漢字,見證的是一段古老漫長文明的存續,它以其浩瀚廣博書寫著華夏歷史,以其獨有的魅力影響著世界。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大批外國探險者來到風雨飄搖的中國,他們在大量盜取中國文物的同時,也揭開了這個文明古國一個個塵封地下的秘密。
1922年6月,比利時傳教士凱爾溫在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掘開了遼興宗皇帝的陵墓永興陵,從中出土了遼代哀冊。哀冊就是皇帝、皇后、皇儲的墓志專有的名字,一般的大臣和官員就叫墓志銘。
契丹哀冊的出土讓契丹國文字在失傳數百年之后重見天日。
漢字產生之后,很早就傳播到各少數民族地區和周邊國家,在很長時間里,漢字和文言都是這些民族的正式文字。在長期使用漢字的過程中,各民族逐漸掌握了漢字的結構規律,創造出更適合自己民族使用的文字。
契丹崛起于唐末,興盛于宋,立國后,改國號為遼,逐漸強盛,其疆域東起大海,西至流沙,南越長城,北絕大漠,統治者參照漢字的形體結構創制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
契丹正好處于遼、宋、西夏三足鼎立的割據局面。無獨有偶,在與其相鄰的西夏國,他們的文字同樣是根據漢字創制的。
公元1036年,西夏開國皇帝李元昊命大臣野利仁榮根據漢字的造字特點,參照融合了契丹文字的造型創制西夏文字,三年始成,共五千余字,筆畫繁多,結構繁雜。西夏大力推行西夏文字,翻譯各種漢文經典及佛經,但漢字并沒有因此而廢棄,它與西夏文同時并用,直到西夏王朝的結束。
依然是天蒼蒼,野茫茫;依然是遼闊雄壯,長風浩蕩。 那奔騰而去的鐵馬金戈已無處眺望,那余音已絕的鼓擊鐘鳴也已無處傾聽。斷壁殘垣之間,千年一晃而逝,當曾經的一切都被歷史掩埋,唯有那凝固在石板上的模糊文字記錄著那曾經輝煌的年代。
公元753年,唐。一艘日本商船在風浪中劇烈搖擺,人們尖叫、掙扎,但是最后還是沉入大海。
消息傳到長安,有一個人十分悲痛,他就是詩人李白。悲痛中他寫下這樣一首詩:“明月不歸沉碧海,白云愁色滿蒼梧”,他的好友,日本遣唐使阿倍仲麻呂在回國途中遭遇風暴,失去了消息。
717年,初到長安的阿倍仲麻呂才十九歲,他離開父母、離開家鄉,來到這個當時世界上最繁華的大都市。唐玄宗給他取了一個中文名字,晁衡。
那時長安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有許多像阿倍仲麻呂這樣的外國留學生,大唐政治清明、思想開放、文化繁榮,在國際上擁有無與倫比的美好形象,對包括日本在內的周邊各國都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日本朝野上下出現全面學習模仿中國的熱潮。遣唐使,就是日本皇家為汲取中國先進的政治、經濟、文化而派遣的官方外交與留學使團。
每次遣唐使的人數都在200到500名不等,同時還有10到20名留學生,30到70名留學僧,留學生進入國子監所屬的六學館修習各自的專業,而學問僧則匯集于長安和洛陽的各大寺院鉆研佛法。
在古代,日本只有自己的民族語言,而沒有自己的文字。公元405年,一個叫王仁的朝鮮人帶著《論語》到日本講學,并教授漢字,具有文化修養的日本人開始能用漢文記事。8世紀以前漢字是日本記錄書面語的工具。
遣唐使在長安學習唐文化的同時,也精心研究漢字。據傳,日本遣唐留學生吉備真備和留學僧空海結合漢字創制了日本片假名和平假名。
空海是日本書法史上的重要人物,為書法“三筆”之一。
空海和尚在日本被稱為弘法大師,他的書法在日本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境界。空海在唐朝精研書法,借鑒草書形成新的字母形式,創制了日本平假名。
其實,平假名確實是從中國漢字的草書演化而來的,但并非空海一人所創,它早期為日本女性專用,由于宮廷女人長年抄寫《萬葉集》,而“萬葉假名”的漢字,都有固定字音,寫著寫著,無形中便簡略了漢字,變成類似草書的字體,就成為“平假名”。
學習漢字的日本宮廷子弟或考上大學的精英,為了將漢字念成日本本國固有語音,在漢文旁加上種種拆解漢字而形成的各種助詞與記號,就形成了后來的“片假名”。有傳說,片假名最初的創制者是吉備真備。
由漢字脫胎而來的日本文字,以漢字為素材,并且在應用中與漢字有機結合起來,促進了漢字在日本社會的廣泛應用和深入普及。與漢字相聯系,中國的書法藝術也傳到了日本。
雖然歷史無法確定究竟是誰將漢字改造為日本的文字,但是龐大的遣唐使團無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近300年間,留唐學生144名,其中許多人留唐時間超過了20年,甚至還在唐朝娶妻生子,從生活起居到言談舉止,全與唐人無異。他們在回國后,對日本的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阿倍仲麻呂官至三品,他工于詩文,與李白、王維等同代詩人過從甚密。
753年,離開家鄉30多年,已經55歲的阿倍回國了,他以為能夠再次拜望自己的父母,然而,他的這個愿望卻因為海上的風暴而無法實現。
在那場風暴中阿倍仲麻呂并沒有死。大風將他吹到了安南,最終又回到長安。阿倍仲麻呂卒于72歲,他的墓地至今仍保存于西安興慶公園內,這位日本的遣唐使再也沒能回到自己的家鄉。
在武則天和唐高宗的陵墓前,佇立著64尊藩臣石像,他們所代表的是唐朝的盟國和友好鄰邦。不僅僅是在唐朝,也不僅僅是日本,漢字早已伴隨文化流布四方。
朝鮮文字原來一直用漢字,只不過加上他們自己的讀音,叫做吏讀。越南也是在秦代的時候就跟中國有來往了,他們一直也是用漢文作為他們的文字,一直到后來才發明了自己的文字叫做“字喃”。
東至渤海、朝鮮、日本,南至安南、緬甸,西至西域,北至漠北,這一片廣闊的空間,超越漫長悠久的歷史,用漢字連結了中國與周邊世界的文化,形成了一個漢字文化圈。
隨著周邊各個國家在文化上的崛起和民族自覺意識的產生,一些曾使用漢字的國家先后放棄漢字。韓國創造了自己的訓民正音,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期也提出了廢除漢字,越南也已經實行拼音化。
雖然這些曾經飽受中華文化浸潤的國家如今都有了自己的語言文字,但是,他們語言中仍明顯留有漢字遺跡,朝鮮語、越南語和日本語詞匯的6成以上都是由古漢語派生出的漢字詞組成的,中國文化對他們的影響已經融入到了他們的本土文化里。
公元112年,漢武帝在南越設郡,漢字正式成為越南的文字;公元285年之前,漢字開始在朝鮮應用;公元3世紀左右,漢字的典籍大規模進入日本。
中國,經歷了五千年的民族大融合,一個又一個的民族登上歷史舞臺,現在卻難尋他們曾經的輝煌。
千百年來,世界上不知道有多少文字伴隨著他們民族的遷徙而傳播,有的依然閃爍著光芒,有的早已消失了……
五千年前,埃及人在石碑上刻下他們的故事,古巴比倫的蘇美爾人用形如楔的文字記下歲月,這一切都消逝在時間中,留下今天關于遠古文明的謎。
中華文明具有海納百川、包容萬物的氣魄,歷來以博大的胸襟面向世界,因兼容并蓄而豐富多彩,因推陳出新而永葆活力,因特色鮮明而遠播四方,成為世界四大古文明僅存的碩果。有人這樣說,除中國之外的其他古老文明消亡了,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文字沒能傳承下來。
在中國的歷史上,大量的詩詞詠嘆的都是同一個主題:統一。諸葛亮在《出師表》中寫下了“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說國家的事業不能偏安一隅。后來,東晉占領長江以南,有了“偏安江南”之說;南宋建都杭州,有了“直把杭州作汴州”之語。
有人說,中華民族是一個圓,周長可大可小,圓心無處不在,而半徑就是漢字,漢字就是中華民族的向心力。歷史不斷發展,朝代不斷更迭,可是不管怎么變化,中華民族大一統的國家觀念始終沒有改變,直到現在,一直深深印在每一個中國人心中。
漢字是中華文化的根,也是活化石,她是目前世界上惟一傳承的歷史在3000年以上的古文字,且在發展過程中成為中華文化的代表。
中國人認為世界萬物都是有靈性的,天地、樹木、河流,他們把對自然的認識融入漢字當中,同時將自己的感情嵌入這些筆畫之間。
從遠古演化而來的古老漢字,被人們賦予了超自然的能力,用來避禍求福,一副對聯、一個字謎都是中國人智慧的結晶;一個福字、一個雙喜都寄托了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渴望。大概在我們整個文字生活里面,沒有哪一家、沒有哪一個傳統節日不和文字發生關系。比方說過年的時候,任何一家,在任何一個角落里,不可能不貼對聯的,不可能不貼“福”字的,比如說過去家家都養豬,于是在豬圈上要貼;有馬廄,就是放馬的地方或者放牛的地方,甚至于趕的車也是“日行千里路,人馬報平安”,這樣的對聯都是要貼的,這個貼實際上沒有用語言把它固定在對象上,只有用文字的辦法。文字實際上已經在我們的生活當中占據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回望千年歷史,漢字曾經對中國周邊國家的文化產生過巨大影響。今天,它再次在世界掀起一股中國熱。
2007年12月,第二屆孔子學院大會在北京舉行,來自世界各地的孔子學院代表共一千多人聚集在這里交流辦學經驗。截止到2008年10月,教授漢字、傳播中國文化的孔子學院在全球已開辦292家,孔子學院傳達著漢語漢字的魅力,目前海外學習的人數超過三千萬,到2010年將達到一億,漢字跨越千山萬水、打破千年時間的阻隔,悄然將中國文化帶到了世界每一個角落。
2008年8月8日 舉世矚目的第29屆奧運會在北京開幕,世界為之震撼。數千書童齊誦《論語》,書聲瑯瑯,伴隨著漢簡的出現,蔚為壯觀。
古老的漢字承載著中華文明久遠深邃的歷史。和,一個簡單的漢字,不僅滲透著中國人幾千年來待人接物的處事智慧,更體現了中國思想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遠流長,漢字以其獨特的方塊骨骼支撐起中華文明。
浩如煙海的歷史古籍,氣象萬千的詩詞歌賦,我們的民族歷經磨難卻始終銘記著千百年來信守過的靈魂與信仰。中國漢字古老精深、歷久彌新,它與中華文明一脈相承、血脈相連,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瑰寶,綿延的筆畫書寫五千年的文明興衰;漢字是一個超越時空、生生不息的文化精靈,它將占地球人口五分之一的人們,用同一種符號連接在了一起,它獨有的魅力將會繼續影響著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