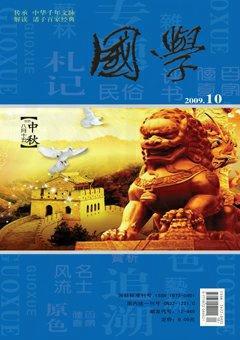屈原,面向風雨的歌者
鮑鵬山
有些歷史人物往往隱身在重重黑暗之中,等待著后人智慧的光芒照徹他們,使他們重新熠熠生輝……
壹
我一直都覺得,屈原之影響中國歷史,不在于他的思想,也不在于他的事功。這兩點他都不突出。屈原之影響后代,乃是因為他的失敗。這是個人對歷史的失敗,個性對社會的失敗,理想對現實的失敗。屈原在他的作品里(主要在《離騷》和《九章》里)淋漓地展現了這種失敗。可以說,在中國歷史上,這是第一次有關獨特的個人與社會、歷史發生沖突并遭致慘痛毀滅的記錄。在此之前的諸子及所謂儒家的六經,都只是對所謂社會秩序、歷史規律的認知,并沒給獨特個體及個性留多少余地,而《詩經》中的為數不多的個性痛苦,也因“怨而不怒,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而暗淡無光。比屈原稍前的莊周已經看出了個性與社會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和沖突的必然性,同時他也悲觀地認識到,在這場正面沖突中失敗的一方只能是個性,故而他避開了社會冷酷的鋒芒,避免與之發生沖突,他幾乎是不戰而退。而比屈原稍后的荀子(注意這三人都與楚文化有關系),則是通過對人性的否定,進而否定個性,否定獨特個體的道德價值,或者說,否定個體在社會秩序之外的獨立價值。唯獨屈子,既要堅持個性,又要堅持以自己的個性去改變世界,以個性的溫熱去融化那冷酷的秩序。因此,他的失敗是一次意味深長的歷史事件,也是人類永恒的悲劇。甚至我們可以把他的作品看成是有關人類自由、幸福的啟示錄。
他以至善至美的古圣賢做自己立身行事的榜樣——天真的屈子并不知道,這些古人的“至善至美”往往只是后人的想象甚至是有意的欺騙,他更不能知道,至善至美往往不能與現實并存。聰明的莊子看穿了這種歷史騙局,他推倒一切圣賢,把他們通通置于他的戲侮之下;犀利的韓非更是從唯物的角度拆穿儒家的美化,把古人推下神壇。而屈原對這些道德幻象則是真誠地信奉,甚至還把自己看成是古圣人的影子,并把自己當成是古圣人意志的現世體現者。由此便出現了這樣的結果:他把君主應當“效法先王”的命題,不經意地就變成了君主應當“聽信賢臣”,應當對賢臣信任、重用,守信而不改。因為這樣的臣子就是先王意志的化身。“先王”由一種抽象的精神傳統具體為一個活生生的人,與君主對峙。屈原就是這樣與楚懷王對峙著。當然,與孟子一樣,他不能明白的還有,道德模范式的圣人及其個人魅力決不是現行體制的對手!所謂的“法先王”,不過是一種幼稚而天真的愿望而已!
當楚懷王背棄“成言”,“悔遁而有他”的時候,屈原才發現,“君可思而不可恃”,這時他感受到了個人在體制中的委屈與孤獨。甚至他認定一國之中沒有一個人能理解他,“舉世皆醉我獨醒,舉世皆濁我獨清”,他慨嘆“人之心不與吾心同”,至此,他就把自己放在整個世界的對立面去了,不僅是一個壅君,幾個奸臣小人,而是所有人。一個人站到所有人的對立面是什么結果?可悲的是,屈原在為大多數人謀福利,但大多數人并不能對他援之以手——姐姐罵他,不支持他,還要他屈服;太卜鄭詹尹很有分寸地緘口不言,漁父甚至對著他“莞爾而笑”,唱了一曲“清斯濯纓,濁斯濯足”來諷諭他,然后是“不復與言”。在別人的眼里,他太固執,太鉆牛角尖,不容易對話與溝通。屈原就只能死在孤獨之中,死在庸君的昏憒、奸人的險惡以及大眾的沉默中了。
貳
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
屈原的“求女”,就是“求知音”,而“無女”當然也就是無知音。屈原筆下的“求女”都是失敗的。屈原的知音在后代,而不在當代。他的最早的知音大約是賈誼,一個年輕有為而又多愁善感情緒不穩的書生,天才政治家,當然也同屈原一樣,是一個失敗者。當他被貶為長沙王太傅時,過湘水,投書以吊屈原。而此時,距屈原自沉汨羅,已是“百有余年”了。后來司馬遷把他兩人合傳,不同時代又無學術承傳而合傳,除《刺客列傳》《游俠列傳》外,僅此一例。顯然,這三種傳記,都取的是精神上的承傳、際遇上的相似。
屈原也缺少孔墨孟荀等人的達觀。他畢竟不是冷靜從容的哲人,他是詩人。同時,他也缺少他們曾經有過的苦難磨煉。當他20歲行冠禮作《橘頌》時,他是何等儒雅自信,前途遠大。而孔孟等人此時還在社會底層掙扎,受盡白眼與辛酸,因而他們有韌性。
而屈原,他純潔無瑕的貴族血統與心性使他無法面對失敗。在失敗面前他不能沉默,不能隱忍,不能迂回。他呼喊,他叫屈,他指責,他抗爭,于是他得到的是更大的打擊與蔑視,是別人對他的徹底的失望。
他撣去灰塵,保持自己的皓皓之白。他凜然地站在邪惡的對立面,與他們劍拔弩張。一點也不含蓄,一點也不躲閃,一點也不講策略。他給對方看他的傷口,以便對方知道他的仇恨與報復心切。他由此遭到邪惡的全面徹底的攻擊,邪惡無法容忍他的存在,因為他把自己擺在與邪惡你死我活的對立面上,邪惡即使僅僅為了自己的活,也要讓他死。而屈原的偉大與可貴也正在這里:他不理解邪惡與不公。他無法和他們和平共處,哪怕是虛與委蛇。他謹持著他理想的絕對純潔。他至死也不曾丟失一寸土地。他是代表獨特個體而與社會宣戰的最偉大最慘絕人寰的戰士。因為他的絕不讓步,這世界有可能免于全面墮落。
而他的這種行為必然會遭到一些孱頭式的批評。比如揚雄與班固。
揚雄看到了人性自身的弱點與功利趨避。他收斂自己的光芒與芬芳,降低自己的精神品位,從而與世俗取齊。他認為與其與對方弄得魚死網破,倒不如以自己的茍活換得對方的寬容,或者,以自己對對方的道德寬容忍讓換得自己的茍活。他大概是在為自己附莽作辯護吧?(揚雄《反離騷》)
而班固,本來就是一個見識不高的人。他臧否人物往往持論乖謬得令人莫明其妙。他認為對君上是不能批評的,對小人也是不應該斗爭的。而屈原則偏偏“責數懷王”,“競乎危國群小之間”,所以屈原簡直是咎由自取了!班固對屈原的批評,如同青銅對鐵的批評,不,是青銅做就的,貴族手中把玩的酒器溺器,對鋼鐵鑄成的叛逆英雄手中青鋒長劍的批評!
屈原堅定地忠于自己的內心感受。屈原愛君、戀君,這只是因為只有楚懷王才能實現他的理想;對那個頃襄王,他就毫無思慕之情,因為他對這個憨大孱頭不抱任何希望。他是一個個性極強,意志極強,脾氣也極壞的人,是一個極自尊的人。他的作品是“發憤以抒情”的產物,是無休無止的“怨”——“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劉安、司馬遷所標揭出來的,就是屈原的“怨君”及其合理性。而班固則只承認屈原“忠君”,而不滿于他的“怨君”了。班固的這一改造,便是幾千年的沉沉大霧:由“忠君”(班固)到“忠國”(王夫之)再到現代的“忠民”。但我這里要恢復屈原的本來面目:他忠于自己,忠于自己的感覺,忠于自己的良心!
叁
屈原的代表作《離騷》,若從其具體政治主張上講,實際上并不見得有多高明。《離騷》的訴說有三個對象:對君,對自己,對小人。簡單地說,對君是忠,屈原標志著對士之朝秦暮楚式自由的否定,對士之“棄天下如棄敝屣”的自由的否定,也標志著另一種觀念的建立:忠。忠而見疑,便是怨。由忠而見疑而產生的“怨”,是很近于“妾婦之道”的,是頗為自卑而沒出息的。而且《離騷》還把自己的被委屈、被疏遠、被流放歸罪于小人對自己光彩的遮蔽,對自己清白的污染。這小人插足在自己與君王之間,導致自己的被棄。不可否認的是,中國文化傳統中,失意官僚普遍存在的棄婦心態,就是從屈原開始的。
好在《離騷》中還有對自我的充分肯定與贊揚,這在很大程度上洗刷了“忠君”帶來的污垢,而保持住了自己的皓皓之白。這可能是因為先秦士人主體精神的強大基礎尚未坍塌,屈原尚有精神的支撐。令人稍感吃驚的是,正是在屈原這樣一位向君權輸誠的人那里,這種桀驁不馴的個性精神表現得尤其強烈和突出,除了孟子外,大約還沒有人能和屈原相比:他那么強調自己、堅持自己、贊美自己(有不少人就據此認為《離騷》非屈原所作。他們的根據是:一個人怎能這樣夸獎自己)。而且一再表明,為了堅持自己,他可以九死不悔,體解不懲。正是這種矛盾現象,使得屈原幾乎在所有時代都會得到一部分人的肯定,又得到另一部分人的否定。我想提醒的是,在我們大力宣揚屈原忠君愛國愛民的同時,一定不要忘了他張揚個性的一面。這后一點,也許是屈原最可貴的東西。誰能像他那樣讓自己的個性直面世界的輾壓而決不屈服?誰能像他那樣以自己個性的螳螂去擋世界的戰車?誰能像他那么悲慘,誰能像他那么壯烈?誰能像他那樣成為真正的戰士?
“屈平辭賦垂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他在后半生人生絕境中的數量不多的藝術創造,已勝過楚國王族——也是他的祖先——幾百年創下的世俗政權的勛業。他寄托在他詩歌創造中的志向與人格,“雖與日月爭光,可也”——這是劉安和司馬遷的共同評價。我們知道,司馬遷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是一言九鼎的。而屈原的藝術創新,“軒翥詩人之后,奮飛辭家之前”,超經越義,自鑄偉辭,“衣被詞人,非一代也”——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杰出的文論家劉勰對他的評價。一個史界的司馬遷,一個文論界的劉勰,兩個在各自領域中的頂尖人物,對他的精神與藝術、人格與風格,做這樣至高無上的推崇,屈原之影響人心、之折服人心,于斯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