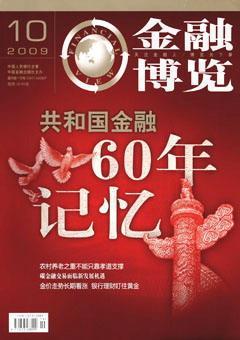孝道變遷的調查藍本
穆光宗
中國人孝的觀念,遠在西周時就有文字可考。而《詩經》中更是有“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的詩句。待到孔孟時代,中國孝道便上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但與之相對的是,時至今日,種種關于“棄老”的傳說仍舊在我國民間流傳,并且廣布全國各地,各少數民族——至少涉及15個省份,18個少數民族,其流傳地域囊括了中華文明的所有核心區和邊緣區。
如果說古時候養老道德還沒有普遍建立之時的棄老是因為貧而不養,缺乏食物,那么現在孝行減少則是富而不養,缺乏愛心。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孝道變遷在一定程度上佐證了子女對老人的愛心在減少。
老人評價子女不孝比例驚人
中國老齡科研中心在聯合國人口基金的資助下,于1992年初開始分別在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蘇,黑龍江,山西,陜西,四川,廣西,貴州,湖北1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進行了“中國老年人供養體系調查”,樣本量達20083人。在被調查的老年人中,城市高齡老人比中低齡老人對子女的孝敬程度評價低。明確回答子女不孝敬的比例城市為2.73%,農村為3.7%。回答“說不清”的比例無論城多,無論男女,均占11%左右。
2000年,中國老齡科技中心開展了“中國城鄉老年人口一次性抽樣調查”,結果發現:城鄉子女的孝行有所不同,城市子女對老人的孝行并不像農村子女那樣表現在經濟贍養上,而更多地表現為精神慰藉,體現了現今社會老人與子女之間的孝與養是可能分離的,孝并不一定需要通過養得到證明,子女的孝道需要從多方面進行評價。在這次調查中,北京市共獲得有效樣本1708份,84.7%的城市老人評價子女是孝順的,而農村的比例為80.1%。也就是說,老人評價子女不孝順的比例城市接近15%,農村接近20%。這實在驚人。
2004年,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科學系對北京,南京、上海、廣州、廈門、西安,香港進行了一次孝心調查,在上述7個城市抽取60歲以上老人,30~59歲中年人、15~29歲青年人三類樣本,進行有關孝道的研究。其中,“期望政府支援長者”認同度最高,達95%;其次是“對社會人士照顧父母的認同”和“對長者在居住環境上要溝通”,占87%;排名第三的是“照顧父母”。
農村孝道堪憂
2005年10~12月,黑龍江省人大代表翟玉和率調研組自費普查全國農村孝道現狀。調查組擬定了老有所養現狀調查問卷,涉及10大項55小項,通過對32個省市10401人的調查,統計結果顯示:孝18%,一般52%。不孝30%。被調查者人均收入650元,自養者78%,兒女供養者22%。調查組總結“吃得最差的是老人,穿得最破的是老人,住房最小的是老人。空巢老人大多沒精神,眼神茫然空洞,腦筋遲鈍,面無表情。家里清風冷灶,有電不使,有電視不開,不燒煤……”這些得不到物質贍養的老人,更難得到精神贍養。
最令人感嘆的調查是三位大學生在山東曲阜開展的“中華孝道調查”。2009年2月20日,在翟玉和的資助下,黑龍江雞西大學三位學生以“中華孝道調查”之名開始了山東曲阜之行。他們歷時兩個月深入43個村莊探訪2000多個家庭,調查1186位老人。受調查的老人中,與兒女分居者占72.2%、三餐不飽者占5.6%,衣著破舊者占85%、生活必需品不全者占90%,喪失勞動能力者占89%。另外接受調查的300多個子女中,56%的人認為孝與不孝與經濟有關,13%認為無關,31%認為父母無凍餒之虞就算孝。
孝行減少的主要原因
概括來看,“孝子女”減少的現象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是主觀上孝心減少,另一方面是客觀上孝行難舉。
首當其沖的是孝心的泯滅。翟玉和等人的調研報告指出,不孝歸罪于“文革”中的“親不親,階級分”及對孔子“愚孝”的批判。政治上,孝道這一德行被扼殺后,人性中被德行抑制的獸性抬頭。市場經濟又讓帶著政治烙印的一代轉向拜金——“世上只有錢最親”。由此,孝道在部分中青年人群中漸行漸遠直至消失。
二是我國急劇的社會變遷導致家庭結構核心化,家庭規模小型化,家庭贍養功能弱化。家庭戶平均規模的縮小和完全核心家庭(由父母與未婚子女組成)的增多導致純老年戶不斷增加。
三是代際居住分離,崇尚私密,追求獨立成為潮流。根據2007年全國老齡辦發布的《中國城鄉老年人口狀況追蹤調查》,2006年,我國城市地區的純老戶(空巢戶)為49.7%,與其他家庭成員一起居住的占50.3%,農村地區的純老戶(空巢戶)38.3%,與其他家庭成員一起居住的占61.7%。其中,城市中老年人表示愿意與子女住在一起的為37.1%,愿意入住養老機構的為16.1%;農村中的這兩項比例分別為54.5%和15.2%。
四是廣闊的人口流動拉大了人際間的地理距離和心理距離,導致贍養脫離,親情淡漠,心理趨于理性。
五是很多子女陷入了“角色困境”,一方面要做孝順子女,另一方面要做成功人士,在時間和精力上難以平衡和取舍,這在人口高齡化驅使下的長壽時代是格外嚴峻的挑戰。
(摘自2009年第9期《中國國家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