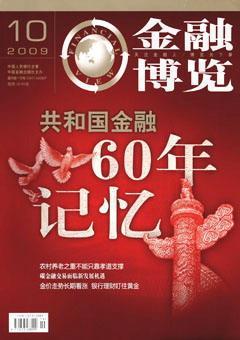“明清金融革命及其貨幣商人”之九:明清貨幣商人的經營策略
孔祥毅
明清貨幣商人經營的中國金融業,特別是清中期以后的票號,錢莊,賬局,已經實行企業化的經營管理,它們十分重視經營謀略,能夠正確把握貨幣市場的經營策略。它們從商品經營資本中分離出來,帶著豐富的普通商號經營管理的經驗,重視信息,審時度勢,靈活機動,慎待社會各方面的關系,營造和諧的經營環境,通過不斷的金融創新,探索貨幣經營業的經營管理藝術和策略,一步步走向成熟。
穩健謹慎,重視市場信息
審時度勢,伸縮機構。清代貨幣經營業規模較大的金融機構要數票號,票號實行總分支機構制,增設新的分支機構,必先進行調查研究,在掌握市場發展趨勢的基礎上,決定新號布局,拓寬經營地域。在經營過程中,如果發現某地環境變化不能盈利,就果斷撤莊。票號分支機構設遍全國通都大邑、商埠碼頭,拉薩,巴塘,理塘,打箭爐,雅安等藏區雖然地理偏僻,但因財政和商務有匯兌需求也設有分號。在太平軍進軍南京時,長江一線的分號受到侵擾,總號遂令該地分號急速收縮。日俄戰爭期間,東北營口等地業務困難,不得不停業,戰后則迅速調整力量,擴展業務,在四平,哈爾濱,齊齊啥爾,黑河,丹東等地設立分支機構,繼而設莊于朝鮮仁川,后又伸向日本神戶,橫濱,大阪,東京。可以說,票號分支機構的設置是隨盈利與風險大小而伸縮的。
重視信息,嚴格情報。商諺道,“買賣賠與賺,行情占一半。”重視信息,自古皆然。《太谷縣志》稱,太谷商人“至持籌幄算,善億屢中,講信耐勞,尤為谷人特色,自有明迄于清之中葉,商賈之跡幾遍行省”。據史料記載,“票莊做生意,必須視各莊之出產,四時之遭遇,……預測某處之豐歉,早定計劃以兌款,屆時銀根松緊,于中取利,得貼水,可卜優勝。”寧波錢莊商人也是如此,他們凡事均宜刻意研究,從不知而求知。本行既為商業銀行,所辦之事皆為商業之事,則一舉一動皆應與商業合拍,方不愧商業兩字。現將聘請于絲,布,紗,糖,棉花以及其他種商品富有經驗者為顧問,——研究其來源出處,工本若干,售價若干“舉凡漲落之比較,銷路之淡旺,時間之關系,市面之需要,無不加以徹底研究”。票號,錢莊都重視從各種渠道掌握各方面的信息,包括市場信息,地方政治軍事信息,工農業生產信息以及政界人事變動等等。票號規定,當天晚上必須用信函形式,及時匯報總號,以便總號審時度勢,深思遠謀,謹慎決策,絕不貪圖近期利益,甚少短期行為,它們能夠注意別人不經營的業務,開拓市場,出奇制勝。在其資產負債管理中,又能謹慎行事,既要發行錢帖,擴大資金來源,又要現金準備充足,防御憑帖擠兌,存戶提現,當票質典,甚至還要準備地方政府財政急需周濟時的立即墊付。這樣做,使客戶感到“相與”,信用卓著,樂與往來,不斷擴張業務。
預提倒款,資金抽疲轉快
預提護本,嚴防空底。金融業在經營中會因市場風險,信用風險等發生虧賠,損及資本。為防御風險,票號商人設計了一種預提“護本”的制度,即在利潤分紅時,從紅利中預提一定數額的可能發生倒賬的損失,建立風險基金,專款存儲,一旦發生損失,以此作為補償。這種“預提倒款”,亦謂之“撇除疲賬,嚴防空底”,防止虧煞老本。這種護本,因為是按照股份所有者的股份多少,用同一比例提取的,故也稱為“倍股”。另外,還有的企業將應收賬款、現存商品及其他資產,予以一定比例的折扣,記人資產賬,使企業實際資產超過賬面資產,謂之“厚成”。還有一些企業實行“公座厚利”,即在利潤分配之前,提取一部分利潤留在企業周轉使用,謂之“公座”,以便厚利。無論是倍股,厚成抑或公座厚利,其目的都在于保證資本的充足率,以擴大業務,防范風險,反對急功近利和短期行為。這是中國金融業歷史上最早的風險基金制度。
酌盈濟虛,抽疲轉快,票號在經營活動中,因為異地款項匯兌,往往出現此地現銀多,彼地現銀少的現象。為了平衡現銀擺布,保證票號各分支機構的清償力和安全支付,不致發生擠兌,他們創造了“逆匯”辦法調度現銀,減少現銀的運送,大大節省了費用開支。逆匯與甲地先收款,乙地后付款的順匯不同,它是主動在乙地尋找急需在甲地支用款項而無現款的客戶,允許其在甲地先付出,隨后某一時間在乙地后收進,這樣就使得乙地商人在沒有現款的情況下可以立即在甲地購貨,待商品運抵乙地銷售后再在乙地付款。這種財務創新,一是滿足了商人異地采購急需款項的需求,二是減少了票號資金閑置,增加了利息收入;三是減少了異地現銀運送,用現銀多的地方的錢,去接濟短絀的地方,謂之“酌盈濟虛,抽疲轉快”,如北京分莊資金盈,張家口分莊資金短,張家口可主動吸收向北京的匯款,在張家口收匯,北京付匯,此叫順匯;也可以由張家口分莊先貸款給當地的商人,允其去北京取款購貨,北京先付出,張家口后收進,叫逆匯。如此平衡兩地現銀盈絀,同時多賺了貸款利息和匯款的匯費收入。
金貿結合,兩業混合生長
金融貿易混合生長,明清錢莊,當鋪,賬局,票號等金融企業,大多是在商品經營資本發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些金融企業產生以后,它們中的很多投資人并沒有放棄原來經營的商號,貨棧、店鋪,擁有眾多商號,也設有多家金融企業。山西介休冀家有綢緞、茶葉,皮毛,布匹、雜貨等商號,也有賬局,錢莊、票號,當鋪等金融機構,僅在湖北襄樊一帶就有70余家商號、十幾家當鋪,其經營地域南起湖北,北到喇嘛廟和庫倫。這些金融業首先是支持東家的百貨業的資金需求,有的還將一部分資本投入紡織,面粉,火柴,釀造以及采礦、冶煉等輕重工業。從而形成了金融資本與工商業資本的相互結合,互促互動,使其兩類企業得以高效融資,混合生長,加速了資本周轉和增值。
著名的晉商企業大盛魁,是近代中國最大的“長壽”企業,從清康熙初年直到1928年,存續280余年,其組織機構精悍,靈活機動,指揮如意,辦事效率很高。大盛魁的下屬機構有兩類,一種是直屬機構,即在外蒙古的科布多和烏里雅蘇臺的兩個分號,由總號直屬機構直接發號施令,各營業單位(駱駝隊組成的貨房子)在總號的指揮下從事運銷貿易,大盛魁在整個蒙古地區東西六千多里,南北二千余里的區域內,基本上是依靠這個總號和兩個分莊組織貿易活動的,并且壟斷著蒙古地區的貿易。另一種是“小號”,是由總號投資獨立經營的單位,獨立核算。大盛魁的這些“小號”,有商品經營業和貨幣經營業兩類,前者如三玉川茶莊,長盛川茶莊,天順泰綢布莊、德盛魁羊馬店,東升店貨棧,以及藥材,糧店,飯館等商店;后者有大盛川票號,裕盛厚銀號,宏盛銀號,以及其他錢莊,當鋪等等。它的茶莊,既是商業,又是手工業,設莊于湖北、湖南產茶地區,
就地收購鮮茶,按照華北人喜歡花茶,蒙古和新疆人喜歡磚茶,俄羅斯和歐洲人喜歡紅茶的不同習慣和要求,加工成不同種類的茶品分別包裝,北運銷售。蒙古牧民只要看到印有川字的磚茶,便爭相購買。天順泰綢布莊經常派人往返于京,津,蘇,杭等地采辦紡織品,專營馬匹的小號南設漢口,專營羊的小號則設北京,如此寵大的南北物資交流,需要巨額的資金運轉,大盛魁只通過自己的銀號,票號,錢莊辦理借貸,存放,匯兌,融通資金,就可以從全國各地進貨,通過歸綏,庫倫,科布多,恰克圖,行銷于蒙古草原,新疆,西藏與俄羅斯;又從那里運回北方和歐洲特產,轉銷內地。大盛魁最有特點的是“大盛魁印票莊”,它們在蒙古地區銷售商品時,因為牧民缺少現銀,便將日用百貨賒銷于牧民,按照購買商品數額計息,償還時以牲畜皮張作價清償貨款和利息,有時還將收購的牛馬羊等牲畜暫不趕走,交給牧民代為喂養,等膘肥肉圓時再趕走。同樣,大盛魁貸款給蒙古王爺貴族,或者代辦王爺晉京值班全程后勤服務,事先印就借據,由王爺府蓋以印信,償還債務時由牧民公攤。其借據稱為印票,上印著“父債子還,夫債妻還,死亡絕后,由旗公還”等字樣,故無貸款不能歸還之事發生。
金融控股集團的雛形,清代中國已經出現了金融控股集團的雛形,這就是晉商的聯號制,即由財東投資辦若干個不同行業的各自獨立核算和經營的商號或票號,賬局,錢莊,銀號,在業務上相互聯系,相互支持,形成一個網絡體系,近似現代企業集團,其分支機構遍布全國各地以致國外。早在明代,山西商人就已經有不少家族形式的大型商業集團,到清代則進一步發展為由金融企業領頭并管理的企業集團。如祁縣的喬家,渠家,榆次的常家,聶家,太谷的曹家,平遙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臨汾的亢家等等。以太谷曹家為例,該家族的企業,在19世紀20~50年代,有13種行業,640多個商號,37000多名職工,資本1000多萬兩白銀。商號名稱大多冠以錦字,如錦霞明,錦豐慶,錦亨泰綢緞莊,錦泉涌,錦泉興茶莊,錦豐泰皮貨莊,錦生蔚貨行,錦豐慶當鋪,錦泉匯,錦泉和,錦豐煥,錦豐典,錦隆德錢莊,錦元懋賬莊,錦生潤票號等。在曹家這個錦囊集團之中,管理所有商號和金融機構這個網絡體系的總機關是“六德公”,設于清康熙中期,資本金300萬兩。“六德公”通過“用通五”,“礪金德”,“三晉川”三個賬局管理全部曹家商業“勵金德”賬局管理設在太原,潞安及江南各地的企業,“用通五”賬局管理設在東北的各號,“三晉川”賬局管理設在山東,西北,朝鮮,日本的各號。在保持各商號獨立核算基礎上,由上一級商號領導相互進行信息交換,聯合采辦商品,融通資金、調劑人才等,充分發揮了綜合優勢,形成了類似現代金融控股集團公司的組織框架。
慎重處世,營造經營環境
重視企業形象。金融業的經營活動,需要好的經營環境。環境雖然是客觀的,但是也需要自己不斷地去營造,以形象創立事業。比如寧波錢業商人,就十分重視面子,他們認為面子是形象是牌子,人沒有好的形象就沒有朋友,企業沒有好的形象就沒有后勁。企業的形象好壞,往往與職員的形象有關,山西票號,寧波錢莊都十分重視職員形象的教育與培訓。言行舉止和品行鍛造,首先從自身節儉做起,常人看似“土財主”、“守財奴”,但是這些經理人員,對自己刻薄,卻對他人寬宏,這是一個有眼光的大企業家必備的品格。山西票商,寧波錢商的精明,開明加上節儉,吝嗇是他們成功的重要條件。
慎待商界相與。票號商人主張和為貴,認為和氣才能生財。凡經常有業務往來的誠信客戶稱為相與。凡是相與,不講價格,友好相處,世代相傳:一旦發現不誠,永不往來。晉商重視慎待“相與”,所謂慎待,就是不隨便建立相與關系,一旦建立起來則要善始善終,同舟共濟。如山西喬氏的“復”字號,盡管資本雄厚,財大氣粗,但與其他商號交往時卻要經過詳細了解,確認該商號信義可靠時,才與之建立業務交往關系,否則均予以婉言謝絕。但是當看準對象,摸清市場的狀況,認為可以“相與”時,又舍得下本錢。對于已經建立起“相與”關系的商號,均給予多方支持,業務方便,即使對方中途發生變故,也不輕易催逼欠債,不訴諸官司,而是竭力維持和從中汲取教訓。榆次常氏天亨玉商號掌柜王盛林,在財東將要破產時,曾向其“相與”大盛魁借銀三四萬兩,讓財東把天亨玉的資本全部抽走,天亨玉在無資金的狀況下全靠借貸維持,僅將字號改名為天亨永,照常營業,未發生倒賬,這全憑著王盛林掌柜的人格信用。后來大盛魁發生危機時,王盛林認為該號受過大盛魁“相與”的幫助,不能過河拆橋,不顧一些人的反對,仍然沒法從經濟上,業務上支持大盛魁,幫助大盛魁渡過了難關。
依托行會維護金融秩序。金融業的經營活動需要穩定的市場秩序,在沒有規范的金融法規的明清時期,全靠金融業行會來維持。金融業行會的制度是貨幣商人自發地聯合議定的規矩,大家必須自覺遵守,久而久之,就成為金融業的“習慣法”,其本質是維護金融業的信用,使得各種金融交易得以持續不斷地進行。這種金融業習慣法,一是授人以積極的預期,得以繼續融資;二是使金融交易有章可循,降低交易成本。所以無論票號,錢莊,賬局,無論在北方抑或南方,各地貨幣商人都很尊重行會的組織管理,否則就會被逐出市場。
慎處與政府的關系。處理好與政府的關系是金融業經營中不可回避的環境問題,是歷代銀錢業都很謹慎對待的事情。票號與政府關系比較密切,這是咸豐朝開始的事。咸豐皇帝登基之時正遇太平天國起事,太平天國占據南京,活躍于長江一線,切斷了清政府南方稅款上解通道,財政收入銳減,同時又要派兵鎮壓,財政支出驟增,用了很多辦法都不能平衡財政收支,遂想出賣官鬻爵一法。票號發現各地特別是邊遠省區的入京應試費用浩繁,捐官者需直交現銀于戶部,路途遙遠,費用高昂,便創新了代辦捐納印結之業務。凡新官上任,代辦支墊應酬,而在其赴任后隨行開辦票號分號,拓展業務,再請求公款存入票號,一步步與官僚,官府建立起不解之緣,以致有后來的官商相維,官商結合。繼而票號商人也捐納報效,取得虛職虛銜,必要時可以官服加身,與政府官員稱兄道弟,平起平坐,追收逾期貸款或者延攬公款存入,就成輕而易舉之事。在遇到重大社會問題時,請求政府出面,維護市場穩定,比如貨幣流通問題,社會治安問題等等。請求政府出面通過指令,文告,穩定金融市場秩序,諸如貨幣流通借貸利率等等,歷代政府多有介入為貨幣商人提供了必要的經營環境。
競爭合作,吸收外來經驗
靈活的錢莊老板。鴉片戰爭以后,西方列強用大炮和鴉片打開了中國關閉的國門,外資銀行,保險進入中國,
但他們在中國的經濟活動很難直接進行,必須委托中國人來承辦。外資銀行雇傭中國雇員,為銀行在班(經理)了解經濟和市場情況,招攬各項業務,經手銀錢往來,這些雇員被稱為買辦,買辦處理業務的地方叫做買辦間。外資銀行和買辦訂有契約,規定買辦業務范圍,責任以及擔保事項。
外資銀行與錢莊之間常有收付莊票,鑒定金銀,買賣匯票,款項拆借等交往,均通過買辦之手,故買辦必須了解錢莊。這些買辦不是出身于錢莊,就是與錢莊有密切聯系,熟悉錢莊的情況,一切由買辦搭橋掛鉤。有些人當了買辦后又與人合開錢莊,一身二任,既是買辦又是錢莊老板,外資銀行,洋行與錢莊就這樣聯結起來了。錢莊商人又常常托庇租界,進行金融市場投機。19世紀60~80年代金融投機盛行,上海縣、蘇松太道乃至江蘇巡撫曾不止一次發出布告,要查辦投機活動,而租界內錢莊竟敢不予理睬。1871年上海縣知事出了告示,規定了錢莊連環互保,錢莊倒閉由投資人完全負責等等。各國領事竟“拒絕在租界中公布這個告示”。錢莊走了買辦化的道路。
也難怪。錢莊業由于資力比較弱,為了自存并擴展業務,除了向票號融資外,不得不與洋行或外資銀行建立業務聯系。錢莊向外資銀行融通資金的工具是莊票。當中國商人向洋行進貨時,若資金有限,洋行又不了解中國商人資信而不予賒銷,商人仍請求錢莊提供信用,錢莊便開出自己的莊票,洋行對錢莊莊票較為信任,到期即可在錢莊取得現金。于是洋行擴大了銷路,中國商人獲得了購進洋貨運銷內地所需資金,錢莊擴大了放款,增加了利潤。后來,經買辦介紹,外資銀行對錢莊以莊票為保證品提供貸款。此種業務不斷擴大,遂使錢莊進一步依賴于外資銀行,只要外資銀行稍微收緊貸款,錢莊就感到周轉不靈。由于錢莊和外資銀行拆款關系的建立,外資銀行和錢莊之間通過相互軋抵,減少了現金的搬運,建立起了新的清算網,這對中國的對外貿易也是不可少的。
錢莊、票號,洋行與中國市場化。據海關《關冊》統計,從1864~1894年的30年中,中國進出口貿易的總值由9400余萬海關兩,逐步增加到29000余萬海關兩,而同期在中國通商口岸的所有洋行最多時不到600家,各國商人不到萬人。對外開放與貿易直接關系著中國內地的市場化進程,這與錢莊、票號等金融機構是分不開的。比如,洋貨進入西南地區,西南地區土產出口,多借助于四川商人之手。四川商人又得助于漢口和上海的錢莊提供信用。中國土產如生絲,茶葉由鄉村進入通商口岸,也經過了錢莊和票號融資。在北方,洋貨從天津來,土產從華北,西北來,以張家口,,歸綏等地為集散地,通過天津的錢莊、票號為之融資與匯兌結清款項。就這樣,錢莊,票號等金融機構就成為這種交易的聯結器。
清末,近代銀行、保險公司,投資公司等已經產生,雖然在工商業中的地位還不高,但它們普遍采用了股份有限公司的組織形式,資本較多,存貸額比較大,發展勢頭很好。錢莊與新式商業“同舟共濟”,而且錢莊主和新式商人的身份常常是“二合一”。19世紀60年代以后,上海商人仿照山西幫票號的辦法,設立南幫票號,如胡光墉的阜康、嚴義彬的源豐潤,李經楚的義善源等,它們除匯兌外,其存放業務與錢莊相似。由于錢莊在進出口貿易中的地位如此重要,早期的洋行就支持買辦開設錢莊,或與買辦合伙開設錢莊。雖然外資銀行控制著中國的金融市場,但不可能控制錢莊的內部業務,錢莊的性質仍然是民族資本金融業,它們與晚清時期國人設立的30家銀行,14家保險公司,1家投資公司一起,服務于中國工商業發展和經濟市場化運行。
中國的錢莊、當鋪,印局、賬局和票號,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商業銀行,它們由小到大,由弱到強,不斷壯大,固然有各大商幫的支持,但是不能不說是伴隨著工商業發展需要而不斷進行的金融創新的成就。在對外金融活動創新方面,進口貨幣金屬,與外商融資貿易,將票號錢莊設往國外;在金融制度創新方面,有金融企業股份制、兩權分離制,聯號制,人力資本制,薪酬激勵制;在金融工具創新方面,有憑貼,兌貼,上貼,上票,壺瓶貼,期貼,會券;在金融業務創新方面,有本平制度、票據轉讓貼現、順匯與逆匯,代辦代理,掉期業務,轉賬結算、同業拆借、信約公履:在風險控制方面,有“護本”制,宗法與擔保約束,銀行密押,金融稽核,內控制度,等等。金融創新是明清金融業發展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