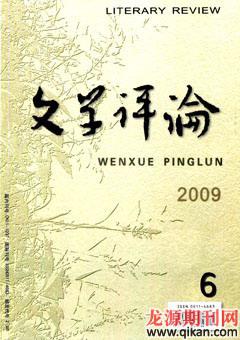“變臉”后的難題與可能
杜國景
內(nèi)容提要:80年代“變臉”后的文學批評,對新中國前三十年文學的正面價值似有難言之隱,多以“反讀”代替正讀、“發(fā)現(xiàn)”代替判斷、闡釋代替評價。個中原由,除歷史本身的某些負面效應(yīng),批評方法的缺失也值得反思。借助韋勒克文學理論的反歷史主義立場及其“透視主義”觀點,批評似可得到拓展。在“透視主義”的視野下,文本內(nèi)部呈現(xiàn)方式出現(xiàn)了新的可能性,并可帶來外部意義關(guān)聯(lián)的另一種可理解性。
一、問題的提出
三十年前,基于認識論和反映論立場的批評話語霸權(quán)開始遭到質(zhì)疑,西方的各種文學理論和流派大量涌入,我們迎來了一個“批評的時代”。由于以此為界,新中國文學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歷史幾乎是顛覆性的,因此“變臉”后的文學批評,對前三十年文學的正面價值似有難言之隱。其中尤以文學的真實性問題為最。重評,再解讀、重寫文學史等等,大都涉及這一領(lǐng)域,但多為詬病和詰難。直至以“反讀”代替了正讀,以“發(fā)現(xiàn)”代替了判斷,以闡釋代替了評價。“變臉”的批評始終在尋找如何從前三十年文學的真實性問題中突圍的路徑和方法。世事盛衰,真應(yīng)了“三十年河?xùn)|,三十年河西”那句老話。直到21世紀初,關(guān)于文學作品的評價,還有一種“寫得怎樣”的批評方法被提了出來,旨在以“文學性”來模糊“寫什么”、“怎么寫”與“真實性”的邊界。研究者以反映法國大革命、三國紛爭、北宋農(nóng)民起義、特洛亞戰(zhàn)爭等歷史的小說為例,認為“面對一部文學作品,人們有理由從作者‘寫什么去追究去闡發(fā)他所寫的‘什么。而這追究這闡發(fā)與對作品的文學評價無關(guān)”。研究者舉例說,《三國演義》持鮮明的擁劉反曹立場,人們當然可以研究三國時期的歷史,比較曹魏和蜀漢哪個政治集團的政策更有利于社會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考察作者將劉備與曹操定位于“仁”與“暴”,“忠”與“奸”的描述哪一個更符合歷史真實,但“這樣的考察與探討,與小說《三國演義》的文學成就無關(guān)”。研究者還說,關(guān)于《水滸》的主題意向,向來見仁見智,但“都不會影響這部小說的文學地位”。同樣描寫特洛亞戰(zhàn)爭,歐里庇得斯的《特洛亞婦女》表現(xiàn)了與荷馬史詩《伊里亞特》不同的政治態(tài)度,但“對作者政治立場的追究不至于影響對作品的文學評價”。
果真如此么?不!我認為這里的論證是值得商榷的。且不說“寫得怎樣”如何同樣關(guān)乎真實性。僅以研究者所舉的幾個例子而言,就禁不起“審美距離”的推敲。擁劉反曹,水泊梁山,或特洛亞戰(zhàn)爭,離今天都已經(jīng)很遙遠,有如繪畫中的或籠中的老虎,對觀賞者不會再產(chǎn)生直接威脅,因而可以很超脫很悠閑地去談?wù)撍u價它,自然,這談?wù)摵驮u價也就無關(guān)我們切身的現(xiàn)實利益,無關(guān)“作品”的成敗得失。改革開放前的三十年不一樣,那還是昨天的歷史,與我們今天的現(xiàn)實處境有著太多的利益關(guān)聯(lián)。今天的每一點進步,都離不開昨天的積累或者經(jīng)驗教訓(xùn)。所謂創(chuàng)新,也是舊中之新,不可是推倒重來。在今天的現(xiàn)實語境下談昨天的文學創(chuàng)作,只關(guān)心“寫得怎樣”,完全不顧及昨天的功過是非,這無論如何說不過去。事實上,研究者以《創(chuàng)業(yè)史》為例所展開的論述,也并沒有脫離對柳青。怎么寫”的姿態(tài)的評價。既然如此,“寫得怎樣”又怎么能夠和“寫什么”、“怎么寫”割裂呢?
研究者的良苦用心,也許是要別開蹊徑,重新尋找“對話”改革開放前三十年文學創(chuàng)作實踐的可能性,重新驗證闡釋學、結(jié)構(gòu)主義等新的文學理論的覆蓋半徑與時效性。從而打開一條評價文學作品的新通道。這種探索精神當然是可理解的也是值得敬佩的。但新中國前三十年文學的價值,尤其是社會主義改造題材文學的真實性(研究者主要也是以此為例來展開分析的),并非已不能正面接近,撇開“寫什么”與“怎么寫”的立足點,似有回避問題之嫌。主體、文本、昨天的歷史語境,今天的變革,再加上新的批評視點,仍應(yīng)該是所有可能性的前提。
二“透視主義”是否可能
用“變臉”后的批評標準去看,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的文學實踐,尤其是現(xiàn)實題材的文學,最令人難堪的,與其說是“歷史元敘述”的虛幻,不如說是那種功利主義訴求中的真誠、激進和自信。所謂的“難言之隱”也主要是就此而言的。在它的“文學性”面前,哪怕最激烈的否定也不得不有所保留。林斤瀾曾是新中國初期的一位熱情歌者。晚年重翻舊作,他說:“五六十年代的習作,打著明顯的年代烙印。但也真誠,沒有別樣肺腑……三十年后為選選集通讀一遍,青年時候的熱情,還叫老來遲鈍的心胸,一緊一緊的。”類似的話,王蒙、茹志娟等都說過。蓋因如此,“變臉”的批評在論及這三十年的文學時,總體便是從所謂“內(nèi)在的深刻矛盾性”著眼來建構(gòu)意義。目的“是要揭示出歷史文本背后的運作機制和意義結(jié)構(gòu)”,“解讀的過程便是暴露出現(xiàn)存文本中被遺忘、被壓抑或粉飾的異質(zhì)、混亂、憧憬或暴力”。比如在肯定“文學性”的同時;先從“細節(jié)真實”潛入;再重新界定“歷史本質(zhì)”、“歷史發(fā)展必然規(guī)律”,最后論及真實的距離與評價的尺度;或以“民間形態(tài)”、文本的深層結(jié)構(gòu)立論等等,都屬此類角度。但是,隨著批評觀念、批評方法、批評角度的切換,評價標準的游移,是否會帶來文學史與文學理論、文學批評的分離呢?如韋勒克所指出的:“認為文學史旨在展示甲源于乙,而文學批評則在宣示甲優(yōu)于乙。根據(jù)這一觀點,文學史處理的是可以考證的事實,而文學批評處理的則是觀點與信仰等問題。可是這個區(qū)別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在韋勒克看來,這是文學的重建論主張,是一種“歷史主義”方法。“這個方法給人一種印象:文學批評只有一個標準,即只要能取得當時的成功就可以了。”
在批評話語“變臉”后的相當長時期里,前三十年文學的意義和價值正是這樣,被嚴格限制在產(chǎn)生它的那個時代。前三十年與后三十年的審美規(guī)范仍相對割裂。依照這樣的方法,便只能以當時的成敗來論英雄。即認為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文學觀念與批評規(guī)范,評價作品不能脫離這特定的文學觀念與批評規(guī)范。倘若脫離,文學批評要做的事情只能是推倒重來,這其實就是“重評”、“再解讀”、“反評”產(chǎn)生的深刻根源。而在韋勒克和沃倫看來,這樣做會陷入相對主義泥潭,如果“每一個時代都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單元”,不同時代的文學觀念與批評規(guī)范將無法打通,“詩的理想于是人言言殊,破碎而不復(fù)存在:其結(jié)果是一片混亂,或者無寧說是各種價值都拉平或取消了”。具體來說,新中國短短幾十年的文學歷史將會變成各自獨立的斷簡殘篇,各歷史時期文學的意義結(jié)構(gòu),將只能是封閉的而不是開放的系統(tǒng),這顯然是個矛盾,不能解釋文本意義結(jié)構(gòu)至今所呈現(xiàn)的多樣性、豐富性或“內(nèi)在的深刻矛盾性”。
事實上,前三十年的文學是蘊含著各種價值的一個復(fù)雜而又龐大的體系,不能僅僅以作者或同時代人的觀點去評價,也不能以一種抽象的、絕對的標準去衡量。對新中國前三十年文學經(jīng)典的理解與闡釋,既要回到歷史,但又不能離開當前的現(xiàn)實。在歷史與現(xiàn)實之間,現(xiàn)實占有更大的權(quán)重。只有從現(xiàn)實出發(fā),并最終回到現(xiàn)實,才能
令人信服地重新面對當年的文學創(chuàng)作。對此,韋勒克和沃倫給出的方法是:“必須接受一種可以稱為‘透視主義(perspectivism)的觀點。”如同透視法的采用在繪畫中會導(dǎo)致人的視覺改變一樣,透視主義的意思,不僅僅是如何從單一角度去發(fā)現(xiàn)和揭示文本深處的含義,而是要把文學作品看作一個整體。這個整體在不同時代都在發(fā)展著,變化著,可以互相比較,而且充滿著各種可能性,尤其不可忽略現(xiàn)實話語與歷史話語間的意義關(guān)聯(lián)。顯然,韋勒克對文學的普適性價值是充滿信心的,認為“藝術(shù)作品是一個由各種價值構(gòu)成的整體”,甚至斷言“價值恰好就是文學的本質(zhì)”。所以他抵制歷史主義,以為文學批評考察的是不朽的作品。這與伊格爾頓徹底的歷史主義立場正好相反。作為西方現(xiàn)代繪畫的理論方法,透視學有現(xiàn)代科學研究做強大后盾,是理性解釋世界的產(chǎn)物。它所依從的“焦點透視”原理,為逼真再現(xiàn)事物的真實關(guān)系提供了各種可能性。同時,也對我們了解文學何以能在“特定意識形態(tài)指定的位置”,“并且作為某種文化成分介入歷史語境”的前提下,仍能顯出各式各樣姿態(tài),做了富有啟示的示范。對此,新生代作家畢飛宇有著自己的理解。他引用美國文學理論家韋恩·布斯的《小說修辭學》中提到一個“木箱原理”:一個木箱放在客廳里,可以說它僅僅是一個木箱。但如果這個木箱放在閣樓上,一半露在外面,就會讓人產(chǎn)生恐懼心理,甚至擔心掉下來砸到自己。木箱還是那個木箱,僅僅放的位置不同,就會讓人產(chǎn)生完全不同的感受。這其中到底哪一個是現(xiàn)實昵?顯然,都是現(xiàn)實。“純粹的現(xiàn)實主義不存在”。這就是畢飛宇的結(jié)論。現(xiàn)實存在于重要的關(guān)系之中,而各種事物的關(guān)系就源于我們對世界做出的判斷。生活中并不存在純抽象意義、沒有加工和描述的事物。既有加工和描述,那就一定會受到作家或批評家自身所處位置和角度的限定。
這讓我們想起了《創(chuàng)業(yè)史》中的一個藝術(shù)形象:郭振山。用今天的觀點去看,這個形象就是中國農(nóng)民中的一個智慧型人物。他非常懂得尋找政治權(quán)力與經(jīng)濟利益之間的平衡,而做到這一點,他就牢牢抓住了鄉(xiāng)村日常生活中權(quán)力運作的核心,就能成功地把政治權(quán)力轉(zhuǎn)化為個人權(quán)威。福柯說過,權(quán)力不是壓制性的外在控制,“權(quán)力只有將自己主要的部分偽裝起來,才能夠讓人容忍它”。上世紀50年代的農(nóng)業(yè)合作化運動雖然是國家政治權(quán)力向鄉(xiāng)村強行滲透的過程,但它已不再象土改那樣采取劍拔弩張的方式。在鄉(xiāng)村,除了政治權(quán)力之外,宗族、社區(qū)、親屬、婚姻、風俗、禮儀等日常生活,無一不體現(xiàn)著權(quán)力關(guān)系。政治權(quán)力向著日常生活權(quán)力轉(zhuǎn)換就是一種偽裝,一旦轉(zhuǎn)換變成現(xiàn)實,權(quán)力就會變成權(quán)威,服從就會變成義務(wù)。郭振山深諳此道,每一次遭遇個人危機,他都懂得用這一套理由來說服自己,減緩個人發(fā)家的步伐。這種審時度勢的才干和智慧,存在著比較的可能性。假如生逢其時,他究竟會成為吳仁寶還是會成為禹作敏,那不好說。但他在政治權(quán)力與鄉(xiāng)村日常生活權(quán)力之間,在經(jīng)濟利益、社會權(quán)威,以及道德、道義、倫理等等關(guān)系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博奕才能,的確是一種深邃的智慧,令粱生寶望塵莫及。由于進入了特定意識形態(tài)的指定位置,并且作為某種文化成分介入了歷史語境的建構(gòu)。現(xiàn)在的郭振山以獨特的姿態(tài)發(fā)出了獨特的聲音。而文本內(nèi)部的呈現(xiàn)方式所出現(xiàn)的新的可能性,又帶來了外部意義關(guān)聯(lián)的另一種可理解性。特別要說明的是,這種可能性或者可理解性,不同于價值顛覆或文本反讀,而是帶有理解和寬容成分在內(nèi)的判斷和評價。或者說這種可能性和可理解性,正是合作化小說藝術(shù)形象內(nèi)在人格化的魅力!這就是“使價值尺度具有動態(tài)”,“表明從各種不同的、可以被界定和批評的觀點認識客體的過程”。
由此推衍,新中國前三十年文學的各種價值,完全可以產(chǎn)生于不同時期批評的累積過程,并反過來幫助我們認識、理解這一過程。因此,研究這三十年的創(chuàng)作,就必須指出它們在自己那個時代和以后時代的價值,在于保有某種永久的品質(zhì)而又不呈封閉狀態(tài)。它是歷史的,也是現(xiàn)實的,因為它經(jīng)過了較長的有跡可尋的發(fā)展過程。與對這類創(chuàng)作的解構(gòu)性批評一樣,對它們的后價值批評,或者不切實際的意識形態(tài)還原論批評——即把前三十年文學看作那個時代政治危機的道德等同物,其實都靠不住。既然它們是各種價值的體現(xiàn),那現(xiàn)在最重要的事情就莫過于揭示其中各種價值之間的意義關(guān)聯(lián),只有這樣,才可能解決我們究竟要在前三十年文學中去關(guān)注什么和發(fā)現(xiàn)什么,以及為什么要去關(guān)注和發(fā)現(xiàn)的問題,才能既回望歷史,又回到現(xiàn)實本身。現(xiàn)在以至將來,當我們要尋找能夠代表那個時代民族國家形象的文學時,除了那些公認的經(jīng)典,恐怕別無選擇。你可以否定它,忽略它,不欣賞它,甚至可以用鄙夷和厭惡的態(tài)度抨擊它,但你無法忽視它、逾越它。只要逼近現(xiàn)實,追溯歷史,你就必須與其情感、思想和藝術(shù)對話。
2006年7月5日,《光明日報》頭版發(fā)表雷達的長篇論文《當前文學創(chuàng)作癥候分析》。文章指出,中國小說精神缺鈣的現(xiàn)象在日益普遍化和嚴重化。部分人群的精神生態(tài)趨于物質(zhì)化和實利化,腐敗現(xiàn)象蔓延,道德失范,銅臭泛濫,以致一些人精神滑坡。從文學審美的角度來看,由于自現(xiàn)當代以來,人們受到過太多的偽崇高、偽宏大、偽權(quán)威、偽浪漫、偽美的欺騙和傷害,對于號稱神圣的東西心存疑義,于是90年代以來的小說便以較大規(guī)模和較快速度告別了神圣、莊嚴、豪邁而走向了日常的自然經(jīng)驗陳述和個人化敘述。在“癥候”分析的基礎(chǔ)上,雷達特別強調(diào)了作家與時代的關(guān)系,呼吁強化肯定和弘揚正面價值的能力。雷達所說的正面價值,指的是民族精神的高揚,偉大人性的禮贊,是對人類某些普世價值的肯定,例如人格、尊嚴、正義、勤勞堅韌、創(chuàng)造、樂觀、寬容等等。雷達認為有了這些,對文學而言,才有了魄魂。它不僅表現(xiàn)為對國民性的批判,而且表現(xiàn)為對國民性的重構(gòu),不僅表現(xiàn)為對民族靈魂的發(fā)現(xiàn)而且表現(xiàn)為對民族靈魂重鑄的理想。雷達的宏論是針對“當前文學創(chuàng)作癥候”而發(fā)的,但這些“癥候”跟我們的文學批評難道就沒有關(guān)系么?新中國文學前、后三十年的正面價值是否有關(guān)聯(lián)、或究竟有什么關(guān)聯(lián),不是也值得思考么?“當前文學批評”在倒臟水的時候,是否也會把孩子給倒掉了呢?
三、歷史意識與歷史的悲劇品格
無庸諱言,新中國前三十年的歷史有著諸多負面效應(yīng)。這主要是經(jīng)濟建設(shè)急于求成,所有制結(jié)構(gòu)急于求純,以及階級斗爭的絕對化和擴大化,于是,才“形成了這一段曲折而又不失悲壯的歷史”。對這一段歷史,象過去那樣美化它,可能走向歷史偶像主義,即崇拜歷史起點,崇拜歷史過程,進而走向歷史泡沫。否定它,則可能走向歷史虛無主義,即看不起自己,全盤照搬西方。大眾傳播時代。如果對這一段歷史做戲擬化處理,象“大話西游”、“戲說乾隆、康熙”、“水煮三國”那樣,效法的又將是歷史虛構(gòu)主義——這在前幾年楊子榮、郭建光身上,已經(jīng)出現(xiàn)過了。而無論美化、否定、還是戲擬,都將是歷史主義的思維方法,都是不可取的。其中,歷史偶像主義教訓(xùn)深刻,是
不可修復(fù)的歷史記憶。歷史虛構(gòu)主義至少在現(xiàn)階段還缺少必要的土壤和條件,偶有露頭,市場也不大。危害最大因而特別值得警惕的,倒是歷史虛無主義。因為歷史虛無主義往往以“正劇”的方式解構(gòu)歷史意識,被它加以虛無化的,可能正包括著歷史的本質(zhì)。
那么,什么是歷史本質(zhì)?應(yīng)該用怎樣的歷史意識去把握它呢?我以為,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崛起,中國人民改變自身命運的艱苦卓絕的努力等等,當然是歷史本質(zhì)的主要內(nèi)容。除此之外,把握歷史本質(zhì),更要立足于當前的現(xiàn)實。如俞吾金所言:歷史的本質(zhì)與當代生活的本質(zhì)密切相關(guān)。“在研究歷史之前,先要研究領(lǐng)悟當代生活的本質(zhì)”。在這個意義上,任何歷史都是當代史。當前“市場經(jīng)濟和現(xiàn)代化所蘊含的客觀的價值導(dǎo)向——市民社會、民族政治、獨立人格、個性自由、基本人權(quán)、社會公正等等,正是歷史意識首先要加以把握的思想內(nèi)容。”所以,“確定某個歷史事件、歷史問題和歷史經(jīng)驗是否有意義的鑰匙隱藏在當代的思想意識和客觀的價值觀念中”。
誠哉斯言!但如果進一步追問,“當代的思想意識和客觀的價值觀念”卻并不是一個不辯自明的問題,在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歷史學教授、國際知名的中國問題研究專家莫里斯·邁斯納眼里,當今世界是個缺少幻想的時代。所以他說,“我們的時代,是共產(chǎn)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同樣經(jīng)歷著可憐的目標貧乏和令人震憾的缺少幻想的時代”。我們現(xiàn)在唯一能想象的,似乎只有市場。然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卻給我們上了關(guān)于市場的生動一課。當我們想象人類未來的能力遠遠不及毛澤東領(lǐng)導(dǎo)的革命所預(yù)期達到的目標時,我們又有什么資格侈談歷史本質(zhì)或歷史意識呢?“人民擁有想像一個美好未來的能力,這對于作出有意義的努力去改變今日之現(xiàn)狀卻是至關(guān)重要的。因為人們必須先有希望然后才有行動,如果人們的行動要想不是盲目的,不失其目的,那么其希望就必然寓于對更美好的未來的幻想中。”莫里斯·邁斯納這段話,無論對歷史還是對現(xiàn)實,都有警醒意義。也許正是因為如此,新中國前三十年的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shè),才得到了海外學者,包括一些持西方立場的知識分子的理解。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與日本學者池田大作,甚至還在毛澤東時代,就預(yù)言了中國在人類歷史上所將擔當?shù)呢熑巍3靥镎J為在亞洲的文明古國中,“只有中國在迅速接近歐美發(fā)達國家的水平。”中國“政治上獲得了穩(wěn)定。再加上通過社會主義體制實行計劃經(jīng)濟,努力促進社會資本的積累。中國似乎完全敷設(shè)好了自己重建的軌道”。湯因比則分析,在過去的五百年里,西歐各民族“在技術(shù)和經(jīng)濟方面把人類統(tǒng)一為一個整體”,那么以后呢?“中國今后在地球人類社會中將要起什么作用昵?”他的回答是,就中國人來說,“幾千年來,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幾億民眾,從政治文化上團結(jié)起來。他們顯示出這種在政治、文化上統(tǒng)一的本領(lǐng),具有無與倫比的成功經(jīng)驗。這樣的統(tǒng)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絕對要求。中國人和東亞各民族合作,在被人們認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類統(tǒng)一過程中,可能要發(fā)揮主導(dǎo)作用”。既然這么多西方學者,都對新中國前三十年的社會變革,給予如此多的期許,為什么我們自己卻底氣不足,要將“寫得怎樣”與“寫什么”、“怎么寫”人為地切割開來呢?
有理由相信,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shè)包含“現(xiàn)代性”吁求在內(nèi)。就象在“市場”這個隱喻中來理解現(xiàn)代性一樣,我們同樣可以從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shè)中來理解現(xiàn)代性。那么,什么是“現(xiàn)代性”呢?如果用最簡單的詞來解釋,“所謂現(xiàn)代性也就是‘可能性(possibility)”,“在這個意義上,市場其實也就是‘可能性、或者僅僅是‘對可能性的承諾。在市場中,任何人的命運都是相對的——即他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和沉淪”。不錯,新中國的前三十年是走過了曲折的道路,但至少不能說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shè)已經(jīng)走向了“失敗和沉淪”。以和平的、漸進的方式,實行社會主義工業(yè)化和社會主義改造同時并舉的方針,為國家的現(xiàn)代化建設(shè)打下了扎實的基礎(chǔ),這就是前三十年彌足珍貴的“中國經(jīng)驗”,也是我們今天的“歷史意識”的核心內(nèi)容。無論批評如何“變臉”,我們都應(yīng)有足夠的理由來直面這段歷史。
由于“寫得怎樣”是以“重讀”反映農(nóng)業(yè)合作化運動的著名長篇小說《創(chuàng)業(yè)史》并以其為例來展開論述的,而且合作化也確有從興到衰的重大失誤,有必要就此做一點展開。我認為,農(nóng)業(yè)合作化小說今天的審美特性,應(yīng)該是它的悲劇品格。這場運動是失敗了(不是前文所說的“失敗和沉淪”,而是哲學意義的“否定之否定”)。但它隱含著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的深度模式。通過對小農(nóng)經(jīng)濟的改造,引導(dǎo)農(nóng)民從個體經(jīng)濟走向合作化、集體化道路,這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個經(jīng)典表述,也是中國共產(chǎn)黨在奪得政權(quán)以前就早已確定不移的方針。可是,它也只是一種可能性。在1949年中國革命取得勝利、中國社會發(fā)生翻天覆地變化的歷史時刻,這個可能性的歷史必然性和歷史合理性幾乎就是不容置疑的,它必然帶來新的興奮點,造成一場文學題材、文學主題的“革命”。如馬爾庫塞所說,“讓藝術(shù)作品借助審美的形式變換,以個體的命運為例示,表現(xiàn)出一種普遍的不自由和反抗的力量,去掙脫神化了的(或僵化了的)社會現(xiàn)實,去打開變革(解放)的廣闊視野,那么,這樣的藝術(shù)作品也可被認為具有革命性”。然而,合作化既然只是一種可能性,在指向中國革命的這個深度模式時,文學創(chuàng)作就必然會追求烏托邦精神與鄉(xiāng)村日常生活經(jīng)驗的某種價值同構(gòu)。于是,合作化小說的悲劇品格便在這種“革命性”的敘事中被預(yù)設(shè)了。它之所以是悲劇性的,是因為“人們必須一再為不可能的東西而奮斗,否則他們就不可能達到可能的東西”,“如果放棄了烏托邦,人類就會失去塑造歷史的愿望”。就如同維克多·雨果所宣稱的:烏托邦也許并不是“明天的真理”,但是人民擁有想象一個美好未來的能力,這對于作出有意義的努力去改變今日之現(xiàn)狀卻是至關(guān)重要的。因為人們必須先有希望然后才去行動,如果人們的行動要想不是盲目的,不失其目的,那么其希望就必然寓于對更美好的未來的幻想中。而既然是幻想,它就只能是一種可能性,任何失敗和挫折都是情理中的事情——從這個意義說,任何歷史沖動都具有悲劇的品格。在這一過程中,文學的目的在于:幻想、憧憬,甚至信仰可以失去,追求的精神卻是任何時候都不能放棄的。
明顯的是,合作化小說在重建一種倫理想象時,總在烏托邦精神與鄉(xiāng)土倫理之間左右搖擺和游移。互助組也好,初級社也好,要讓農(nóng)民自愿參加,最有效的辦法莫過于共同富裕,讓農(nóng)民擁有財富,過上好日子。然而,合作化小說又總是用“財富恐懼”的道德訓(xùn)誡警告想過上好日子的農(nóng)民。無論三里灣黨支部,還是梁生寶,用來警告范登高和梁三老漢不要走個人發(fā)家道路的,都是楊大剝皮或呂二細鬼這類人物。這類人物在小說中只是一筆帶過,連“跑龍?zhí)住倍妓悴簧希麄冇譄o處不在。由于在土改中剛剛被鎮(zhèn)壓,被剝奪了財產(chǎn),因此,這類人物便成了合作化小說用來做“財富恐懼”道德訓(xùn)誡時最好的反面教員,好象共同富裕就必然排斥財富似的。另外,合作化時期的城鄉(xiāng)差別,在烏托邦視野中早已大大縮小,至少在意識形態(tài)意義上,農(nóng)民的社會地位空前提高,與城里的工人、市民是平等的。“鄉(xiāng)下”、“鄉(xiāng)下人”、“鄉(xiāng)巴佬”這類帶有城市文化優(yōu)越感的詞語幾乎已根絕。于是,馬多壽、梁大老漢即便有兒子在城里當著干部、拿著工資,也沒能引來“鄉(xiāng)下人”多少羨慕。但是,當改霞想進城去當工人的時候,梁生寶又覺得這城市和鄉(xiāng)村,還是隔著一層鴻溝的,執(zhí)意要跳出“農(nóng)門”的女孩子改霞,和他已經(jīng)不是一條心了。與此相關(guān)的,是上過學、讀過書的農(nóng)村青年在選擇對象時的“文化勢利”眼。本來合作化時期的知識青年并沒有什么特別的優(yōu)勢,甚至不如梁生寶這類沒有讀過什么書的農(nóng)家孩子。偏偏在戀愛的時候,傳統(tǒng)鄉(xiāng)村社會的“文化勢利”眼又會跳出來作祟。比如范靈芝疏遠馬有翼,傾心“愛迪生式”的青年王玉生,又嫌他沒上過中學的“文化勢利”心理。夏志清覺得這“應(yīng)該是個很有趣的題目”。
可見,新中國文學前三十年的烏托邦精神所造成的鄉(xiāng)土倫理的某種決定性的停頓和間斷只是暫時的。表面看來,合作化所建立的制度似乎使中國農(nóng)民再也不能依賴他們以前所深深依賴的某些制度和習俗了。但實際上,烏托邦精神和理想化的道德前景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被中國的農(nóng)民所接受的。他們對鄉(xiāng)村傳統(tǒng)價值的依賴從一開始就使得合作化意義秩序的建立危機四伏,只不過在1949年中國革命的巨大勝利面前,這種新的意義秩序帶有不容置疑的真理意味,因而傳統(tǒng)的習俗和制度便屏住了呼吸而已。沖突早晚是要發(fā)生的。這是一場文化沖突。盡管大同社會的理想不完全是舶來品,但大同理想畢竟從來沒有融入過中國的鄉(xiāng)村社會。也許正是因為如此,康有為的《大同書》才不肯輕易示人。現(xiàn)在,合作化制度雖然已經(jīng)有了新的文化內(nèi)涵,但要讓它一下子變成中國農(nóng)民自己的思想觀念,并從此改變鄉(xiāng)村社會運行的慣性軌道,其結(jié)果便可想而知。合作化小說忽略了文化沖突的艱巨性,用一種樂觀主義的態(tài)度描寫這樣的轉(zhuǎn)變,其悲劇性也就在所難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