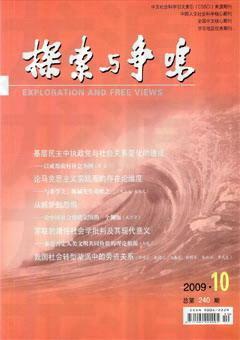“啟蒙與救亡”的變奏:孰是孰非
劉悅笛
內容摘要“啟蒙與救亡”的變奏,所言說的本是中國近代史的內在發展邏輯,同時它也成為近代思想史的基本主題之一。該學說的發明權之爭其實并不重要,關鍵在于哪種理論對歷史和現實更有闡釋力。“啟蒙與救亡”的歷史邏輯,一方面依賴于從嚴復、鄒容到陳天華這些歷史當事人的創造,另一方面又要通過李澤厚、舒衡哲和史華茲這些歷史闡釋者的闡發而獲得。實質上,“啟蒙與救亡”所面對的是一個兩難選擇的問題——國家富強與個人自由何者更重要?如今“救亡壓倒啟蒙”理應轉向“啟蒙就是救亡”,國家富強與個人自由應協調一致并相互補充,這也正是當代中國走獨立發展的道路所必需的。
關鍵詞啟蒙與救亡啟蒙就是救亡李澤厚舒衡哲國家富強個人自由
“啟蒙與救亡”的變奏,這本是中國近代史所蘊涵的歷史事實,但卻遭到了歷史闡述者或顯或晦、時榮時辱的誤讀乃至曲解。首當其沖的一個非常有趣的話題就是:到底誰最先提出“啟蒙與救亡”?
“啟蒙與救亡”的知識產權:歸李澤厚、舒衡哲還是史華茲
爭奪“思想”的知識產權問題,在中國學界是個有趣的現象,許多學者總是勇于擔當西方新潮的“第一個介紹人”。但關鍵不是誰最先發現或發明,而在于誰的說法最有說服力。“啟蒙與救亡”這個“歷史敘事句”,正是后來者對中國近代史發展邏輯的一種歸納。對這種變奏的發現,有可能是共同發現的,從而產生異曲同工的效果;也可能是先后發現的,或許彼此之間并沒有受到相互影響,但更有可能相互之間產生了交互的啟示。
但是,關于誰是“啟蒙與救亡”最早的提出者卻已引發了爭議,既有杜維明、王若水在媒體上為被遺忘的提出者鳴不平,又有林毓生、劉東等在私下發表意見。從學術影響來說,李澤厚的《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無疑是最具有影響力的文章。李澤厚從“學生愛國反帝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的區分出發,認定五四運動形成了“啟蒙與救亡的相互促進”的基本關系,并進而又將這種張力結構擴大到整個近代史。他認為,近代史的發展趨勢就是“救亡壓倒啟蒙”,并將林毓生提出的著名的“創造性的轉換”(creative transformation)轉而變為“轉換性的創造”,從社會體制結構與文化心理結構的兩個層面來面對如何轉化傳統的問題。
這篇以“雙重變奏”作為隱喻的文章發表于1986年初。但是,許多學者將最早提出此說的發明者指定為美國的歷史學者舒衡哲(Vera Schwarcz)。因為在舒衡哲1984年發表于海外期刊《理論與社會》上的《長城的詛咒:現代中國的啟蒙問題》中,更早提出了救亡與啟蒙之間的沖突,不過她用的關鍵詞是“救國”(jiuguo or nationalsalvation)而非“救亡”。該文的核心觀點是,中國第一次啟蒙的時間段為1915年到1921年,中國的啟蒙不同于歐洲啟蒙特別是法國式的啟蒙。首先,啟蒙的重點在于擺脫封建倫理;其次,心靈舊習的穩固性仍很突出;最后,作者明確努力去構建一種后政治啟蒙(post-political enlightenment)話語。但該文后面所論述的重心,似乎在證明,啟蒙運動在中國是發生在政治革命之后的,只是附著于政治革命身上的覺醒的宣言而已。也就是說,舒衡哲本人并沒有明確提出救國“壓倒”了啟蒙,這位歷史學者也并沒有將這一結論加以推演而應用于整個近代史當中。
有趣的是,舒衡哲本人將這篇文章送給了李澤厚,從筆者所見的第一手資料看,前者送給后者的文本落款時間是1985年12月16日。而且,李澤厚也的確閱讀了這篇文章,并在重點之處做出了標記。如果根據紙面的材料,可能是李澤厚受到了舒衡哲的直接影響,因為李澤厚閱讀《長城的詛咒》一文離《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的發表還有一段時間差。況且,舒衡哲還曾聲明說,“救國與啟蒙”的主題是她1982年秋季在所執教的衛斯廉大學的人文中心講課時最早提出的,并要收錄到她原定于1985年出版的專著《中國的啟蒙:五四運動與知識分子的遺產》(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the intellectuals'Legacy)當中,1986年該書正式出版的時候改名為《中國的啟蒙:知識分子與1919年五四運動的遺產》。
但是,李澤厚本人對此并不認同,這是因為他聲稱與舒衡哲早就結識。根據李澤厚自己的回憶,1981年之前舒衡哲就來過北京,李澤厚請她吃過飯并做過幾次關于中國近代史的長談。實際上,從1979年2月到1980年6月,舒衡哲就曾作為首批美國留學生在北京大學中文系學習。1981年李澤厚到美國也是應舒衡哲的邀請,據稱他們再次討論過近似的問題。
所以,根據這些歷史回憶,李澤厚認為,其一,“說她(指舒衡哲)抄襲我倒是可能的”,其二,關于“誰抄襲誰”的問題,舒衡哲在此后與李澤厚的謀面中從來都沒有當面論及此事。但另一方面的情況的確是,據王若水所述,李澤厚是在與舒衡哲聊天當中“獲悉”了這個觀點,然后就發表文章“占為己有”,后者為此非常生氣并專門撰文表示過抗議。由于資料所限,筆者并沒有找到王文所說的這篇文章。還有論者如徐友漁也證明說,舒衡哲認定“啟蒙與救亡”的學說是她首先提出來的,而李澤厚在宣揚和發揮這種觀點時卻“從不提她的名字”,從而使得該說的“發明權”被公認為是李澤厚。
究竟是李澤厚在與舒衡哲的交談當中“獲悉”了這個觀點,還是舒衡哲從李澤厚的早期的見面當中“習得”了這一觀點,作為“第三人”,我們都不是當事人,沒有足夠的證據就無法給出準確的判斷。但是目前的趨勢,的確是一方面由于學術影響力的原因,大多數人仍認為李澤厚才是最初的提出者,而且李澤厚是用現代漢語寫作的思想者(而舒衡哲的影響最初主要在海外漢學界),他在國內的影響遍及了包括歷史界的各個領域(他早期的許多文章大都發表在《歷史研究》而非《哲學研究》上);而另一方面,支持舒衡哲的聲音而今卻愈來愈大甚至已有“既成事實”的趨勢,這種在內心“同情弱者”的公論也成為了詬病李澤厚的事實來源。但是“公論”無論范圍大小,往往都不能與史實相匹配,還是得回到事實本身去“求是”。
在此,筆者既不想為舒衡哲匆忙翻案,更不想替李澤厚打抱不平,只是想給出兩個基本判斷。一個是“或然性”的判斷:這個說法被異曲同工地提出的可能性非常大,即使舒衡哲曾聲稱1982年授課時就提出了此說,但是我們卻可以發現,在李澤厚1979年公開發表的論文中已明顯包孕了這個說法的雛形,在下面我們還要對此詳論。非常可能的是,這個說法本來在李澤厚和舒衡哲的內心都是一個“模糊的共識”,他們于20世紀80年代早期見面的時候,“啟蒙與救亡”的說法被相互激發了出來。不過可以肯定的事實還有,當時李澤厚早已在中國思想界“顯山露水”,而舒衡哲在漢學界才剛剛“嶄露頭角”。
另一個則是“必然性”的判斷。無論是李澤厚所說的
“啟蒙與救亡”,還是舒衡哲所論的“啟蒙與救國”,其實所說的都是一個意思,我們暫且不論誰先提出,但是可以基本肯定,“變奏”的說法就是來自李澤厚。從比較的視角看,李澤厚與舒衡哲論述的基本差異在于:其一,李澤厚明確提出了“壓倒說”,從他早年認定“反帝”就是近代史首要命題始,就已經明確認定了救亡壓倒了啟蒙;其二,李澤厚試圖將這種“壓倒說”貫穿到對整個中國近代史的闡釋當中,而顯然舒衡哲還沒有如此恢弘的視角和闡釋的野心。她更多聚焦于五四運動這場其所謂的“未完善的啟蒙運動”,盡管她也承認“啟蒙與救國”形成了長期存在的張力結構,但卻始終沒有像李澤厚那樣將相應的思想貫徹為歷史的“發展邏輯”。可以肯定的是,舒衡哲作為歷史學研究者與李澤厚作為思想者的視角并不是完全重合的,他們提出“救亡(或救國)與啟蒙”的立足點并不相同,舒衡哲更多是就歷史狀態本身來言說的,而李澤厚卻是將這種雙重變奏作為“歷史教訓”來論述的。簡言之,舒衡哲是“從歷史到思想”,而李澤厚則是“從思想到歷史”,前者是自下而上的,后者是自上而下的。在這個意義上,二者的基本觀念是否可以被看作是一種“同體的互補”?
如果我們再往前追溯,除了這個Schwarcz之外,另一位大名鼎鼎的中國思想研究專家本杰明·史華茲(Benjamin Schwartz)在研究嚴復的時候,也曾經隱含地表露了類似的思想。有趣的是,這個Schwartz與舒衡哲的英文名Schwarcz只差一個字母,翻成中文都通譯成“史華茲”。那么,“啟蒙與救亡”的知識產權,到底是歸中國的李澤厚,還是美國的“兩個史華茲”呢?
從嚴復到鄒容和陳天華:誰來“啟蒙”,誰來“救亡”
眾所周知,本杰明·史華茲曾經在1972年編輯過《五四運動的思考》(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1972)的論文集,并在1964年出版了他的成名作《尋求富強:嚴復和西方》。在史華茲的恢宏視野里,“在嚴復的關注中,占突出地位的仍然是對國家存亡的極大憂慮。這些(自由主義)原則可能有它們自己抽象的內在價值,但是,引起嚴復最強烈反響的,卻是它們作為達到富強的手段這一直接價值”。
按照這種分析邏輯,從嚴復發出本土化聲音的時代開始,富國強民的訴求,就已經在中國知識分子中形成了某種“集體無意識”。當然,當時嚴復所依據的主要還是“社會進化論”的觀點,要富強就要成為“適天”者,而中華民族要得到“天之所厚”就要“循天”而動,這一方面會引導國民走向富強,但另一方面又需要普遍價值來規范國民行為,這實際上就是走向所謂的“啟蒙”。
就史實來看,嚴復早在1895年的《原強》中就已提出,“是以今日要政統于三端:一日鼓民力,二日開民智,三日新民德”,但嚴復所主張的所有一切啟蒙“新民”的說法,都必定服從于國家和民族的危機,他的自由主義的基本觀念也必定以富國強民為目的,這可謂是東亞社會近代思想界的普遍現象。由此可見,所謂的“富強壓倒自由”、“外競壓倒內競”,究其實質就是——“救亡壓倒啟蒙”!但是,嚴復的思想還只是有了啟蒙與救亡的思想萌芽,并不能說他直接提曲了這樣的主張,畢竟他還只是歷史的當事人,盡管在老史華茲的闡釋當中嚴復思想的內在邏輯已經被揭示了出來。
實際上,嚴復已經提出了一個近代史上的重要問題,或許對于中國知識分子來說是根本性的問題,那就是:我們究竟要的是“國家富強”,還是“個人自由”?“國富”與“自由”到底哪個重要?這也是近代以來的思想史的核心問題之一,盡管嚴復打內心深處選擇了自由,但卻始終認為尋求富強的目標在現實中是高于個人自由的。如果運用漢學家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所說的那種“情感與理智”的悖論邏輯來說,那就是,在情感上向往自由,但在理智上卻毫不猶豫地接受國富民強的基本目標。這的確是從近代到現代許多中國知識分子的共同思想悖論。思想問題在中西沖突的本土語境中始終難以在純理智的層面加以解決,事實上也不能只囿于這個層面來加以解決。
換個角度來看,李澤厚所說的“救亡壓倒啟蒙”,用更熟悉的話語來解釋,就是“反帝”壓倒了“反封”。這種觀念在李澤厚那里成形于20世紀70年代末,對“反帝與反封”的基本矛盾的這種闡釋,可以被視為“啟蒙與救亡”說的最初來源,起碼對李澤厚來說正是如此。有事實為證,李澤厚在發表于《歷史研究》1979年第6期的《二二十世紀初資產階級革命派思想論綱》中就曾經反復論證過:“反帝是中國近代一個首要命題。”
啟蒙與救亡的沖突,在李澤厚20世紀70年代末已成熟的論述當中,就已明確而集中存在了:“五四運動提出科學與民主,正是補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思想課,又是開新民主主義的啟蒙篇。然而,由于中國近代始終處在強鄰四逼外侮日深的救亡形式下,反帝任務異常突出,由愛國而革命這條道路又為后來好幾代人所反復不斷地再走…~方面,歷史告訴我們,經濟基礎不改變,脫離開國家、民族、人們的富強主題,自由民主將流于幻想,而主要的方面,則是沒有人民民主,封建主義將始終阻礙著中國走向富強之道。從而,科學與民主這個中國民主革命所尚未實現的目標,仍然是今天的巨大任務。”由此文可見,“啟蒙”與“救亡”,“自由民主”與“富強主題”,“科學民主”與“富強之道”,已經形成了互文之勢。
進一步從歷史線索來看,“啟蒙與救亡”的沖突,在李澤厚最初的構想那里,就表現在——講求“啟蒙”的鄒容與講求“救亡”的陳天華之間的思想對峙。我們不妨抄錄如下兩段來證明這種思想對峙,在此,做出大量的引述也是為了證明“啟蒙與救亡”說在李澤厚早期思想那里是如何被孕育的,這也恰恰是為人所普遍忽視的。
第一段是說鄒容的“啟蒙”——鄒容的《革命軍》的特點是“全面地、明確地宣告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口號、綱領、政策、原理,是整個革命派的最早最鮮明的號角。它把比較徹底的天賦人權說、民主共和制,盧梭、華盛頓,法國革命綱領和美國獨立宣言……統統以明朗的語言搬了進來。”第二段是說陳天華的“救亡”——“如果說,鄒容《革命軍》的基調是反封,那么,同樣受到狂熱歡迎的陳天華的作品——《猛回頭》、《警世鐘》、《獅子嘞等基調則是反帝……如果說,前者著重宣講的是為民主自由而革命,那么后者著重宣講的是為愛國、救國而革命”。
由此可見,從當時的歷史境遇來說,如此急迫痛切的“國家種族的危亡感”,如此憤激慷慨的“救亡呼聲”,都證明了“救亡愛國”成為壓倒性的主題。這也就從另一個角度解釋,盡管鄒容與陳天華在當時的歷史階段都影響甚眾,但是為何陳天華的“救亡”最終壓倒了鄒容的“啟蒙”。孫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后,曾贈與鄒容以“陸軍大將軍”的美謚,并崇祀宗烈祠,這倒正好像一個救亡壓倒啟蒙的“象征”(因為鄒容更像是一位書齋里的革命者)。
因此,正如李澤厚在寫于1978年秋的《中國近代思
想史論·后記》當中所總結的那樣,“中國近代緊張的民族矛盾和解放斗爭……把注意和力量大都集中投放在當前急迫的社會政治問題的研究討論和實踐活動中”。從這種歷史的眼光來看,在嚴復內心深處糾結著的——擔當“救亡者”還是“啟蒙者”的矛盾在近代史上始終是凸顯著的,但嚴復最終還是選擇了前者,鄒容則想擔當理想化的“啟蒙者”的角色,而陳天華無疑是一位現實化的“救亡者”。
如此看來,我們今天再去爭論究竟誰是“啟蒙與救亡”的第一個提出者;亦即知識產權的歸屬問題,其實并不十分重要。關鍵還在于持“啟蒙與救亡”說的哪一位論者的理論更有闡釋力?哪種理論對整個近代史能給出更具新意的闡發?究竟是誰的思想對于當代中國思想界產生了更為深遠的影響?
再退一步而言,無論是“啟蒙與救亡”如何變奏,它們描述的不過都是近代史的事實而已,這同時也是近代思想史的基本主題之一,而這一事實從嚴復、鄒容到陳天華的理論和實踐那里都已經顯現了出來。最重要的就是,一方面通過歷史當事人的創造,另一方面通過歷史闡釋者的闡發,“啟蒙與救亡”的內在邏輯已經非常清晰了。實際上,“啟蒙”在中國(從對立面來說)首先就要面對“反封”,進而(從正面來說)才能直面“科學與民主”的問題,而中國的“救亡”(從對立面來說)首先就要面對“反帝”,同時這也就是(從正面來說)追求獨立和解放的“民族運動”,“反帝”在近代史上是當務之急,而“反封”至今仍是棘手難題。
“啟蒙就是救亡”:“國家富強”還是“個人自由”
如前所論,從嚴復的思想矛盾當中就可以得見,啟蒙與救亡的實質,其實就是面臨一個兩難的選擇——“國家富強”與“個人自由”誰更為重要?
這是因為,按照雙重變奏的思想邏輯,“啟蒙”無非就是指對于西方“德先生”與“賽先生”思想的接受和傳播。這種科學與民主的思想,在歐洲語境當中更多是同“個人自由”相關的,而在中國的特殊語境當中這二者則都是用來同時“反封建”的。相比之下,“救亡”卻是諸如中國這樣的第三世界國家獲得解放和贏得獨立的民族運動。事實上,在任何一個遭遇列強的第三世界國家那里,首要的任務都是“反帝”,而“反帝”的最終目的不僅僅是“民族國家”或者“多民族國家”(如中國就是其中的典型)的獨立,而且更要走向“國富民強”,這是獨立之后必然選擇的“后發現代化”的社會目標。
由此來反觀五四運動的得與失,就可以非常明顯地看到,在激情四射的新文化運動之后,盡管“啟蒙的計劃”已經理性地被建構了出來,但卻由于救亡的重任而遲遲沒有被真正地執行開來。更重要的問題,正如老史華茲所追問的那樣:“啟蒙時代觀念的主流,似乎是在社會政治秩序中尋找人類困難和罪惡的根源。而它的樂觀主義則基于這樣的假設:一個理性與自然協調的新社會政治制度能夠建立起來。然而問題在于:誰來建設這一新制度?”老史華茲其實隱含地指出了中國啟蒙之路的缺陷——啟蒙往往停留在高蹈的文化理念上,而沒有真正落實到具體社會制度的建構。
這種啟蒙思路,決定了中國社會的設計者們在“文化啟蒙觀念”上的方法論缺陷。它首先表現為林毓生所謂的“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基本思路,它強調文化變革優先于政治、經濟等社會變革的決定性和前導性。因此,五四時期無論是激進西化的陳獨秀們還是力主保守的梁漱溟們,都將變革的當務之急歸于“文化運動”而非“政治的問題”,而后代的文化論爭也基本遵循了這一思路。與此同時,還有一種“理想化”的致思取向,它具體表現在無視社會的“可能”性的現實變遷,而只是設計文化“應當”如何發展,也就是以理念性的“應當”取代了現實性的“必定”。但是,“新制度”的建構卻顯然是更為復雜的系統社會工程。
這也正是中西啟蒙進程的差異。西方啟蒙運動最初來自于西歐的“先發現代化”,其歷史進程當中“啟蒙者”的自我建構與現代社會政治制度的建構是大致相互匹配的。從德國哲學家伽達默爾的“歷史大視野”來看,歐洲社會起碼出現了兩次,第一次是在古希臘,第二次則在18世紀。歐洲的啟蒙主要面對的對象就是宗教,“啟蒙時代”往往與“宗教批判時代”成為了同義語。但是除了對待宗教的態度之外,歐洲啟蒙還有一個重要對象那就是科學,而科學在兩次啟蒙中所扮演的角色卻是相反的:“在古代,啟蒙最終導致了對科學的反對;在近代,啟蒙則完全依據科學。”相比之下,“中國式啟蒙”的特殊性就在于,一方面既沒有宗教的問題的困擾,這是實用理性的文化所造成的社會后果;另一方面,雖在口頭上宣稱接受科學精神,但實質上真正接受卻又何其難也!進一步看,更為特殊的情況還在于,在中國無論是“啟蒙什么”和“如何啟蒙”,都要面對傳統文化這個積重難返的問題,如何去“創造性的轉化”抑或“轉化性的創造”本土傳統,百余年前與當下所面臨的情境似乎始終沒有多少改變。
對于“救亡已壓倒啟蒙”的中國而言,“啟蒙者”自身很難在歷史的動蕩當中迅速成熟起來。所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份歷史缺憾仍在于“啟蒙尚未完成”,但同時也遺留下來這份豐厚的歷史遺產供后來人來繼承,給后來的知識分子照明道路以繼續前行。在此,林毓生對五四的“三個層面”的區分非常精妙:那就是具體的“五四口號”、“五四的理念”和“五四的精神”。他認為,口號可以商榷,理念可以批評,但是五四的精神決不能丟棄!由此來看,中國啟蒙的時代依然是“現在進行時”。
如果真的如20世紀30年代至今的許多知識分子認定的那樣,五四新文化運動是“激情有余”,“理性不足”的話,那么可以說,這場運動恰恰是以“感性的形式”提出了“啟蒙的理性任務”。有趣的是,李澤厚在紀念五四運動70周年紀念會上,又提出了“啟蒙就是救亡”的觀點。那么,在這種科學、民主與傳統相交織的復雜局面之下,如何繼續完成中國的“啟蒙的計劃”?
顯而易見,我們現在面臨的情況的確已今非昔比,既不是嚴復、鄒容、陳天華的年代,也不是從五四運動到新啟蒙運動那個時代,今日的中國至少已經沒有救亡之虞了。但在“救亡”的基本任務完成之后,后續的革命不但沒有使得“啟蒙”得以繼續推動下去,反而在一定的歷史時期之內使得傳統的舊意識形態繼續登場,“文化大革命”就是“啟蒙不徹底”的歷史教訓之一,當然這里更有“現代化”與“現代性”建構之間的矛盾張力問題。如林毓生就曾區別過“Rule by law”(法制)與“Rale of law”(法治)的微妙區別,中國社會為何更多采,取的是前者而非后者呢?部分原因或許就在于救亡壓倒啟蒙。
然而,在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之后,我們已經開始走上了國富民強之路,但是對(與國家相對的)個人問題的解決也還只是處于初級階段。在啟蒙的意義上,不僅“啟蒙者”還有“被啟蒙者”的自我建構就變得尤為重要了。按照康德的基本理解,所謂“啟蒙”最終是對于個人而言的,其核心問題就是“掌握你的理性”,但問題并不僅僅是“覺醒與支配”那么簡單,這里似乎還有“理性的共同使用”等諸多問題。所以,在當代中國正在進行的新啟蒙運動中,個人自由問題在中國仍要在“集體主義”而非“原子主義”的基石上才能加以解決,理性的“公共性”問題在中國應該是更加突出的問題。
實際上,“啟蒙就是救亡”所說的“救亡”已非民族解放和獨立意義上的“國家和民族的救亡”,而更多是指向了一種更新意義上的“文化救亡”。盡管市場機制正在逐步建成、民主體制也在逐漸完善,但是即使這些任務都基本完成了,什么樣的中國社會才是“中國的”社會呢?換句話說,中國社會的“中國性”(Chinese-ness)到底從何處找尋呢?照此意義來講,“啟蒙就是救亡”所言說的乃是一種理想狀態,那就是“國家富強”與“個人自由”能夠在未來中國的發展當中得以協調一致并相互補充,這也正是當代中國走獨立發展的道路所必需的,難道不是這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