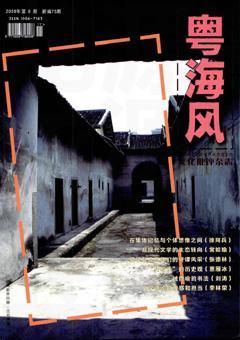文學評論的惶惑和擔當
李林榮
一
當前,文學評論正遭遇一種“于浩歌狂熱之際中寒”的尷尬:一方面,文學評論的作者和產出,都顯示著空前龐大的存量和增量規模;另一方面,在影響以作家和讀者為主體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接受群體的實際效果上,格局如此盛大的文學評論,卻又分明暴露著渙散、浮乏的“話語泡沫化”癥候。對這樣的情形,文學圈內外都已多有不滿。
本職并非文學評論的作家和一般讀者,早厭煩了在概念游戲里空兜圈子的那路虛頭巴腦、言不及義的文學評論,因而他們對時下文學評論這種虛熱癥的不滿之中,更帶有些“活該如此”的鄙薄。而在文學評論的專業人士和行家里手們看來,環繞在內部沸騰不息、熱力四射的文學評論話語圈以外的,居然是無人喝彩、乏人問津、青眼和白眼的投射都一概疏落的滿目冷清,文學評論本身固然應負一份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文學評論圈外的社會條件、文化風尚、大眾心理等環境因素,也絕對脫不了干系,必須承擔一份“什么樹上開什么花、什么土壤長什么莊稼”的連帶責任。
顯然,由于角度和立場的不同,文學評論的作者和讀者、生產者和消費者,感受和分析文學評論現狀及其成因的思路與結論,并不完全一致。不過,這也正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文學評論如今確已深陷寫作和接受、生產和消費兩端嚴重不對稱、不均等、不順暢的傾斜、失衡和壅塞狀態。從寫作和生產的一端看來:收納、投放、設置在文學評論這一文體模具和話語框架內的解析對象、理論資源和問題意識,都正與日俱增地紛繁復雜起來;文學評論的思維基礎和方法運作,也正前所未有地朝著縝密周詳的技術化、規格化的方向加速奔趨;而展現在文學評論的視野疆界和話語場域上的那種度越古今、橫亙中西的氣勢和縱深度,則更是在全面的加強和提升中,達到了新的歷史性標高。但文學評論生產環節上的這種種專業技術含量不斷升級的變化,一經推衍到傳播、接受或流通、消費環節,就都迎頭碰壁似地陷入橫遭冷遇、無人買賬的尷尬狀態。而且,越是專業旨趣濃厚、學理色彩亮麗的文學評論,往往還越是容易被作家和讀者“同仇敵愾”地漠然置之或者忿然斥之。
要細致剖視這類現象,在就文學論文學的專業視角之外,社會心理學和傳播學等文學理論范疇以外的思路和方法的助益,也是不可或缺的。換句話說,當前文學評論所面臨的這種在生產環節“高熱”而在傳播、接受及消費環節“遇冷”的問題,實質上是與文學評論的作者/生產者、傳播者/流通者、接受者/消費者多重主體具有共時性的同等程度關聯的復雜問題,這樣的問題不是單單通過苛責或追究文學評論的作者、讀者或傳播者中的任何一方主體,就能求得解決的。從傳播學的意義上看,這是一個與文學評論的發送者、傳遞者和接受者同時相關的信息量和信息價值雙重衰減的問題。從社會心理學的意義上看,這又是一個文學評論的作者和受眾群體的文學觀念、文學價值和文學需要等認知背景發生錯位和悖反的問題。兩面合觀,則可以說,這是文學創作和文學評論及其相互關系的意識形態背景,在一個價值多元化和分眾消費主義的特征日益凸顯的社會轉型時代,經歷深層沖突和根本蛻變的問題。
二
法國文論家阿爾貝·蒂博代在距今八十多年之前,曾對其所處時代的歐洲文學評論,做過“自發的”、“職業的”和“大師的”三大類型并行一時的描述和分析。遙隔時空,以史為鑒,我們眼前文壇上的文學評論,也顯而易見地存在著因話語主體、媒介載體、運作規則、價值訴求和文化功能的不同而形成的類似多元拼圖和多層堆壘的狀況。除去“大師的”評論形跡不彰之外,分別以媒體記者和學院派師生為主體的“自發的”和“職業的”評論,仍然可說是現今我們文學評論界的主力構成。換用我們近年來慣用的稱謂,前者也即“媒體評論”,后者也即“學院派評論”。
這兩類文學評論一般易有的利弊得失和優缺長短,蒂博代當初在《批評生理學》里早有鞭辟入里的剖析、論斷。據此衡量,我們今天的情形,幾乎沒有任何一點可以傲對前人的超越性。例如,兩者都同樣免不了沾染“不讀而論”或“未讀先論”的自欺欺人作風,也同樣規避不開劃圈子、立門派、黨同伐異、嫉賢妒能的團伙山頭習氣。而前者所特好的追風逐潮、營造時尚、炮制熱點之弊,以及后者所專有的厚古薄今、挾“史”自重、崇信知識教條而蔑視鮮活的作家作品之弊,當然也都在我們如今的“媒體評論”和“學院派評論”中,各自得到了很完整的傳承。
然而,所有這些,都只能算是文學評論與生俱來的先天局限。局限固然不好,但這類先天性的局限,歸根結底是與生機和活力伴生在一起,屬于同一肌體的不同面相,對其有必要小心節制以防惡變,卻不可能也不應該徹底割棄。換句話說,如果我們當前文學評論所面臨的種種問題,只能被歸集到這一層次,那其實也就意味著這些問題是根本無解的。正是基于這一點,我們有理由毫不遲疑地繞開針對文學評論現狀和文學評論寫作者的群體人格所展開的道德圍攻和倫理審判,從文學評論作為社會話語的一種特定形態所勢必依賴的那個由生產、傳播、接受、反饋幾個環節雙向連鎖、無限循環、連綿交織而成的信息和意義的雙重社會化螺旋出現梗阻的意義上,去分辨和確認問題的癥結。
文學評論作為一種社會話語的意義,首先在于將文學評論從發生、傳播到接受、消費的過程,歸結為文學評論的“生產”與“再生產”過程,其中,文學評論的作者完成文學評論的第一度“生產”,文學評論的傳播者和讀者則進行文學評論的“再生產”,所謂文學評論的“再生產”,也就是對文學評論的評論。其次,文學評論的社會話語性質還包括這樣的內涵:只有當文學評論的作者/生產者和文學評論的傳播者/流通者、接受者/消費者在文學基本的觀念認知和價值判斷上都達成一致,也即文學評論的寫作/生產、傳播/流通和接受/消費各環節上都共享相同的文學觀念和價值尺度時,一個正向、順暢的文學評論的話語生產和再生產過程才能夠實現。否則,文學評論話語的社會化過程就必然遭遇梗阻,或者說,這個過程就不能成為一個信息暢達交流、共識持續累積的過程。
依照上述闡釋模式,文學評論的作者/生產者、傳播者/流通者和接受者/消費者之間的不協調現象,是以他們在文學觀念和文學價值上缺乏基本共識的事實為基礎的。離開這層事實基礎,前列三者間的不協調狀態,也就無從獲得恰切、合理的解釋,更談不上改變。
三
以施予受眾群體的接受效應而論,文學評論和文學創作的功能幾乎是向度相反的:文學創作更多地傾向于促進受眾群體在價值信念層面上發生個體分化,而文學評論則更多地傾向于凝聚和整合受眾群體的價值共識。簡單地說,文學創作具有價值“分眾”的作用,文學評論卻具有價值“聚眾”的作用;文學創作更宜于在一個宏大價值主體突遭瓦解的時代里產生威力,而文學評論,則更宜于在參與建構一個宏大價值主體的過程里得到充分表現。
迄今為止的當代文學史六十年中,前半段的三十年,適逢整個社會文化價值體系日益趨向宏大化和總體化的特定時期,即“十七年”和“文革”時期;后半段的三十年,也即自“新時期文學”發軔至今,則恰屬全社會的總體價值體系告別“大一統”,轉向多樣、多元并存和科層分化的深刻轉型時期。正是在后半段這三十年間,我們的文學評論領域開始日勝一日地形成了目前這般局面:“媒體評論”的眾語喧嘩聲調連連高漲,“學院派評論”通貨膨脹似地陷于信譽破產,享有公認權威的“大師”的徹底銷聲匿跡。
比起一個有中心、有權威、整飭有序、高度組織化的局面,一個充斥了誰也不服誰、誰也不信誰的一派聒噪、囂鬧,缺乏一言九鼎的權威和一錘定音的主調的局面,顯得不甚雅觀,也不夠規矩。但這樣的局面之所以出現并在一個時期內穩定存在,究其根本,實際上還是文學評論整個行當在主動和被動、自覺和不自覺之間迫不得已地適應了社會變化和時代要求的結果。
意識到這一點,我們自然就會放棄那種試圖對當前文學評論界展開道德批判和德行教化的無謂努力(——除非這種批判和教化能先行在全社會層面取得成效),同時,也可避免有意無意地把過往時期的文學評論和社會環境的共生形態奉為圭臬,進而據此對當前的文學評論做出“以古例今”的誤判和“削足適履”的妄斷。現實留給文學評論的權利,不是如何通過改變外部環境來謀求自身的優化,而是如何通過自身的調整和改變,來達到更積極地作用于外部環境的目的。
有基于此,不難理解:當前文學評論各式各樣的癥候,很大程度上是由我們下意識中頑固保持著的那個對于上一個文學史時期的刻板記憶所引發的。假使我們不是從一個社會和文學的價值體系高度一體化的時代邁進到今天,或許對于今天的文學評論,我們的觀感和判斷將完全不同。
這樣來看,擺在當下的文學評論作者面前的問題,就不再是高調的“應然律”或“必然律”式的問題,而是低調的“或然律”和“偶然律”的問題。具體地講,就是思考現在的文學評論應該如何或必須如何的問題已然毫無意義,探求文學評論現在可以如何和能夠如何的問題倒還比較切實。說得更明確、更堂皇一些,就是:要消除當前文學評論的“惶惑”感和“無力”感,唯一有效的途徑只能是讓文學評論自己來更新和變換自己擔當的職責或使命。隨后,通過職責、使命的改變,再進一步逐漸實現社會角色和文化身份的改變。
四
提及文學評論的職責、使命和社會角色及文化身份,我們司空見慣、習以為常、因襲至今的內容,是品第、鑒定,好處說好、壞處說壞,灌溉佳花、剪除惡草,是作品的裁判、作家的教練、讀者的導師、文藝政策戰線上的哨兵和巡邏兵,是整個文學創作事業的領航員、監護人和評斷者。——這都是一個已經具備或正在積極尋求廣泛的價值共識的文壇所必需的和所歡迎的,也是一個正在經歷全方位的價值分化和重構階段的文壇所必然抵觸、必然排斥的。
對于后者而言,文學評論與其擔當品第、鑒定之責,不如擔當闡釋、對話之責;與其好處說好、壞處說壞,不如多分析分析好處何以成為好處、壞處何以成為壞處;與其灌溉佳花、剪除惡草,不如多去論證“佳花”之“佳”和“惡草”之“惡”有無相反相成的內在關聯;與其當裁判、教練、導師,以至哨兵和巡邏兵,不如降低身段、丟開理性和知性的傲慢、收起居高臨下以勢壓人的嘴臉,拿出直面文本和人性的更多誠意,來做與作品、作家和讀者平心相對、坦然交流的朋友。
尤其是當文學市場和新傳媒的發展臻于完備、成熟之際,把文學評論的功能重心,從孤立地度量、評定文學創作的價值,轉移到對文學創作及其復雜多樣的接受效應進行多向度的詮釋、溝通和斡旋,這事實上已經不再是可供文學評論的寫作者們單方面進行或是或否的選擇的一件事。因為相較于文學評論界始終只是流轉在筆墨唇齒間的那種紙上談兵式的褒貶抑揚,直接反映著作家作品商業價值的即時兌現率的文學市場數據的反饋,顯然對文學創作實踐更具立竿見影的評估效能和引導作用。
此外,在品鑒文學作品細節上的妙處或敗筆,以及尋繹相關作品的互文意蘊方面,以博聞強識的個人學養為基礎、以僵化封閉的學科壁壘為界域的專家型文學評論,也因基于互聯網的新媒體和數字信息即時共享技術的極大普及,和由此所致的平民化的個人“自媒體”的大規模盛行,而開始經受致命挑戰。越來越多觀點警辟、發現獨到、文筆生動的文學評論見解,如今都已慣于從互聯網始發,并借互聯網獲得范圍最廣的傳播面和接受面。或者應該反過來說,以互聯網為主陣地的文學評論,已經挾理論上沒有任何設限的個人“自媒體”化和無遠弗屆的“信息共享/共產”這兩大優勢,日漸明顯地贏得了同傳統的紙介質文學評論相抗衡甚至更勝后者一籌的實力。
在這樣的客觀情勢之下,文學評論必須經歷全面的移形換位,然后才能重獲自己應有的尊嚴。這種復歸的尊嚴,絕不是為文學評論家們重披文學法官的制服或長袍,相反,它要讓從事文學評論的人們首先學會誠懇地謙卑地面對文學內外的雙重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