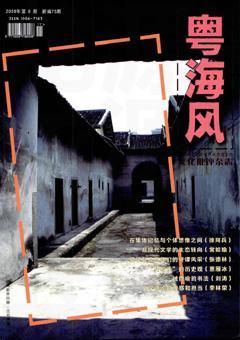略談節日文化之守正創新
顧 農
我們中國歷史悠久,節日很多,這是我們精神家園里的一些景點,非常值得珍惜。
從歷史的發展來看,傳統的節日中也多有變化:有些曾經比較重要的節日后來不再流行,現在大概基本沒有人過了,例如上巳,又如盂蘭盆節。上巳后來大抵為清明所取代,盂蘭盆節本是佛教徒的節日,當佛教不是那么最流行之后,它也很自然地就被淡化了。
始終沒有被淡化,一直最受重視而且時間跨度最長的是春節。按舊時風俗,進了臘月門就要忙年了,臘月初八尤其是一個重要的標志;一直要到過了正月十五的元宵節(甚至二月初二)才算結束。民國初建時國家規定只過陽歷的元旦,陰歷年被取消,政府機關照常上班;但民間并不買賬,還是很隆重地過陰歷年,不過陽歷年。魯迅先生的小說《祝福》一開頭說得好:“舊歷的年底畢竟最像年底,村鎮上不必說,就在天空中也顯出將到新年的氣象來。”民俗的力量是很巨大的,行政命令取消不了它。到1934年,當時的政府明令撤消關于廢止陰歷年的規定。
過年以外其他節日也就一天。經過多少年的考驗和淘汰,春節之外有兩大節日,這就是端午和中秋,加上春節合稱“三節”,家里的小孩子和仆人在這三節可以領到一點獎金(賞錢);如果有什么外債,到節下一般來說應當還掉。魯迅有一篇小說《端午節》,其中說,兼做教員的官員方玄綽因為學校和政府全都欠薪,弄得經濟緊張,其時正是端午節的前一天,他打發仆人到酒店去賒一瓶“蓮花白”來,“他知道店家希圖明天多還賬,大抵是不敢不賒的,假如不賒,則明天分文不還,正是他們應得的懲罰。”方先生還不禁動了一下買彩票的念頭。過節還錢,我不大清楚現在是否還有這樣的習慣。應該說這是個好習慣。
“三節”之外還有一個清明。二十四節氣中清明最受重視,因為這是掃墓祭祖的傳統時機,中國人特別尊重祖先,每年是非掃墓不可的。
過去只有春節才放假;現在端午、中秋再加上清明,四大傳統節日都由國家明確下來了,這是很得人心的。假期有了,怎么過這些節日很值得研究。單是吃粽子還不是端午,隨便哪一天都可以吃,快餐店里天天有得賣。大而言之,乘此幾大節日的機會改善一下伙食當然是不言而喻完全可行的,對拉動內需也頗有意義;但只是大吃一通也沒有什么太大的意思。想改善伙食哪一天不行,何必一定都擠在這里?這四大節日最好都能有一些讓人印象深刻的、值得留戀的文化內容,而且要讓老、中、青、幼各有所得。節日要有節日獨特的魅力,非得好好過不可,不能變得可過可不過,成為雞肋似的東西。
為了讓傳統節日富有魅力,起到文化認同凝聚人心的作用,“守正創新”是完全必要的。
所謂“守正”就是要繼承悠久而且優秀的傳統,讓這些節日繼續保持強烈的中國色彩。過年舞獅子,端午賽龍舟,中秋賞月,清明上墳都是好傳統。還有些更細微的東西也大可發揚,例如唐人過清明(以及寒食)喜歡賽球(“蹴鞠”)、拔河、斗雞、蕩秋千、放風箏,如此等等。王維詩云“蹴鞠屢過飛鳥上,秋千競出垂楊里”(《寒食城東即事》),杜甫詩云“十年蹴鞠將雛遠,萬里秋千習俗同”(《清明》),可見這兩項運動最為流行。現在也不妨在清明這一天舉行傳統體育項目運動會,大家走出家門活動一下。
繼承優秀傳統還有一層意思,就是消解一些不良的不合時宜的傳統。清明掃墓祭祖,慎終追遠,本來是很有意義的,只是古人習慣于在家門口或墳墓邊燒紙錢,那就不必繼承了。在古人的觀念里人死后仍然過著與活人大抵類似的生活,無非是在另一個世界里,所以也要花錢,燒一些紙錢就等于給匯過去了;此外還有燒家當的,用紙扎成房子家具,也在墳前燒給逝者。這個傳統就不科學,沒有道理,完全可以取消。宋代詩人高翥《清明》詩云:
南北山頭多墓田,清明祭掃各紛然。
紙灰飛作白蝴蝶,淚血染成紅杜鵑。
日落狐貍眠冢上,夜歸兒女笑燈前。
人生有酒須當醉,一滴何曾到九泉。
頸聯二句說白天掃墓時墳地里固然顯得人氣很旺,一旦太陽落山,祭掃者離去,就變成一片冷清,狐貍們就睡在這里;掃墓者回家,恰恰可以享受一家人團聚的天倫之樂。這是很殘酷的對比,也是常見的情形,詩人由此逼出尾聯來,自有他的道理,并不完全是消極。同樣的道理,燒紙錢也毫無用處,一分何曾到九泉,只是污染空氣,而且容易引發森林火災。有這份孝心,不如平時多給家中老人多一些關心,如有必要就多送上一些錢。錢只對活人有用。
掃墓而燒紙,在今天應視為不文明的行為。我曾經偶爾見過幾種上面印有“冥國銀行”字樣的紙錢,面值很大,紙質甚劣,上面且有錯字。現在也還有扎家當燒家當的,不單有房子家具,還有電視機、冰箱、電腦……好像很現代化的樣子。熱中于燒這些高級家當的人在器物層面確實是現代化了,而思想卻十分陳舊,堅持的是古代落后的東西,頭腦還不如高翥清楚。此種古風亦可以稍息矣。
過年放爆竹放煙火當然也是傳統,但恐怕要適當加以限制,加強管理,嚴防火災發生,這一方面教訓很多,弄得樂極生悲,豈非大背初衷。
在傳統中取其精華棄其糟粕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完全靠行政命令,除了最必要的規定之外,主要得靠啟蒙,靠教育,靠引導。
如果說守正還比較簡單的話,創新則相當不容易。這不是關起門來策劃可以奏效的,我想可行的路徑有三條:
一是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如果發現哪里有為群眾所喜聞樂見愿意參加或實行的過年過節的好辦法,就通過媒體加以宣傳、推廣,供大家參考。
有一次在電視里看到某地在中秋之夜舉辦街舞大會,月光下充滿了歡樂的人群。這是個好主意。群眾的首創精神是無窮無盡的。
二是加進一些比較新潮的內容,試驗一下,看是否行得通。例如端午節,因為紀念屈原的關系也叫詩人節,不少地方舉行詩會、詩歌朗誦會,除了寫舊體、誦古詩以外,是否也可以寫些新詩,朗誦新詩,也可以唱各路新舊之詩。清明掃墓固然很好,但還有不少無墓可掃的人,要為他們考慮些適當的活動才好。現在農民工等流動人口數量很大,節日活動如何適應他們的胃口,很值得研究。沒有民俗內涵的節日,總是少了些什么。
過去,過年過節總是以家族、家庭為基地;現在傳統的大家庭已經很少見了,小家庭怎么過節?怎么能讓小孩子(他們在小家庭中處于某種中心的地位)喜歡過節并從中受到傳統的熏陶?社區怎么安排節日的活動?這里有許多值得探討的問題。過節日既要守住傳統,又要趕上時代,否則就很容易漸漸淡化、萎縮,讓人找不到感覺。
三是加強風俗史的研究,看看這些重大節日古人是怎么過的,其間有些什么變化,從而了解古人怎樣不斷創新,從中汲取營養和啟迪。
例如過去過小年(臘月二十三或二十四)要祭灶,先送灶王爺上天,過幾天又把他接下來,繼續呆在灶間里貼有一小副對聯“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的神龕里。我小時候多次參加這樣的活動,至今記憶猶新,因為祭品特別簡單:沒有飯菜,也不燒香,只有一碟干草,上面撒幾粒豆子,下面壓一張用紙剪成的馬;另外一碟是幾小塊麥芽糖。大人解釋說,紙馬和干草是灶王爺的坐騎和它的食料,麥芽糖給灶王爺吃,這樣他上了天以后就不好說我們家的壞話了。只須磕一個頭,我就可以吃那麥芽糖,牙也并沒有被粘住;大人們則并不磕頭,連躬也不鞠一個。敬神沒有比這送灶更簡單而有趣的了。
這一套奇怪的辦法,讀過魯迅先生的《送灶日漫筆》(后收入《華蓋集續編》)一文以后才有比較多的了解,該文開頭兩段道——
坐聽著遠遠近近的爆竹聲,知道灶君先生們都在陸續上天,向玉皇大帝講他的東家的壞話去了,但是他大概終于沒有講,否則,中國人一定比現在更要倒楣。
灶君升天的那日,街上還賣著一種糖,有柑子那么大小,在我們那里也有這東西,然而扁的,像一個厚厚的小烙餅。那就是所謂“膠牙餳”了。本意是在請灶君吃了,粘住他的牙,使他不能調嘴學舌,對玉帝說壞話。我們中國人意中的鬼神,似乎比活人要老實些,所以對鬼神要用這樣的強硬手段,而對于活人卻只好請吃飯。
原來這級別本來就比較低的灶王爺竟是這樣一位最好糊弄的神仙,難怪只給他吃這種低級的糖。按先前他的待遇并不是如此,宋人范成大《祭灶詞》云:
古傳臘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
云車風馬小流連,家有杯盤豐典祀。
豬頭爛熟雙魚鮮,豆沙甘松粉餌團。
男兒酌獻女兒避,酹酒燒錢灶君喜。
婢子斗爭君莫聞,貓犬觸穢君莫嗔。
送君醉飽登天門,杓長杓短勿復云。
乞取利市歸來分。
宋朝時他還是有好飯好菜的,人們真的希望他“上天言好事”,“乞取利市歸來分”;而后來不知道怎么一來,竟對他不抱積極的美好的希望,變成降格以求,只希望他不要說壞話——或干脆不要說話,于是就請他吃麥芽糖粘住他的牙。
從請灶君享用“豬頭爛熟雙魚鮮,豆沙甘松粉餌團”到只有“膠牙餳”,從希望“乞取利市”到但求無過,古代老百姓的要求越來越低了。這中間具體是怎么變化而來的,很值得民俗學家分析研究。我也查過一點材料,始終未得要領,只有向專家請教。
民俗學不能只限于靜態的描述,而須作動態的跟蹤和分析。現在已經不祭灶了,大家用燃氣灶,灶君已無安身之地。如今好像只是用諸如此類軟硬兼施的辦法對付上面來的檢查團,請他們上去以后多說好話,至少不說壞話——完全不說話,像吃了“膠牙餳”之灶王爺似的,顯然已不可能。
又如貼春聯,這個風俗前后也有變遷,據說這要到明朝以后才通行,更早的時候并不普及或根本沒有這回事。又如門神,起先是神荼、郁壘這兩位能夠捉惡鬼的勇士,后來則改用唐太宗手下的兩員大將:秦叔寶和尉遲敬德。用歷史的長鏡頭看,民俗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古代社會進展緩慢,節慶文化尚且與時俱進;現在社會發展很快,民俗文化生活創新的余地應當是很大的。如果完全是老一套,年輕人很可能興趣不大,而沒有他們的積極參與,節日就火不起來,單是幾個懷舊的老年人忙著過節,那還有什么大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