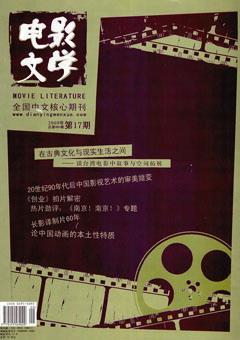在古典文化與現實生活之間
馬小青
[摘要]賴聲川的《暗戀桃花源》和陳國富的《我的美麗與哀愁》,代表了上個世紀90年代臺灣電影創作的一個流向。在這兩部作品中,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在中國經典文學中尋找自己創作的靈感,在劇作結構上也部形成了別具一格的敘事構架;同時形成了影像在視覺空間上的拓展,而這種拓展是基于將中國的古典文化精粹,形象地展現在銀幕上,與當代的社會生活的對比和交叉,在絢麗華彩中有效地傳達了創作者對生活的觀察和對哲理性的思考。由此而生發到電影敘事時空的一次實驗。
[關鍵詞]古典;現實;實驗;唯美
20世紀90年代的臺灣電影,經過80年代新電影運動的洗禮,一些新銳導演在渴望獲得突破的同時,并未將以前的歷史當成包袱,而是客觀地將個人的從業經歷背景,如舞臺劇、電視劇編導、廣告攝影、影評人等藝術經驗,投射到隨后的電影創作上,無論在主題上,還是藝術形式上都展現了后工業社會里新人類的獨特人文氣質。他們除了在題材上傾向于對都市次文化的描述,尤為突出的是在敘事中將中國的古典文化與超現實主義、極致寫實主義等手法結合起來,為自己的影片涂上了濃重的作者色彩。
賴聲川的《暗戀桃花源》和陳國富的《我的美麗與哀愁》等實驗性的作品代表了20世紀90年代臺灣電影創作的一個流向。在這兩部作品中,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在中國經典文學中尋找自己創作的靈感,在劇作結構上也都形成了別具一格的敘事構架,同時形成了影像在視覺空間上的拓展,而這種拓展是基于將中國的古典文化精粹,形象地展現在銀幕上,與當代的社會生活的對比和交叉,在絢麗華彩中有效地傳達了創作者對生活的觀察和對哲理性的思考。由此而生發到電影敘事時空的一次實驗。
“一個講故事的人即是一個生活詩人,一個藝術家,將日常生活、內心生活和外在生活、夢想和現實轉化為一首濤,一首以事件而不是以語言為韻律的詩。長達兩個小時的比喻,告訴觀眾:生活就是這樣!”對電影敘事的理解,羅伯特·麥基認為,電影敘事的創作是有其原理和規則的,但是,發掘生活的真理,對實際發生的事件進行思考才是電影劇作的本質。這一點我們在《暗戀桃花源》和《我的美麗與哀愁》這兩部影片中恰好得到印證。
一、賴聲川的“桃花源”
公演在即,《暗戀》和《桃花源》兩出話劇意外地在一個劇場里彩排。電影一開始就是《暗戀》劇組張望著,打量著進入到了故事的舞臺。青年時代的江濱柳和云之凡相互傾心。一起感嘆人生的戲劇性和對時局的困惑,并相約日后。導演的介入讓觀眾知道了這無非是電影里面的話劇。
出身于戲劇,并有著豐富舞臺經驗的導演賴聲川在整部影片中有效地利用了兩出戲相互爭場地這一意外的事件,自然為影片提供了一個共用的敘事空間,讓兩出戲之間有了對話和交融的機會。事實上,影片涉及了三段敘事體。首先,“暗戀”中江濱柳和云之凡由暗戀而離散,最后再次重逢恨晚的故事。這一段敘事的時間跨度從20世紀4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前后有30多年的時間跨度,而敘事的內容則涉及了大陸、臺灣、個人的一生的悲歡和命運。“暗戀”用的是正劇的手法來表現。第二個敘事構架是沒有明確的時間跨度,卻有著更為豐富的空問想象“桃花源”的故事中,老陶因為老婆春花的偷情而去尋找桃花源,卻在桃花源里而見到春花與情人袁老板是一對美滿夫妻,離開桃花源回家后,是春花與袁老板結婚生了,卻并不美滿的生活。在這個故事的板塊里通過夸張的動作和語言,延用喜劇的形式表現了一個悲哀的故事;第三敘事線索是較為隱蔽的一條線:一個不時地會出現在舞臺上呼喊、尋找“劉子驥”的女子。劉子驥的名字是《桃花源記》中尋桃花源未果的南陽人。在這里沿用這個名字,作為一種指代,我們從這女子的呼喊中發現,這又是一個不夠圓滿的故事。那么她與劉子驥是什么關系?她會不會是又一個心中存有桃花源,追尋桃花源的人呢?故事到此,似乎不再繼續。
這部影片的敘事空間和時間的巨大差異看起來互相不搭界,如何能夠將這些融為一體,影片成功之處不僅僅在于導演所采用的“互爭場地”的契機,更是在于導演在劇中所蘊涵的主題意旨,才最終將多個故事融合為一部真正的電影。在劇作結構上,這是一部反結構或者說是反情節的影片。所謂的反情節就是在經典的電影敘事中,混合了多種互動模式的背景,其中的故事章節不連貫地從一個“現實”跳到另一個“現實”,借以營造出荒誕的感覺,《暗》片的編導將兩個故事問進行隨意的片斷組合,起初由《暗戀》來開始交代一對相愛的人的故事通過他們的對話,我們了解了《暗戀》故事的起因,并為他們今后的命運沒置懸念。重排的過程中,《桃花源》的劇組進入畫而,并由此發生了爭吵。開始了《桃花源》“三角關系”的片斷,,在這里,生活被描述為處處的不如意,三個人在一起也充滿了吵鬧和不休的爭執。充滿抽象的舞臺布景展示絕望的老陶逆流而上,被打斷的排練被迫進入到《暗戀》“臺北醫院”的故事場景。“桃花源”進入到了敘事,老陶所見到的酷似春花和袁老板的阿個人,實際上也暗示這也是春花和袁老板的理想世界,“時間愉悅地過去了……”但是,現實又發生矛盾。舞臺被分成了兩半,精彩的是兩組演員的臺詞看似相交混亂,卻址這兩個故事融合成了一個故事,因而這一叨也具有了普遍的意義。場地重新交回給了《桃花源》,此時在武陵中對生活充滿抱怨的是春花和袁老板。精神受到洗滌的老陶,此時此地還是打不開酒瓶的蓋子。再想逆流而上的老陶的故事被落下的大幕打斷。在大幕里面,《暗戀》的最后一場“相見”還在排演。江濱柳的感慨:“在上海見面了,卻在臺北沒能在一起”暗含著對人生的無奈和失意。各個片斷之間能夠彼此呼應,看似隨意的碰撞,卻推動劇情的進展,并且直接指向了影片所要表達的主旨。正如導演所淪:
“《暗戀桃花源》的成功,在于它滿足了臺灣人民潛意識的某種愿望:臺灣實在太亂了,這出戲便是在混亂與干擾當中,鉆出了一個秩序來,讓完全不搭調的東西放到一起,看久了,也就搭調了。”
將現實文本與理想國“桃花源”文本的相融,創造了多重的敘事和影像的空間。這不僅豐富了影片的內涵,也使影像呈現出一抹詩意而多樣的色彩。攝影機故意的間離效果,又超出原舞臺劇原先所設定的三個空間:桃花源、上海一臺北、桃花源之外尋找的女子活動空間,還有本身導演介入的創作空間,而又多出了電影本身的一個空間。其實,雖然有幾個故事內容和空間,而事實上,這原本就是一出戲。陶淵明的名篇《桃花源記》是中國文人心中千百年來精神上永遠的“烏托邦”,也是映射出“美好生活”的敘事母題。將這一母題再次在20世紀后期做了一次尋找,電影對桃花源進行了一番絕妙的諷喻。理想永遠是理想,它的迷人之處在于它的不可實現。到底存在真正永恒的愛情嗎?《暗戀桃花源》的最終答案是否定的。
二、愈“美麗”愈“哀愁”
這里有兩個世界,一個是充滿了生活各種壓力之下的現實的世界,而另一個則是郁郁的唯美的古裝的死而復生
的愛情世界。處于青春期的莉莉對性只是好奇,而現實的升學壓力和與母親的隔閡使她覺得現實的世界了無生趣,而漸漸莫名地在昏睡中進入到一個古代的情境,在那里她能夠找到愛的溫情。在這一段落里的夢境,暗合了湯顯祖《牡丹亭》的“驚夢”和“寫真”的兩個段落。一次在街上意外發現的巨幅廣告上的人像正是夢中的書生。故事到這里成了敘事的第一段落的戲眼,為柳玉梅的出現做好了鋪墊。恰是心中的茫然才真正導致了莉莉的死亡。第一段落結束了,第二段落在經典劇作中通常被認為是故事的發展階段,而這里故事卻發展到了另外一個女主人公——柳玉梅的身上。柳玉梅所受到的生活和情感的困惑通過影像又傳達出都市生活里的另一個層面的情感困擾:小歌星柳玉梅與自己的音樂制片人同居,而此時,兩人的感情似乎隱藏著危機。意外搬入莉莉生前生活過的房屋,提供給她和莉莉交流的機會,她開始進入到了莉莉一樣的夢境中,這個夢境暗合了《牡丹亭》的“玩真”和“冥誓”的兩個段落。柳玉梅似乎與莉莉合二為一了。這看似是一個兩個女人今古并存的故事,可是,導演在影片中蘊涵的是每個人心中都有的情感問題。莉莉摔死以后所出現的鬼魂實際上是有著每個人心理的依據的。
這部影片所呈現出的是一種基于經典戲劇結構上的小情節影片,故事的真正沖突主要在于人物的內在沖突,莉莉和柳玉梅也許與家庭、社會和環境具有強烈的外在沖突,但是推動故事的力量是來自于她們自己內心深處對愛與溫情的渴望。《牡丹亭》在影片中作為夢境的設置,一方面將兩個故事聯結成一體,一方面也是人物的情感的外化表現渠道,因而也使影片在影像上多出一個古代的空間,影像也由此變得更為豐富和絢麗多彩,增加了影片的可看性。
《牡丹亭》原本就代表了中國傳統敘事母題:充滿奇情的男女愛戀,并為追求純粹的愛死而復生的故事。對應著這一母題,《我的美麗與哀愁》設汁了一個奇情的故事情節,現實的愛戀是帶有瑕疵的,前世的愛戀是純美的。《我的美麗與哀愁》在表現夢境的場景中,嚴格遵照《牡丹亭》的四個段落,不僅形成了夢境中的敘事張力,而且在影像中將中國古典亭臺樓閣的美景糅入才子佳人的幽怨凄清的情緒當中,帶給觀眾以視覺和情緒的美感,在與現實的對比中,使得人們更易于認同影片所表現的當下現代人情感的失落。
三、唯美的影像和現實的情懷
無獨有偶,這兩部影片都是20世紀90年代前期在臺灣出現的由古裝和時裝交織而成的復雜的作品,蘊涵了豐富的時代意義和人性中共同的夢想和無奈。有趣的是這兩部影片對經典結構的反叛又都是借鑒了中國古典傳統文學的經典文本。將現代社會的生活和經典中國文化形成互本文,在影片中彼此參照,彼此對應。影片中,經典文本不僅在敘事上更富于層次,甚至成為推動敘事的動因。例如,《我的美麗與哀愁》中莉莉的行為的真正推動力都在于她夢境中的敘事段落所帶給她的心理沖擊甚至心理依賴,最終導致她的死亡。與“冥誓”相對應的現實生活的表現就是柳玉梅和莉莉融為一體。《暗戀桃花源》看似三個敘事體,彼此不構成敘事的推動力,而觀眾在欣賞的過程中,逐步被帶入到創作者所期望的哲理性的思考,將敘事的推動力變為思想表達。當前,中國電影的時空設計,經歷了“第五代”的影像造型的洗禮,再經歷好萊塢大片的沖擊,高科技的虛擬技術的沖擊,難道別無他路了嗎?其實,臺灣的《暗戀桃花源》和《我的美麗與哀愁》就提供了一個時空設計的優秀范例。中國古典文學進入敘事,也就提供了一種另類空間的可能性。而在這個另類空問的造型和視覺圖譜與現實空間的視覺圖譜交叉,調節了觀眾對單一視覺形象的厭煩心理。在視覺不斷的變換中,觀眾也被不停地調動起觀賞的興趣,敘事的跳躍也不再是難以忍受的事情。《暗》片中的“桃花源”和《我》片中的“后花園”不僅使故事更有意蘊,它們所代表的美好的理想境界,對應著現實的無奈。跨度較大的故事時間,空間影像呈現的亦古亦今,帶給觀眾的是豐富而多義的視覺圖景,將不同時空的故事能夠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有效地表達了創作者的一種哲理性的思考。
雖說電影的欣賞過程是一次短暫的視覺消費,但是如何提供給觀眾豐富的視覺想象,如何啟發觀眾的思考,已經是電影發展百年以來對電影本體創作所提出來新的課題。對這兩部影片的敘事和時空的解讀,對我們今天的中國電影的創作仍然富有建設性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