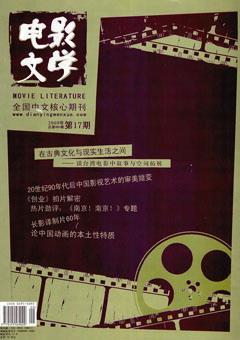兩層客體的雙重表意
張 琪
[摘要]電影《二十四城記》秉承了導演賈樟柯一貫積極的入世心態,將兩層害體,即人物個體和工廠生命體,糅合于雙重的表意,即懷舊與訴苦之中,借助這種豐滿的電影語言,完成了以工廠回憶為載體的對現時世界反向而清晰地坦誠接受和美好寄望。此外,影片在歷史縱深中挖掘被政治與時間合謀屏蔽的苦難聲音,使其內容具有人類學文獻的價值意義,帶給觀眾以邊緣化的他者之觀照。
[關鍵詞]《二十四城記》,入世,他者
電影理論家安德烈·巴贊(Andre Bazin)曾經頗帶精神分析學意味地為攝影影像進行本體論上的界定,他認為人類對影像手段的運用意在用逼真的模擬物替代外部世界,通過這種“與時間相抗衡”的方式來保存生命,并將此稱作“木乃伊情結”。對此,仿佛可以推論出兩點說法:其一,影像的核心意涵在于對現時世界強烈的“逃避傾向”;其二,紀錄片是“木乃伊情結”和“逃避傾向”的最佳形式載體。但是,就最近的電影紀錄片《二十四城記》來說,這樣的推論就顯得本末倒置。這部作品的所指承載的絕不是逃避現時、皈依歷史,相反,這部作品為的是以塵封的苦難話語、鮮為人知的口述史料來表達對現時的反向性思考,在不無批判地揭示420~軍工廠是作為國家政治技術的綜合展演體而存在的同時,落腳在對這半個世紀社會變遷的承認和對當下的大膽接受、反省與前景眺望。
影片通過對兩個層次的客體對象進行書寫而達到要旨的展現:一是與420廠直接或間接相關的人物個體(筆者主要分析影片的歷史指涉和社會意涵,并非技巧和手法,在這里將片中專業演員視作真實被訪者),二是420廠整個作為有機的生命體。對前者的記憶展現實則就是對后者的輪廓勾勒,對后者變遷的綿延關注即是對前者生命實踐的環境再現。前者的話語帶有口述史意味,它所擁有的集體性、生動性、過程性都能更貼近真實地還原時空坐標中的具體內容,420廠因此而變得鮮活;后者則帶有即時史學的影子,從420廠遷出沈陽到定位于成都,從軍工企業到轉為民用生產,從興盛繁華到賣地籌資,它從來都沒有真正地從歷史的舞臺上退場過,不斷以新的姿態被持續卷入變化的權力、經濟格局中,工廠人員因此而平添了身不由己的底層色彩。“人物”個體與“工廠”個體具有互文與整合之關聯。在這兩層客體基礎上,影片再通過懷舊和訴苦之表意,達到對現時世界的認同、憂思與希望。
一、懷舊:集體主義的派生物
集體化時代的中國,農村有公社、城市有單位。立基于傳統鄉土的農村公社制,在國家直接進入農村基層的全能時期遭遇了一股自下而上的反向制度化,因而系列的政策調整與各種肅清活動不曾停歇,而單位制所遭遇的“民間改造”要微弱得多。究其根本,還在于單位制雖然在一方面的確施以人們流動限制,但更多地是以國家的名義為人們帶來了生活的無縫式服務,這既契合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家國一體、官民一家的觀念,又契合了人們對于執政黨的信任和渴望實際好處的功利主義一面。單位中的個體成為依靠單位為中介的“國家人”,坐享制度性福利的同時,又能得到精神與道德的修養。在這個物質與精神的溫暖之“家”中,國與廠兩類集體以互相通達的形式被注入工人的心肺中,身處其中可以保障生活、習得品行、提升自我,享受“孩子王”的另類主人翁之感。
在影片中,我們可以看到有三位被訪人都或多或少地流露出了對420廠的某種相對美好的記憶,而這些記憶都是集體主義在城市派生出的單位制文化的正性留存物。首先是何錫昆,他在鏡頭面前把當年在工廠跟著師傅學做工和學做人的情景平靜道出,流露出的對師傅教導和包容的感恩式回憶,正好就是對工廠如母體般將未完成生長的個體納入其寬宏的懷抱所持有的感恩情懷。師傅教育他要珍惜別人的勞動成果,節約工具使用的成本,這幾乎被他奉為了集體化年代的基本道德標桿,而工廠正是培養道德苗頭的最佳溫室。其次是宋衛東的段落,他作為工廠辦公室副主任,是以一身精英的裝束和語態出現的。由于他在工廠這個結構內部所占據的特殊位置,他的記憶非常自然地會落腳在對舊時光里那些值得把玩的趣聞軼事上面,包括童年的打鬧與兒戲般的初戀,全能主義的工廠因為具有“小型社會”一樣的生存完備性而帶給他浪漫性情和無憂無慮。再次是“標準件”顧敏華,她落落大方地出現在鏡頭面前,毫不避諱地大談自己的私人生活與愛情經歷,并且從骨子里仍然流露出多年未變的上海女人特質,這基本上說明了曾經的工廠生活給足了她自由的空間,讓她能夠以犧牲青春來不斷尋求工作與生活、現實與夢想的理想化平衡。電影宣傳語中的“塵封在時間里的信仰、青春與熱情”,正是三位受訪者在工廠密實的屋檐下無意識演繹的。
但是,上述這些故有的美好并不是為了標榜對那個時代的膜拜與推崇。從賈樟柯以往的作品來看,包括早年地下產物的《小武》《站臺》到后來的《世界》《三峽好人》,更直接的是同為紀錄片的《東》,這些作品在意旨上給人統一的感受:對變遷之下的現時世界的不滿,不滿之余的批判,批判過后的寄望。寄望意味著坦誠現時的失敗與荒謬,勇于、敢于面對當下,善于、忠于立足當下,進而目視前方,而不是沉溺過去,演出世于逃避,得虛假之安寧。這次的《二十四城記》雖然拿回憶做文章,但仍未逃離他風塵入世的慣常哲學。如心理學家所說,懷舊是成熟的表現。有了懷舊,才標示了成長的確鑿刻度,對過去的幾分念想正是在反問:現在怎么了?以后該如何?用賈樟柯自己的話來說便是:“越是面對當代現實,就會開始對歷史越感興趣……但是我相信未來。”
二、訴苦:政治規訓的后遺癥
《二十四城記》宣傳語中的“被犧牲和毀滅的那些人和他們的生活”已經很好地表達出了電影對待人物個體的基本立場,即挖通他們被時間堵截的回憶之流,用他們的“訴苦”來營造時代的回響。所以我們看到影片在形式上是以幾個小人物的訪談為主料的,有的是在陳述過去的痛楚與辛酸(侯麗君、大麗),也有一些通過對“工廠”二字的領悟來旁敲側擊其背離人性的一面(趙剛、蘇娜)。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侯麗君,她不僅作為工廠子弟完成了上輩人的傾訴,更作為工廠人遭遇了上世紀90年代的國企下崗潮,這將工廠記憶拉入了離今天更近的現代性轉軌的激蕩中,貼合了更多受眾的認知。這些民間的苦難與認知不曾被官方和主流很好地注意到,工人的失語是由國家的在場以及強大的政治話語所規訓的結果。
1958年,420廠搬遷至成都,雖然這不是由1964初始的三線建設任務所啟動(在大麗的回憶里是因為蔣介石要反攻大陸),但它并不與三線建設的歷史內涵相左。從建國之初到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國一方面總是處在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余孽的間接火力壓迫下,朝鮮戰爭與越南戰爭中的中國都是跳板后方的終極目的;另一方面,新中國成立后的很長一段時期內,全民都處于一種由內而生的“后革命氛圍”之中,革命時期的理想主義與激情特質留存完好。在這兩方面的作用下,全民國防與狂飆猛進的雙重建
設思想貫穿始終,“三線建設”和“文化大革命”成為兩場具有代表性的運動。420廠的搬遷準確地映射出這段時期的社會總體狀態:國家一方面如奇跡般無所不包地管理數以億計的個體,龐大的個體群也以忠誠的信仰來回應國家的各種政治指示,使得社會運行如同一場接一場的“儀式”一般,權力結構與意義系統都在上下“串通”的表演中獲得建構。¨所以應該說,影片中那些人物個體的苦難回憶實際上是國家與民眾互認儀式的結果,這在“大麗”的訪談段落表現得最為明顯。她的孩子在工廠人員大遷移的過程中丟失實則是非人格化的紀律與大麗夫婦二人主動摒棄私人利益的雙重后果。當然,這些并不意味著在那段時期里,420廠的個體們對于自身所承受的苦難完全沒有體悟,而是在那樣的集體情境中,反抗話語只能以隱藏文本的形式被迫掩藏,并且也不可避免地會以“弱者的武器”之形反饋在日常的工作中。也就是說不滿與怨恨并不是不存在,而是一方面自我壓制,使得正面形象象征性地符合上層期望,一方面又以怠工、搭便車或者順手牽羊的方法反抗著政治與工業相結合的異化。
“整個造飛機的工廠是一個巨大的眼球,勞動是其中最深的部分”,電影里引用了詩人歐陽江河的這句話。這就是對420廠眾人命運最真實的寫照——工作與生活都逃不開工廠這個無所不包的體系,猶如存活在全景環視的監獄中,車間主任作為視覺監視、廣播喇叭作為音響監視、名冊登記和各類手續作為行動監視,形成一種無終止的審問、調查、裁決與懲罰的固定程序,“勞動質量”是程序的核心代碼。
三、結語
《二十四城記》是導演賈樟柯實驗精神和實驗興趣的一次井噴式的集中爆發,形式的大膽與曖昧之下,仍舊潛藏著社會敏感。這次,影片將兩層客體,即人物個體和工廠生命體,糅合于雙重的表意,即懷舊與訴苦之中,完成了突破之中的個性延續,使得其作品中一脈相承的現實主義和人本主義傾向因為堅持而越顯中立。賈樟柯的影片從來都注重寫實,對畫面的粗糙程度有一定要求,但是在《二十四城記》里,每個鏡頭都做到一絲不茍,前期的機位與后期的調試都精雕細琢;大量的運動空鏡頭更是帶給破敗的廢墟以唯美之感,這就形成了畫面形式與內容的緊張感。化解這種緊張感的出路就在于——將回憶復位于時間并服務于現時世界——,420應該屬于過去,廢墟之廢,殘壁之殘,正是新時代所欣慰見到的,重現工人的血淚在于規避血淚的再次降臨。這個意義上,廢墟是美好的象征。于是,那段看似與整部電影的主體不是很契合的農民工的靜立群像仿佛獲得了重新解釋的機會:一群由社會變遷所生產出的邊緣者被犧牲為變遷列車的軌道,碾壓過他們的鋼脊,前方應該到站了。
此外,影片以420工廠廠志(演員表演部分的依照)與人物口述這兩種敘事相結合的文本,使其擁有朝著歷史與社會靠攏的文獻價值。加上對工廠記憶中的女性部分給予比較多的書寫,更是彰顯出了人類學的特質:平等對話弱者化的、邊緣化的他者,在此觀照中釋放出廣闊的文化闡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