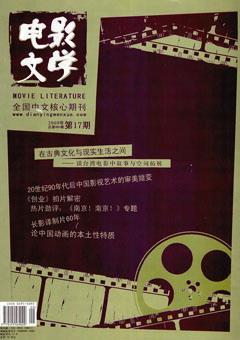《愛的流刑地》:愛與殺的日本式迷戀
徐舫州 謝 璐
[摘要]《愛的流刑地》這部日本影片,片名就直白地透射著愛的柔情與冷峻的死亡氣息,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愛是與性愛和死亡三位一體的,筆者試圖從日本文化藝術史中的情色現象、日本人的物哀意識、日本人對櫻花的獨特情感、日本人的地理危機以及弗洛伊德對生本能和死本能的闡述為切入點,通過一定剖析研究,解密該部影片中愛與殺的日本式迷戀。
[關鍵詞]《愛的流刑地》;日本;愛;死亡
愛,人類共同的美好情感。
流刑,古代將犯人流放遠地的一種刑罰。《書》云:“流宥五刑。謂不忍刑殺,宥之于遠也。”僅次于死刑。
愛的流刑地,直白地袒露著愛的柔情與冷峻的死亡氣息。
《愛的流刑地》,一部日本影片,一部詮釋愛與殺的日本影片,一部詮釋根植于大和民族內心深處的愛與殺的日本影片。
說到愛與殺,很自然地便會想到奧地利精神分析學派創始人——弗洛伊德在《超越唯樂原則》一書中提出的“生本能”和“死本能”概念。“生本能”包括人的自衛本能和性本能,最后都是指向生命的生長和增進。“死本能”指的是每個人都有一種趨向毀滅和侵略的沖動。死本能向外表現,就體現為傷害他人,而以人類戰爭的最高形式達到頂峰;死本能向內發展就表現為對自我生命的否定、自毀和自殺。生本能,是生活和生長的原則,它是愛和建設的動力;死本能,是衰退和死亡的原則,它是恨和破壞的動力。死本能多半不是表現為一種求死的欲望,而是表現為一種求殺的欲望。弗洛伊德認為,人不可抗拒要走向死亡,一切生命的目標就是死亡。簡單地說,生本能指向的是性、是愛,死本能指向的便是殺。
弗洛伊德的本能學說還只是人類20世紀的探究成果,而那種對愛與殺的迷戀,自古就能在大和民族的歷史文化生活中得到普遍印證。
日本這個國度,似乎有著強烈的關注情愛欲望的民族傳統,有著強烈的生殖崇拜和性開放意識。日本的情色文藝源遠流長。史前繩紋末期的大量女性形象的土偶就十分夸張與突出人物的生殖器官;奈良時代男女可以自由戀愛,男人可以與他人之妻戀愛,而身為人妻的女人也可以與其他男人戀愛;
《源氏物語》,在日本的地位相當《紅樓夢》之于中國,其間充滿男女之間的花柳韻事,不倫的愛欲生活更是隨處可見;江戶時期的井原西鶴,以反映町人享樂思想的“好色物”著名,描寫男女性愛肉欲是其主題,例如《好色一代男》《好色一代女》《好色五人女》等。情色,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最代表日本傳統審美文化的浮世繪中也有情色畫,精致的茶道傳統中也有藝妓的影子(雖然不同于妓女,但同樣暗示的是色情)。即便是現代,指向色情的AV女優和“援助交際”乃是日本語匯中的特有名詞。
在電影領域,日本是世界情色電影的出口大國,二戰后的60-80年代是日本情色電影的繁榮期,日活公司成立,帶動了情色電影的潮流,拍攝R級、P級浪漫性愛黃色電影的“日活路線”被大眾普遍認可,一度創作出世界頂級的情色作品,培養了日本四大情色大師——寺山修司、神代辰己、若松孝二、大島渚。
性愛這個話題,早就已經滲透進日本生活的各個角落,早就融合進日本人民骨髓的每一個分子。《愛的流刑地》中對男女主人公視覺化的性愛描寫尤為突出,有一種唯美化、唯情化,甚至于是彌漫著歌頌色彩,蕩氣回腸,令觀者也不免為他們的融合而動容。這種融合更是讓女主人公冬香心醉神迷,她稱自己是“飛舞到天上的女人”。酒吧女老板說:“女人分兩種,知道這個的和不知道的。”“男人也分兩種,會引導的和不會引導的。”顯然,冬香屬于前者,男主人公村尾菊治也屬于前者,他們是幸福的。
導演在用心琢刻著這一段段愛的影像,暖暖的色調、仿佛頌歌般的哼唱、細膩的鏡頭,把人物在情愛呢哺中的各種情感體驗傳達得活色生香。還有那玫瑰色的晨日、絢爛的煙花,以及美到奢靡的漫漫櫻花。
櫻花,盛開時燦爛華美,然而看似柔弱的嬌花卻有著剛烈的性格,不會等到枯萎而是在櫻滿枝頭時華麗飄落,幾乎一夜散盡,落英漫天。日本人把櫻花看作大和民族的象征,可以說是他們的精神寄托,如滿櫻一般絢爛飄落的死亡方式正是他們所深深崇尚的。在日本的和歌集《萬葉集》中,“櫻”用來比喻為情所困、最后選擇死亡的美麗少女形象。可見,在日本的文化里,“櫻花”很早就與死亡建立了某種聯系。日本現代著名女詩人茨木則子有一首詩,名字就叫《櫻花》,在詩的結尾部分有這樣幾句話:“信步在繽紛的落英下/瞬間/我有如名僧頓悟/惟有死亡才是常態/生不過是可憐的海市蜃樓”。
煙花,又何不如此呢?綻放時絢爛、旖旎,剎那間也就灰飛煙滅,而燦爛的死去不能不說恰好符合日本人的生死理想。他們對于生命常常會有這樣一種態度——選擇年華正燦爛之時死去,將時間永遠滯于最美好的瞬間。
物哀是日本的一種傳統審美觀念,有感慨、感動、哀傷、壯美的含義。《源氏物語》研究者認為,《源氏物語》并非以道德的眼光看待和描寫男女主人公的戀情,而是意欲以此引發讀者的興嘆、感動、產生“物哀”之情。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說過:“日語的美是同悲哀相通的。”對日本文化有深入研究的魯斯·本尼迪克認為,當我們在品味日本的文學和電影時,首先吸引我們的就是作品中透露出來的強烈自殺情結。當然,這種自殺情結的體現并不僅局限于“自殺”這一具體行為,它更流露于日本文藝作品在敘事中體現出的對自殺的贊頌和對死亡的敬意。畫家古賀春江有句名言:
“再也沒有比死更高的藝術,死就是生。”作家村上春樹的作品同樣不乏死亡,在《挪威森林》中有這樣一句話,“死不是生的對立面,而是作為生的一部分永存。”
然而在基督教文明的西方國家中,自殺被認為是懦夫的表現。《圣經》中,自殺的人是不能上天堂的。日本人則將自殺者如英雄般敬仰,對死亡毫無畏退,將死亡看得平淡異常,這種民族性格與國家所處的地理環境不無關系:日本是個四面環海的島國,又處于環太平洋火山帶,擁有全球十分之一的火山,這使得島國時時處于臺風、海嘯、地震的淫威之下,令人民賴以生存的漁業、種植業始終面臨著大自然的威脅。另外,頻繁的戰爭也讓死亡時刻籠罩在日本人的生活中。這些,都使日本人認為一切美好虛浮易逝,難于把握,惟有死亡才是永恒。他們一方面不舍美好事物,一方面又對死亡瘋狂迷戀,從而形成通過永恒的死亡留住易逝美好的獨特生死觀。
《愛的流刑地》將愛推到了頂點,遂將死推到了高峰。
電影的小說原作者渡邊淳一語出驚人,他認為真正的純愛就是“不倫之戀”。他坦言,現在日本電視劇中上演的各種所謂“純愛”根本就不是完整的愛。真正的愛絕對需要靈與肉的完全統一。向來被世俗視為不倫之戀的婚外戀情正因為是沒有未來的苦戀,才使得雙方飽受靈欲的痛苦折磨,徘徊在情感與理智的邊緣,進退兩難。這種苦戀沒有婚姻帶來的太深重的權利和義務,一切只是因為彼此相愛,碰巧對方又已經結婚罷了,這種被社會所不容的苦戀才是真正的成人純愛。正是這樣的一種“純愛”,令冬
香想要死一幸福得想死。
從男女主人公的相識、相愛、相別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出冬香選擇死亡的情感堆積。她說她“幸福得連死都愿意”,并且“隨時都能死”。在冬香決定死去的那一晚,燦爛的煙花、靜美的和服以及精心裝扮的面容,讓這一晚看起來是如此的神圣,神圣得就像一場儀式,冬香選擇死亡的儀式,亦是冬香升華自我人性的儀式。
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愛是與性和死三者一體的。正如日本當代著名的思想家今道友信所寫,愛在某種意義上與性和死相關。亦如法國民謠中所唱:
“愛就是一點一點地死去。”真正的愛就是將自己犧牲,達到自己死的彼岸。
從弗洛伊德的本能學說角度,同樣能夠解釋他們之間的關系,那就是生本能和死本能的相互轉換。人在極度開心時會哭出來、極度幸福時會希望死去,極度絕望時會煥發出強有力的生的力量。生本能和死本能的轉換構成了人的生命過程的全部內容。當人們面對美麗的景色心中格外欣悅之時,都可能會有希望個體消失、消融在景色中的沖動。人們內心中愛的本能達到一定強度值會希望用死亡去定格它,就像用照相機定格一樣,愛本能就是人的生本能最重要的表現,這里用照相機的定格來比喻很是形象。只有死亡,才能做到一生一次,所以心靈純凈又單一的人,想用這種做法成就自己的惟一,冬香就是這樣的一個人。這個總是無比堅定地說“幸福得連死都愿意”的女子,用自己的死鑄造了一座“愛的墓碑”,以此來表達她對愛的篤定,來定格他們的愛。她心甘情愿地用死成為男子的惟一,不想給任何人。泰戈爾說:“生如夏花之燦爛,死如秋葉之靜美。”在他的筆下,死亡和生存一樣美麗,將死亡賦予了許多美麗的令人向往的色彩。
日本人將性和死亡看作人生的至高境界。1969年《情死天網島》的治兵衛和小春,雙雙削去頭發后殉情。1978年《愛的亡靈》中豐次和阿石被處極刑。1983年《槽山節考》中母親面對即將到來的“朝山”的坦然態度。1986年《臺風俱樂部》恭一縱身跳下窗予,希望他的死能讓大家活下去。1997年,《花火》西佳敬與妻子在海邊的兩聲槍響。同樣是渡邊淳一的《失樂園》飲罷毒酒,纏綿死去……這種種的死,都不只是死本身。日本人對待它有更高級別的態度,是高于一切的崇高,坦然地面對死亡,甚至于欣賞死亡是日本民族的一個特性。
冬香對死亡也是向往的。外表純鈍的她,早在18歲讀過菊治的《愛的墓碑》后,就將愛的墓碑奠基于心底,她羨慕里面那個嬌艷、自由有個性的少女并一心想成為那樣的女子。似乎家庭生活牢牢禁錮了她的這一個性,她甚至不肯寫丈夫的姓(在日本,女子出嫁后要隨丈夫的姓氏)。菊治的女兒高子也深諳這部小說的魅力,她問父親:“是成為預期的好孩子,還是顯露真正的自己,讓人認為是壞孩子?”冬香的死同樣表明她也在追求這種個性中的自我。那個女監察官不也羨慕冬香嗎?她說她也想被掐死,但是她沒有勇氣去爭取她的自我,甚至刻意回避遮掩。《愛的流刑地》通過主人公的婚外戀情,引發了一種前面提到的“物哀”之隋,讓觀者內心超越倫理的束縛,得到美的升華,將人世的情欲和對死亡的崇敬升華為審美對象。
日本,以它獨有的悲劇氣質,上演著一個個愛與殺的故事。或許這愛,與這殺都是一回事。既然生命無常,那么讓死亡永遠將愛定格,是不是也是對愛的珍重呢?而這種對愛與殺的迷戀,或許也正是日本人的智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