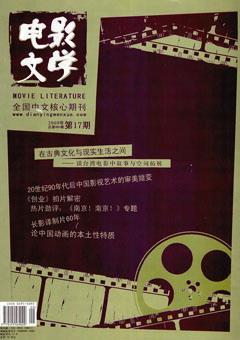民族魂的祭奠
孫大志
[摘要]《血色湘西》雖以抗日斗爭為題材,但它不重在表現抗戰過程,而重在探究抗戰過程所顯示出的愛國主義精神的歷史淵源,即民族魂。《血色湘西》的作者,就是想用原始意象說話,以喚醒我們身上所有的仁慈力量,去度過漫漫的長夜。《血色湘西》不是一首抗戰精神的頌歌,而是一個祭壇,民族魂的祭壇!
[關鍵詞]《血色湘西》;原型;民族魂
湖南電視臺攝制的34集電視連續劇《血色湘西》,是近幾年來難得的優秀劇作。作品以抗戰為背景,以雪峰山大會戰為聚焦點,深刻展現了湘西人民忘我的民族精神。為了保衛自己的家鄉,他們義無反顧,浴血奮戰,直到流盡最后一滴血。很明顯,這是一部反映抗日斗爭生活的作品,歌頌的自然是愛國主義。但是,這部作品不像以往抗戰題材作品那樣,注重抗戰過程的渲染,諸如發動群眾、轉變落后、克服艱險、至死不渝,反映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頑強斗爭的愛國主義精神,而是注重開掘主題深意,探究愛國主義的根源和那種民族意識的原型,以揭示那個民族不可征服的歷史淵源。正因為如此,作品沒有更多表現抗戰過程,而是大量展示民俗,如“祭屈原”“賽龍舟”“蒙童開筆”“天坑賭命”“男女對歌”“哭嫁”“墜天坑”……通過這些民俗生活,集中表現了湘西質樸淳厚、禮義誠信的民風;同時,也極為鮮明地刻畫了湘西人的驍勇蠻悍、矢志不渝的性格特征。
作品主線沖突是竿子營和排幫的沖突。竿子營是明清建制,竿子營的竿民平時為民戰時為兵。以麻溪鋪鎮為中心所屬有九弓十七寨,地處雪峰山中部,與外界基本隔絕,是古代楚地。這里的人剛毅尚武,崇拜英雄,因很少受外界影響,故兩千年來一直受著屈原愛國精神的滋養。在他們的心里,屈原是楚之魂,每年端午是他們最盛大的節日,必祭屈原為之招魂。“大夫大夫,楚之魂兮;大夫大夫,魂歸來兮……”儺公高亢蒼涼的招魂歌聲,震撼著每個人的靈魂,鑄就著一個集體的、熱戀本土的民族情結。所以,在麻溪鋪不僅背靠群山有屈子臺和巨大的屈原雕像,而且在供祖圣案上還有戚大帥、葛大帥的神位。明朝抗倭名將戚繼光部下曾有八百名竿兵,為捍衛疆土,驅除倭寇,英勇善戰,所攻必克;前清總兵葛云飛抵抗英軍入侵死守定海,部下五百竿兵均壯烈戰死。這些都是竿子營的驕傲,也是他們群體精神的體現。對于家鄉故土,他們有著極其深厚的熱戀情結。另外,這里的人都非常重義,有難必幫,有仇必報,絕不含糊。所以如此,是他們長期接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結果。儒家忠孝節烈、禮義廉恥觀念,已經滲入他們的骨髓,成為他們一切行為的準則。
排幫是當地水匪,壟斷水上運輸,極為兇殘霸蠻,歷來與竿子營不和。整個作品圍繞竿子營和排幫對立,糾葛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沖突。而每個沖突的解決,幾乎都是拼殺,不是你死就是我死,不共戴天。排幫前幫主石天保,趁雷公寨竿民田大有下四川之機,踢死田大有父母并搶走其懷孕的妻子。田大有回來后,只身闖排幫砍死石天保,救出剛出生的女兒穗穗。雖然石天保多行不義該殺,但其義弟現任幫主麻大拐,在已歷16年之后仍繼續尋仇。龍十四太爺設計陷害田大有,致使田大有誤殺麻大拐。盡管麻大拐養子石三怒與田大有女兒穗穗即將拜堂成親,石三怒還是要為養父報仇逼死了田大有。在愛情與復仇之間,石三怒選擇了后者,原因就是為了一個“義”字。麻大拐是被誤殺,其情可憫,況且田大有是石三怒岳父,恩怨本可化解。可父仇不報是謂不義,只是石三怒內心也充滿矛盾,難以下手又難以放脫。田大有是竿子營公認的英雄,為給石三怒一個了斷,眉頭不曾皺一下,開槍自殺。田大有也是為了一個“義”字。其實,他們為之付出寶貴生命而爭得來的這個“義”,不是民族大義,和戚大帥、葛大帥部下竿民的義舉相比,不可同日而語,完全是爭個人意氣的愚義,毫無價值。
這里不難看出,湘西人的愚昧與他們的傳統有關,因為傳統深厚,愚昧守舊,所以當清朝皇帝最后免除竿子營當兵義務的時候,這塊土地就成了與世隔絕的封閉王國。龍德霖雖為麻溪鋪鎮長,但鄉民還是習慣于稱他十四太爺,在竿子營鄉民的心目中,他仍是前清傳下來的第十四代竿子營守備。
抗日戰爭已進入決戰階段,長沙會戰后,日軍逼近雪峰山。這里還在大慶端午節,祭屈子、賽龍舟、拜儺公、對山歌一如既往,似乎國家危難民族存亡與這里全然無關。甚至共產黨員童蓮帶領商隊運送抗戰物資,請龍十四太爺為她們向排幫借路,都遭到拒絕,并斷言日本人不會到這鳥不拉屎的地方來。新86師奉命在麻溪鋪祖墳山建芷江機場導航雷達站,為保護雷達站童蓮請求龍十四太爺重組竿軍,又遭到嚴詞拒絕,聲言清朝皇帝已免除竿民當兵義務,竿子營的血老祖宗都給流完了。簡直是食古不化,愚不可及。然而就是這位老長者,在寨首大會上,看到童蓮展示給眾人日軍屠殺中國婦女兒童照片時,靈魂受到了震撼,終于同意借路。當他聽到第二個孫子護送雷達設備被日軍飛機炸死的消息時,他沉積在血液里的民族意識終于被激活了,竿軍不僅成立了,他還親自送竿兵們上了前線。日軍進了麻溪鋪,逼龍十四太爺帶路為日軍尋找雷達站,他抱起五歲的重孫虎仔,為日軍帶路進了深山,不是去雷達站,是去了天坑。日軍明白受騙還未及發作,龍十四太爺抱起虎仔讓他閉上眼睛,說阿公帶你去見老祖宗,連他祖輩生活過的熱土都不曾回眸,毅然投入天坑。在場鄉眾見狀,群情激憤,蜂擁而上,與鬼子死拼,最后全被亂槍打死。
日軍進攻祖墳山雷達站,九弓十七寨男女老少全都云集到祖墳山。祖墳山大決戰打得十分慘烈,在情勢危急的白刃戰時刻,石三怒帶領全體排幫兄弟前來助戰,并高聲大叫:
“竿子營鄉親們,排幫兄弟和你們一塊打鬼子來啦!”戰場上盡釋前嫌,各種恩怨均化為云煙,有的只是你幫我,我救你,全力以赴打鬼子。最后,雷達站保住了,大決戰勝利了。童蓮、石三怒、龍家二少爺和竿子營、排幫眾多的男女老少死于這場戰斗中,尸橫遍野,血染山河,這就是血色湘西!
從作品內容看,湘西人確實驍勇蠻悍,愚忠愚義,有時幾乎不近人情。國難當頭,他們無動于衷,似乎真的身居世外。穗穗曾與石三怒相戀,但因雙方有殺父恩怨終難結合,穗穗便決定嫁給她很敬佩的新86師師長鎖云超。就在舉行婚禮的時候,石三怒聞訊趕到現場欲搶走穗穗。當穗穗拒絕同他走時,他便和鎖云超提出三天后在棲風橋上單對單。第二天鎖云超奉命去了新墻河。三天后石三怒帶刀來棲風橋尋鎖云超決斗,可看到的卻是傷員抬回來的鎖云超尸體。鎖云超和石三怒的行為成了鮮明對比。鬼子已打到新墻河,就要到家門了,石三怒居然還要為女人去決斗。然而,也正是他,在祖墳山決戰關鍵時刻,毅然決然帶領排幫沖了上去。和龍十四太爺一樣,見鬼子前后判若兩人,毫無鋪墊,不可思議。但仔細分析就會發現,整個作品都是鋪墊。從端午祭屈子開始,到最后鄉民云集祖墳山,所表現的都是他們的集體無意識,是他們自己都不曾意識到的民族意識原型,一種遺傳性的種族記憶。這種潛藏的民族意識,像魂魄一樣,既包括遺傳因素影響,也包
括后天鑄就。湘西人從祖先那里承繼下來的不只剛毅勇武的性格,還有屈原愛國的魂,沉積在他們骨髓里的不被意識到的民族魂!
瑞士心理學家榮格在研究分析心理學與詩歌關系時發現,藝術家的創作源于“自主創作情結”。他認為,一部優秀作品的意義,不應僅僅限于作品表面所能看到的意義,倘若是這樣,也就不用分析了。如果作品具備一定象征意義,那就隱藏了藝術家的“自主創作情結”,亦即藝術家意識閾下的原始意象(原型)。因此,在探究作品真正寓意時,榮格認為應該追問的是“隱藏在藝術意象后面的,究竟是什么樣的原始意象”。
《血色湘西》在藝術意象后面,隱藏的是什么原始意象呢?是民族意識原型,是榮格指出的集體無意識。集體無意識并不是一種自在的實體,“它僅僅是一種潛能,這種潛能以特殊形式的記憶表象,從原始時代一直傳遞給我們,或者以大腦的解剖學上的結構遺傳給我們。”。湘西人自古以來就有著深厚的戀土情結,為了這塊他們賴以生存的土地,從他們原始祖先一直到明清先輩,不知付出了多少血和淚,才繁衍成今天的湘西族群。他們不像游牧部落,居無定所,隨處安家;也不似海盜民族,漂洋過海,落地生根,他們是祖祖輩輩耕耘在這塊土地上,血的歷史長河。已將這塊土地染紅,這血色的湘西已成了他們“種族記憶”(榮格語)。所以,當這塊土地真正受到侵犯的時候,這里的人就會像英雄的祖先一樣,用滿腔熱血保衛腳下的土地。
竿子營也好,排幫也好,畢竟都是湘西人,在他們身上流淌著的都是湘西祖先遺傳下來血,他們潛意識的最底層,存在著同樣的集體無意識、種族記憶、民族意識原型。這種民族意識原型,平時并不被意識到,能夠意識到的都是自覺意識的各種觀念,人們日常行為全憑各種觀念支配,觀念差異造成沖突。《血色湘西》表現的大大小小沖突,都是有意識的觀念沖突,惟有最后和日軍的決戰發自無意識,像條件反射,而且是集體無意識,集體條件反射。這不等于否定或淡化共產黨在民族抗戰中的領導作用,旨在證明民族抗戰基礎,人民大眾心中的民族意識。這部作品不是正面表現共產黨領導抗日斗爭的,而是重在表現湘西人為什么是不可征服的,擴而大之,中華民族為什么是不可征服的,就在于我們心中有著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識,一個偉大的民族魂!民族魂作為一種集體無意識,并不在我們腦袋里天天回旋,雖然我們也常常提到民族意識,但它和我們意識閾下的民族意識(原型)——民族魂,根本不是一回事。只有當能夠激活原型條件出現時,它作為一種潛能,才會進發出無窮的力量。“仿佛有誰撥動了我們很久以來未曾被人撥動的心弦,仿佛那種我們從未懷疑其存在的力量得到了釋放。”日軍屠殺中國婦女兒童,炸死龍家二少爺,就是激活龍十四太爺心理原型的條件;日軍進犯麻溪鋪,攻打祖墳山,是激活九弓十七寨全體鄉民心理原型的條件;新86師、千余名竿民幾乎全部陣亡,是激活石三怒和排幫兄弟心理原型的條件,始有祖墳山慘烈大決戰。
藝術家創作《血色湘西》,把藝術觸角伸展到了原型,這是頗有深意的。“原型的影響激動著我們,因為它喚起一種比我們自己的聲音更強的聲音。一個用原始意象說話的人,是在同時用千萬個人的聲音說話。……他把我們個人的命運轉變為人類的命運,他在我們身上喚醒所有那些仁慈的力量,正是這些力量,保證了人類能夠隨時擺脫危難,度過漫漫的長夜。”《血色湘西》的作者,就是想用原始意象說話,以喚醒我們身上所有的仁慈力量,去度過漫漫的長夜。《血色湘西》不是一首抗戰精神的頌歌,而是一個祭壇,民族魂的祭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