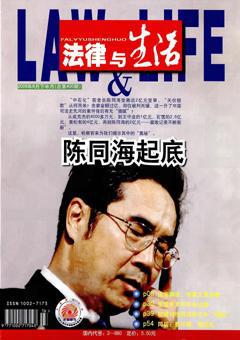心靈對話(二十)
萬秋實
提要:18歲,從青少年到成年人的轉折點,而對陳中(化名)來講,卻是從勞動教養到勞動改造的分水嶺,從15歲到17歲,他3次被捕,在監獄里的時間比在外面還長。剛滿18歲的他,再一次因盜竊站在被告席上。
[上篇]非常故事:三年的盜竊生活
2009年1月的一個下午,陳中在北京一家網吧上網聊天、打電玩,一番酣暢淋漓的網際漫游之后,他準備離開。瞥了一眼自己鄰座的女孩,還在投入地聊天,就在起身的瞬間,他臨時起意將女孩身后的包拿走了,并迅速離開網吧。當女孩發現自己的包不翼而飛時,陳中早已揚長而去。
女孩通過網吧監控器的回放,看到了陳中順手牽羊的過程,然后迅速地察看陳中用過的電腦,一個意外發現成就了兩天后戲劇性的一幕。也許是陳中走得過于匆忙,電腦上的QQ沒有關閉,女孩根據電腦上的QQ號加了陳中為好友。
兩天之后,陳中又來到這家網吧上網聊天,發現有新“好友”,并且“一見如故”,與其聊得很開心,對方也非常熱情,要求跟他視頻聊,陳中欣然答應,在陳中投入地注視著這位“好友”侃侃而談時,女孩已經從視頻圖像中認出陳中,并確定他所在的正是她印象深刻的網吧,她馬上打電話報警,陳中被當場抓獲,而這一天正是陳中18歲的生日。
出生于河南農村的陳中,小學五年級就輟學在家,父母帶姐姐常年在外地打工,他與奶奶在家務農,平靜、簡單的生活因一次探親徹底打破。
2006年春節,剛滿15歲的陳中到上海與在那里打工的父母團聚,父親在一家工廠做技術工人,母親做清潔工,姐姐在一家民營企業打工。雖然父母、姐姐租住的房子并不大,但在陳中眼中,他們像是生活在天堂。上海的繁華讓陳中大開眼界,他在這里學會了上網,好像發現了另一個世界,每天,陳中都游走于上海的網吧和游戲廳,這讓爸爸非常惱火,經常責罵、數落他,并不再給他零用錢。陳中想在上海找份工作自食其力,但找了兩個多月,沒有用工單位錄用他,理由是他未成年。
沒有“經濟來源”的陳中只好回到河南老家。此時,這個寧靜的山村,在陳中看來落后而沉悶,他經常到縣城上網、逛街。一個下午,他路過一個小商店,見里面沒人,就走進去將錢盒里的幾塊錢拿走,“當時我實在忍不住”。
“奶奶不給我零用錢,她沒錢,我爸也不給我錢,我才那樣做!”在陳中看來這是一個充分的理由,沒有什么負疚感和恐懼感,致使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盜竊。
2006年,陳中因盜竊兩次被拘留,2007年又因盜竊被勞動教養一年。2008年9月剛剛被釋放的陳中,又在一家商店,趁無人之機,將店內抽屜里的皮包拿走,包內現金一千余元。用這一“大”筆錢,陳中給奶奶買了藥,還為奶奶“辦了大壽”。他告訴奶奶,錢是他給人家干活攢下來的,奶奶沒再追問。不久,陳中只身來到北京。
在北京,陳中找到了一份在住宅小區當保安的工作,包吃住,但要工作一段時間后才能拿到工資。“我往上海打電話,想要錢,但我爸媽和姐姐都不給我。”在手頭拮據的時候,陳中故技重施,在菜市場,他趁人不備,將攤主的錢盒拿走,內有現金二百余元。陳中偷錢主要用來上網,陳中很喜歡上網,在網絡的世界里,他交到很多朋友,網絡游戲也給他帶來快樂和自信,如今,這份癡迷讓他付出了代價。
[中篇]成長經歷:沒有家庭溫暖的童年
在我見到陳中之前,北京市石景山區人民法院的李靖法官向我介紹說:“一般的孩子都愿意讓父母來探望,但陳中沒有這樣的愿望。對于未成年犯罪,法律規定,只要家長積極退賠,可以從輕處罰。所以我希望能通過電話聯系陳中的父母,請他們來北京。但陳中對我說‘法官,你別打了,我爸媽肯定不聽你說完就把電話掛了,他們不會管我的。”
是怎樣的成長經歷造就了這樣的親子關系?我希望在陳中的交談中更多地了解這個家庭。
“我長這么大,他們就沒撫養過我,就看我姐看得多。”陳中有一個比自己大4歲的姐姐,在陳中不到1歲的時候,爸爸媽媽帶著姐姐一起去河北做生意,把陳中留給奶奶照看,在陳中6歲的時候,他們又回到河南老家蓋新房,在這一家五口共同生活的不長的幾年里,在陳中的印象中都是痛苦的回憶。
那一年陳中上小學,由于在班里年齡較小,習慣也不好,學習成績不太理想,老師經常會向家長告狀,每當這時,爸爸都會暴打陳中。沉默了一會兒,陳中回憶道:“那時我上小學一年級……”又停頓了很長時間,他繼續說道:“想起那件事,我就很難受!”陳中的聲音有些哽咽:“小學一年級期末考試,學校讓我們準備兩支鉛筆,我就管我爸要錢,他就打了我,打得特別重,飯都沒讓我吃。”我很不解地問:“你要買鉛筆,他就打你,為什么呢?”陳中滿臉迷惑地說:“我也不知道!就因為我向他要錢,他就打我!”我又問他:“他是沒錢嗎?”他很急地回答:“他有錢,他有的是錢,他不往出拿,連我奶奶他都不給。”
在陳中看來,童年的經歷很痛苦,在學校沒有好朋友,“下課時別的同學都在校園里玩兒,我就一個人在教室里呆著”,而回到家里又經常被爸爸打:“他看我什么有一點兒做不好,就踢我幾腳,打我兩下。”陳中覺得唯一疼愛他的人就是奶奶。
“現在奶奶知道你的情況嗎?”
“我不清楚,如果我奶奶知道了,心里會很難受的。”陳中幾乎要流出眼淚,“那你猜想爸爸知道了會怎么說?”陳中的聲音馬上變得很冷漠:“抓就抓了唄,咱也不管。”稍停頓了一會,陳中接著說:“我和他沒有任何關系了,我出來的時候就跟他說了,我沒有你,你也沒有我,我跟我媽媽也是這么說的。”陳中看起來對父母沒有一點兒感情。“我心里很明白他們倆,就是跟沒我差不多。”我追問:“有你姐姐嗎?”他幾乎不假思索地說:“有!”緊接著又補充道:“他們和我姐挺不錯的,從小到大,他們三個過他們三個的,我過我的!”陳中有些氣憤又有些無奈地說:“說白了,他們兩個心里根本就沒有我這個兒子。”
我看到陳中眼中的痛苦和失望,他繼續說:“在我勞動教養時,生病了,需要錢治病。警官通知他們來看我,他們特勉強地來了,走時都不肯給錢,還是勞教的警官追出去才要來100元。”陳中邊說邊哭。“所以你不想讓他們來北京看你!”我追問。陳中平靜了一下,說道:“我心里很清楚他們也不會來,我也不想看到他們!”我問他:“什么時候會想見到他們?如果有一天,你成功了你希望他們知道嗎?”他快速而堅定地回答:“不想!”
[下篇]專家剖析:陳中的盜竊心理
在一個孩子的成長過程中,即便是行為上最中規中矩的孩子也曾有過“偷竊”的行為,孩子這樣的做的原因很多,舉例子說:覺得不公平——當孩子覺得同學或朋友傷害了自己,會通過偷對方心愛的東西進行報復;驗證他人的反映——偷一個玩伴兒的東西,想看看他沒有它時的舉動,或者將幼兒園的東西帶回家,看看父母、老師會有怎樣的態度;試圖證明自己的膽量——偷鄰居家花園里的菜,只是想證明他不怕那位總是嚇唬他的叔叔;得到更多的注意——為了能夠得到忙碌的父母的注意,孩子可能會將父母的手表、首飾藏起來,因為這樣就可以強迫他們與自己交流,即使這種交流是負面的。但陳中偷竊行為原因屬于另一種:他只是想逃避難堪的境況——與其向父親討要,還不如自己冒險去偷。
處在學齡期的孩子,無論是因為怎樣的原因偷竊,如果家長處理得恰當,用坦白的、尊重的、充滿愛的方式與孩子溝通,對事不對人,就可以幫助其在青春期之前,放棄這種行為。但反之,家長過分嚴厲地指責、懲罰孩子,則有可能對孩子的情感和自我形象造成傷害,從而使這種偷竊行為升級、成癮,甚至發展成盜竊犯罪。
陳中就是如此,毫無疑問,陳中在第一次偷竊的時候就很清楚地知道這樣做是錯的,他希望能得到父母的原諒和接納,甚至在潛意識里,渴望父母可以因此改變對自己的態度,不要在經濟上對自己如此苛刻。但是父母給他的反饋是——對這個兒子徹底的失望,這致使他放棄了試著變好的努力,“我沒辦法,我只能偷”。
每個孩子在成長過程中都會犯錯,而父母的教導方式和家庭關系,決定了他是知錯就改還是一錯再錯,這又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家庭關系與犯罪行為之間的關系,這方面的實證研究是非常多的,在各個年代都得到了“高相關”的結果。
從事犯罪行為的青少年的家庭有這樣一些特征:家人之間感情淡薄,特別是父子之間的感情淡薄;父母放任子女或采取錯誤的管教方式;很少參與子女的活動,忽視或有敵視子女的傾向;父母之間關系僵化,矛盾重重,或父母本身具有犯罪行為。
很多研究還發現,重復犯罪的青少年常常在家中既不喜歡他們的父母,也不做家務。在陳中家庭中,他與父母、姐姐之間的關系非常疏遠。陳中有非常強烈的被忽視和孤立的感覺,他覺得自己從來沒有得到父母的愛和撫養,在他看來他完全不需要這個家庭,這個家庭更不需要他。我想天下沒有哪位父母是不愛自己的孩子的,只是有時這份愛被太多的失望掩埋,被長久的冷漠遮蓋。
無論成長于怎樣的家庭,今天的陳中必須面對自己的人生,已經成人的他要學會對自己的行為負責,靠自己的智慧和能力,重新思考和開創自己的未來。他告訴我,出獄后,先找一家餐館打工,學手藝,將來自己開一家餐館……
(感謝北京市石景山區人民法院的支持)
(摘自《法律與生活》半月刊2009年8月下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