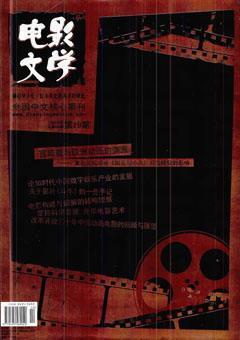專制政體的寓言
吳麗娜
摘要《國王與小鳥》糅合了安徒生童話與法國大革命歷史,以虛構的時空塔基卡迪王國為背景,為專制政體下民眾的生存狀態描繪出一幅寓言般的圖景。專制政體賦予統治者以絕對的權力,其個人素養對國計民生起著決定性的影響。一旦統治者道德敗壞且缺乏治國才能,全體民眾都將淪為犧牲品。專制政體在放縱統治者欲望的同時,還催生了民眾的奴性人格。
關鍵詞《國王與小鳥》,專制政體;奴性人格
在動畫電影中,政治題材與愛情、成長、奇遇歷險等常規題材相比可謂鳳毛麟角。它對重大政治悲劇進行深刻反思,目光聚焦在專制、極權、暴力、黨同伐異等嚴肅宏大的主題上,表現出異于童真童趣的美學追求。如,1979年的《國王與小鳥》之于法國大革命,1999年的《動物農莊》之于前蘇聯國內大清洗,2007年的《我在伊朗長大》之于基要主義掌權后的伊朗社會,2008年的《和巴什爾跳華爾茲》之于1982年貝魯特難民營大屠殺。它們或回首一段不堪的歷史,或假借一個虛擬時空從往事中發掘永恒的人性。無論哪種方式都無意避讓種種殘酷,諸如夢想與現實的斷裂,表象與真相的鴻溝,希望與絕望的交替……作為法國動畫分水嶺的《國王與小鳥》是其中最初的豐碑。它以澄澈的智慧照亮古今,專制政體中人們如何交往,如何自處,在一切關系的洪流裹挾之下未來又將去往何方?對這些問題的探索賦予這部影片厚重的文化蘊涵和發人深省的寓言意味。
一、與自己交戰的統治者
專制政體的核心是人治,以個人或某團體獨裁為特征,行政上存在極大的隨意性,統治者的個人素質顯得特別重要,其賢明與否將對國計民生產生決定性影響。片頭對夏爾十六的道德品質(賢)與治國才能(明)進行雙重否定。
夏爾十六影射法王路易十六,他是一名專制暴君,從不為自己的權力設定邊界,并強制國民絕對服從他的意志。他長著一張撲克臉,善于將自己的真實意圖藏起來,用假象麻痹別人,轉瞬卻置對方于陷阱之中,他就是這樣處理宮廷畫師的。夏爾十六利用恐怖來鞏固自己的統治,人們不因內心的歸屬感而成為他的臣民,而是懷抱僥幸以為獻上忠誠就能幸免予難。撲克臉既是他的統治手段,也暗示著他的人格分裂。他并非沒有辨別善惡的能力,內心其實很清楚把別人丟下陷阱是非正義的。之所以要用笑臉、勛章來做掩飾,只因有第三人在場。可見,夏爾十六顧忌他者的評判或者說他在意良知的衡量。這種衡量在他內心并未完全根除,只是人格陰暗面過于強勢,已將他的良知壓迫得十分虛弱了。然而,正由于這種虛弱良知的存在,他才不敢明目張膽地處置無罪的人,而是在單獨相處時用陷阱這一隱秘方式來達到目的。
內心世界的陰暗蕪雜令夏爾十六不敢正視自己,于是,他將生命沖動轉移到美化外在形象上。打靶時,他的左手總是不停變換優雅的姿勢,他愛穿高跟鞋讓自己肥碩的身體顯得挺拔,他專門建陳列室展出自己千姿百態的雕像。廣場和草坪上到處是他無生命的替身,他對自身的愛借由這些復制品無限膨脹。夏爾十六只愛他自己,但他所愛的并非真正的自我,只是他的幻象。它們或征戰沙場,為國家開疆拓土;或搭弓射箭,百發百中;或拋擲鐵餅,力大無窮……這些幻象呈現給夏爾十六一個理想中的自我。所以,當夏爾十六發現畫像與他本人一樣長著斗雞眼時,他偷偷改掉瑕疵。在病態自戀背后,是他深深的自卑。在理想自我與真實自我之間橫亙著巨大的鴻溝,這令他無法與自身和諧相處,他的內心世界充滿著激烈的沖突,就像一個時刻處在交戰中的人,一點點火星就足以讓他爆炸,代價卻是他人的生命。
夏爾十六鎖閉在自我的重重鏡像中,將與他人交流之路封堵起來。他僅僅憑借權杖、獵槍、棋盤和機器人來統治王國,鎮壓反對勢力。對人,他是不信任的。所以,當他自己的畫像從畫框中爬出,像—個真人那樣站在他面前時,他的本能反應卻是呼召警察捉拿另一個他。這從另一個側面深刻表達了夏爾十六與自身的矛盾。當真國王跌入陷阱后,假國王沿襲了他的身份和精神疾患。衛隊到來后,假國王本能地拉下帷幕,遮住自己原來的居所—那幅只剩背景的畫像。與真國王一樣,假國王也在掩飾自己的本來面目。與自我的矛盾,貫穿了這兩個異體雙生的人物。
二、專制政體催生奴性人格
夏爾十六的專制統治表現為權力由上而下得到絕對執行的社會結構。他討厭誰就將誰投進陷阱;他想捉牧羊女,所有警衛就為此疲于奔命;他要與牧羊女結婚,舉國上下就要齊聲歡騰;他喜歡自己的畫像,全體苦役就夜以繼日趕制他的肖像。夏爾十六的個人意志不僅成為國家意志,而且取代國民自身的主體性成為他們的意志。喪失主體性的塔基卡迪國民們,失去了人作為獨立的個體最寶貴的東西。
比如判斷力。面對國王的乖張,他們失去分辨能力,不以行為本身來判斷是非對錯,而以命令發出者的權威性來做評判。警衛隊長即使在僥幸生還后仍效忠國土,他難道不怕再次遭受生命威脅嗎?然而,若離開國王他將什么也不是。他重回國王身邊后貌似忘記國王曾將自己投入陷阱的事實,或許是出于對無所依傍的恐懼。因為專制政體下的人們都必須被劃入某一陣營。在迫害過自己的國王與曾經遭受自己迫害的平民之間。他選擇再次加入國王的陣營。這一方面源于人們在抉擇時對經驗的慣性依賴,另一方面則表現了他與所依附的夏爾十六精神上的同構關系。
又如差異性。王國的警衛們個個肥頭大耳、大腹便便,穿戴一律是黑色圓頂禮帽、橙色領巾、白襯衣、黑制服,當他們在國王密室里一列排開時,無法分出這一個和那一個,只能以群體為單位描繪他們。這種個體差異性的缺失和“克隆現象”不僅發生在作為國家機器的警衛身上,也出現在國王肖像的制造過程中。這里由機械液壓做動力,成百上千個一模一樣的頭像陶俑整齊排列在傳送帶上,由神情麻木的工匠們上底色,涂胡子、眼睛。一個完整工藝被切割成幾個相對獨立的制作步驟,整個過程配以練兵式的哨音。這已不是藝術創造,而純粹是工業化大生產,只不過出產的產品毫無價值。夏爾十六以此來強暴民意,制造人民熱愛國王的政治幻覺。
再如自信心。地下城居民服飾大都黑白灰色調,神情抑郁悲愁。他們處在王國社會結構底層,食不果腹,朝不保夕,過去是黑暗的,現在是陰沉的,將來是無望的。他們已無信心主動爭取應得的權利,奮爭的勇氣早已熄滅,似乎目前的處境是他們生來的宿命。他們似已習慣了順民的生活。這種逆來順受的軟弱,與警衛們為虎作倀的殘忍,是專制政體中奴性人格的兩極。
在專制政體下,奴性人格的腐毒不僅侵入到每一個利益群體,而且還必然透到原本以社會良知、以公正客觀為立身之本的新聞傳媒。在國王的婚禮上,電視主持人向公眾做“現場直播”:“在這莊嚴的時刻,宮廷大臣跪在他敬愛的國王面前,臉上帶著少有的諂媚的笑容,按照禮儀向他提問。……他們結為夫婦了,年輕王后的臉上充滿著幸福的笑容,參加婚禮的人激動萬分地高呼:國王王后陛下萬歲!”然而,實際的情況是,宮廷大臣對國王只有畏懼之情,參加婚禮的人內心如履
薄冰,年輕的王后悲痛萬分。“現場直播”的目的不在于傳達實情,而是執行國王的意志,為這段原本丑陋的婚姻蒙上華麗的面紗。媒體不再是社會的良知,也不可能實行監督的職能,而是以諂媚心態,對弱勢群體實施語言暴力,美化執政者的暴行,取代人們白行思考的權力。
三、未來的迷途
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影片中,民眾以暴力革命捍衛愛情與自由。然而,革命后的世界真如預想般美好嗎?
小鳥以唇舌煽動野獸摧毀了王國。作為革命主力軍,野獸是來自底層的力量,既可看做人格結構底層的生命本能,又可視為社會結構底層的勞苦大眾,當基本需求得不到滿足時,都會揭竿而起沖擊上層結構。它平時是溫馴的,戰時卻很容易變成一股摧毀性力量。當野獸完成了解救戀人的初級任務后,并未找到預想的羊群從而陷入迷茫之中。此外,巨型機器人最初由國王操縱成為殺戮利器,而后被小鳥控制,變成摧毀專制王國的鐵拳。它比野獸更強大更難以控制,即便在“懂技術”的小鳥操縱下,機器人砸落的磚塊還是讓所有人躲閃不迭,凝聚了無數智慧與心血的塔基卡迪王官也因此在瞬間成為廢墟。
無論是倚靠底層支持,還是借助科技力量,暴力革命在摧毀暴政的同時幾乎摧毀了一切。它并未開啟天堂之門,僅僅將蕭瑟肅殺甚至血腥的景象呈現出來。就像詩人荷爾德林所說:“使一個國家變成人間地獄的東西,恰恰是人們試圖將其變成天堂的夢想。”正是基于對暴力革命的反思,《國王與小鳥》超越了那些意在歌功頌德的革命電影,超越了具體利益集團和有限的時代,放射出不朽的人文價值。那位曾在革命前夜歡呼的盲人樂師,最終在白熊保護下才僥幸逃出崩塌的王宮。影片結尾用同一首憂傷的曲子與片頭呼應,巨型機器人擺出羅丹的著名雕塑《思想者》的姿勢,疲憊地坐在廢墟上,空洞的眼睛望著無盡的黃沙。這不是一個上升式結局,并未以個體愛情的實現來象征集體革命的大獲全勝。絲毫沒有勝利的喜悅,只有迷惘困惑與綿綿不盡的哀愁。革命勝利之后,那個沒有痛苦、沒有饑餓、自由平等、博愛的美麗新世界在哪兒?為了它,我們還將付出什么代價?現實中,無數次革命力圖解決這個問題,卻都折戟沉沙,以慘烈的犧牲為這一斯芬克斯之謎獻上祭品。這種情形就像盧梭在1762年出版的《社會契約論》中所說的:“人生而自由,卻無所不在枷鎖中。”這難道是人類的宿命?除了忍耐或者革命,有沒有第三條路可走呢?與影片溫情的基調相比,現實中的革命往往令人齒冷。“法國大革命進入了1793年,如同一匹脫韁的野馬,瘋狂而盲目地向前飛奔。試圖拉住韁繩將它制服的吉倫特派,不斷地抽鞭催它跑得更快的稚各賓派,二者的對立已經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斗爭的結果是吉倫特派的全面崩潰。”在這個背景下,吉倫特黨領導人之一,著名政治家羅蘭夫人被在朝的雅各賓黨送上斷頭臺,臨刑前留下名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而行!”革命者上臺后的迷失乃至變質似乎成為歷史的必然。在這一點上《國王與小鳥》無意深究,或許是受限于影片時長,或許是源于對情感基調的掌控。
四、結語
《國王與小鳥》的故事原型脫胎于安徒生童話《牧羊女與掃煙囪的人》:牧羊女和掃煙囪的人兩情相悅,牧羊女的爺爺卻中意高貴富有的羊角將軍,最后以有情人終成眷屬作結。這原本只是一則通俗愛情故事,但如果將這里的人物置換到另外—個情境呢?比如,專制政體的塔基卡迪王國。那么、我們將看到羊角將軍的貪婪自私演變為一個巨大的黑洞,將牧羊女和掃煙囪的人乃至整個王國吞噬進去。建立制度的原點,應當是遏制人性的邪惡面,而不是肆無忌憚地加以培植。從童話到電影的轉換中,我們當可看到綿延于歷史與現實中的人性的影跡。其他如《動物農莊》《我在伊朗長大》《和巴什爾跳華爾茲》等影片,又何嘗不是為相似的人性提供了不同情境的舞臺呢?正如黑格爾所說:“人類從歷史中吸取的惟—教訓就是人類從來不從歷史中吸取教訓。”這則人性的預言,還將啟示多少政治寓言的誕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