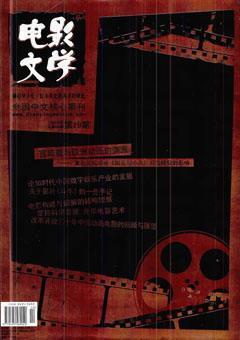《功夫熊貓》中的顛覆與重塑
譚利思 李文偉
摘要好萊塢動畫大片《功夫熊貓》憑著其功夫、熊貓這兩種中國符號引起了極大關注,本文試著在全球化背景下用東方學的觀點分析這部影片中西方強勢文化消解、顛覆東方一些傳統文化和價值觀念,而同時也進行著西方價值觀不動聲色、潤物細無聲的一種隱秘的宣揚的過程。
關鍵詞功夫;重構;東方
當時間跨入到21世紀,全球化加速了融合全世界不同文化的腳步。中國——這一屹立在世界東方的古老國家因其令人驚訝的經濟增長速度越來越令世人矚目。其廣闊的市場前景、深遠的政治影響力以及厚重的文化底蘊使得西方國家用新的目光來審視并向其普通民眾表現這個過去一直被視為落后的國度成為必要。然而,任何一種審視和表述都是有選擇性的。任何一種文學或文化作品都是對與其歷史相聯系的某一剎那的反映,都是一個龐大的帝國主義政治經濟體系結構有機組成部分。選擇什么來表述和表現,表現的內容是什么,讓其中的人們想什么以及讓作品的受眾成為什么或者讓他們想什么才是值得我們深思的。近現代的很多文學作品都印證了薩義德在其著作《東方學》以及《文化與帝國主義》的觀點,即文化一直參與著帝國在海外的擴張并且西方對東方文化的敵視態度一直保留了下來(《東方學》第276頁)。如果說“文學以某種方式參與了歐洲在海外的擴張”(《文化與帝國主義》第16頁),那么在21世紀的電子時代,我們可以推知,電影這種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娛樂產品,也用自己的方式參與著文化的滲透。
最近的一部好萊塢夢工廠出品的影片《功夫熊貓》再一次印證了該觀點,影片用大家喜聞樂見、老少皆宜的動畫片形式消解、顛覆著東方一些傳統文化和價值觀念,而同時也進行著西方價值觀不動聲色、潤物細無聲的一種隱秘的宣揚。
影片的主角阿寶是一只圓滾滾、笨手笨腳、貪吃,卻又樂觀、胸懷功夫夢的熊貓。他每天都得在父親經營的面館里幫忙,父親希望阿寶能夠子承父業繼承面館的生意,而阿寶卻有自己的夢想——成為功夫之王。然而對于一只胖乎乎的、未經過任何訓練、以賣面為生的熊貓來說,成為功夫之王無疑是癡人說夢,而這也恰恰是阿寶的父親一再警告他的話。但萬萬沒想到,他歪打正著被龜大仙(影片中的另一主要人物)選中,并且必須擔負起拯救整個山谷的重任:對抗殘豹——其真實身份是“師父”曾經的愛徒的入侵。
“文化對待它所包含、融合和證實的東西是寬容的;而對它所排斥和貶低的就不那么仁慈了。”(《文化與帝國主義》第17頁)。《功夫熊貓》的主創者們有意或者無意地把故事的背景定格在了清朝,這點從劇中清朝的服飾和打扮就可以看出來。清朝,對于所有的中國人來說是一個特定的時間,就是在這個朝代中原漢人先是被關外滿族征服后又被海外洋人所奴役,清末更是因全民吸食鴉片而被冠上了“東亞病夫”的屈辱稱號。很多愛國志士為洗脫這個恥辱的稱號進行了堅決的斗爭,這也是很多港產功夫片的重要的主題。功夫片能成為一種類型片,是中國功夫對流行文化的一個貢獻。很多西方人便是從功夫片開始了解中國,中國第一個走向世界的明星——李小龍也是功夫明星。
然而,對于西方觀眾而言,東方始終只不過是一個被觀看的對象。西方觀眾總是以一種審視、不參與的態度挖掘著東方所獨有的異質氣質,并將這種異質作為一種吸引眼球的資本搬上舞臺,展示給眾人。這樣的東方并不是現實中的東方,而是被東方化了的東方,或者是被重新塑造過了的東方(《東方學》第136頁)。東方的功夫是作為西方茶余飯后的談資出現的,相當于大餐中的佐料。功夫被當做是一種觀賞對象被重置、被重新建構和表述,要做到這點,表述者們必須借助一套抽象類型。影片主創人員憑借對幾十部港產功夫中獲得的對功夫的理解,試圖在這部影片中對功夫做一個全景式的展示。至此,影片的主創人員其實將他自己的社會所提供的東方形象打上了他自己的獨特烙印,表明了他們對東方可以是什么樣、應該是什么樣的看法(《東方學》第350頁)。因為“對西方而言,亞洲一直代表著遙遠、寂靜、陌生的異域;……為了使(東方)馴服,東方首先被認識,然后必須被入侵和占領,然后必須被學者、士兵和法官們重新創造。”(《東方學》第119頁)
影片中有一個掌握智慧、年邁的烏龜大仙。烏龜得道多年,智慧和功夫都高深莫測,殘豹被捕前的叛逆弒師、欲奪武功秘籍的行為被烏龜大仙一招化解。東方文化中烏龜是古代四圣獸之一,稱“玄武”,道教所奉之神,是不老的象征。中國古代帝王陵寢多有馱碑之龜。影片中的烏龜大仙在東方又被塑造成一個預言師、占卜家的形象,而在古代,龜殼恰恰是占h的必備工具。影片中,行動緩慢的烏龜大仙對未來發生的事情總能未卜先知,而對于迎接未來挑戰的繼承人——熊貓阿寶的選定也是充滿了偶然與荒唐的味道。烏龜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所有的偶然都是必然”。這是典型的東方道家哲學綜合式的思維方式,與信奉科學分析及理性思辨、講究邏輯和方法論、有根有據為特征的西方思維方式是矛盾的。而隨著電影情節的展開,我們可以看到,古老的東方權威在面臨后起之輩(殘豹)的挑戰或者說是威脅時,已經不能直面,它必須選出自己的代理人,并且在挑戰來臨之前仙逝。烏龜大仙仙逝的場景就像同大仙一同消逝的燦爛的桃花一樣,不留半點痕跡。古老的東方文明和智慧,在面對未來的問題和威脅的時候只能預知,不能直面并解決。
東方的荒誕和無邏輯性還體現在影片中熊貓父親的面店的由來上,熊貓父親的面店是打麻將贏來的,也就是通過賭博贏來的。賴以生存的家庭財產的獲得沒有任何理性可言,充滿了偶然性。另一個令人注意的細節是,熊貓的父親是一只鴨子,而熊貓父親——那只鴨子的祖上一直是鴨子,這使得熊貓的身世變得詭異起來。血統的不純暗示著東方文明身上帶有先天不足的印記(《東方學》第197頁)。
片中值得注意的另一個敘述是:在烏龜大仙和熊貓之間有一個浣熊師父。這個選擇耐人尋味,正如熊貓是中國所特有的動物一樣,浣熊完全是美洲土生土長的動物。影片似乎在說,東方文明如要生存和傳承,必須得向別人學習,要有一個西方作為中介和過渡的橋梁。浣熊師父理智、謹慎、兢兢業業,具有西方分析性思維所推崇的一切品質。影片中有一段表現了熊貓對師父動作和語言的滑稽模仿,而這點和自古以來漢家儒家文化對老師的尊敬的價值觀也是相違背的。自古以來,在儒家文化中,老師的地位相當于君親。對于老師的嘲弄和模仿即便是無惡意的也是被儒家文化看成是大逆不道的,而影片中的這段模仿除了能增加喜劇效果之外,其背后更是凸顯了西方人人平等、善于自我解嘲的價值觀念。在《功夫熊貓》這部影片中和平谷的居民無論男女都留著可笑的長辮子,當外來的威脅突然來襲時,居民們能做的不是拿起武器抗爭,而是收拾首飾細軟、拖家帶口地逃難。近代西方大眾文化對東方一向用一種漫畫式的表現,中國人的形象在一些影片中一直以妖魔化的形象出現。他們善于玩弄詭計,邪惡、荒誕而低賤;一般都是黑幫頭領、會功夫的保鏢、小商販、
擁有神秘力量的僧人;華人聚居的地方總是陰暗、骯臟、神秘。很少有電影表現華人的個人行為和經驗。“宣傳家的任務是設定一些目標符號,這些符號具有促使人們接納并且適應所定目標的雙重功能。必須誘發人們自覺自愿地接受。……因此理想的做法是通過直覺領悟而非強迫的方式控制事情的發展。”
更耐人尋味的是在影片結尾處揭示了大家都很期待的兩個秘籍,兩個都需要熊貓阿寶繼承和維護的秘籍——武功秘籍和面湯秘籍的秘密:都不存在。功夫其實并沒有那么神秘,東方也沒有那么神秘,幾代人頂禮膜拜、懷著崇敬的心情辛苦努力、費盡心思所保衛的所謂秘籍其實什么也不是,是一紙空文。至于這個每個人都想搶奪并占為己有的武功秘籍,影片并沒有交代它的來歷,因而歷代功夫大師對這個秘籍的堅守就變成了一種對虛無的捍衛,整個過程變得荒誕可笑,沒有任何邏輯性可言,而這恰恰是西方對東方的界定和描述:東方是怪異的、沒有邏輯的、有著旺盛的感性情感的。西方從這種表述中得到樂趣。武功秘籍代表著熊貓的最高精神理想,面湯秘籍則是熊貓世俗生活的保障,這些似乎都在暗示著東方文化從世俗到精神都不是原本大家所認為的那么神奇。
功夫作為東方所特有的一種健身體育項目對于西方來說,其神秘的特性,始終具有一種誘惑力,這從上世紀70年代起,功夫片熱潮漸起并成為一種電影類型片以及一些功夫片明星能夠在競爭激烈的好萊塢有一席生存空間就可見一斑。在東方的游俠或武俠文化中,反派角色常常是一種外來的反叛力量并總是懷著獨霸天下或獨霸武林的陰謀,以某部武功秘籍為線索展開正義與邪惡的爭奪,20世紀70年代的港產功夫片,更是將這種武俠精神賦予了一種民族正義感的神圣光圈,人們正是從黃飛鴻、霍元甲腳踢拳打在中國國土上跋扈橫行的洋人的劇情中受到鼓舞和振奮,這也恰恰是為什么功夫片會大受歡迎的原因之一。功夫在影片中也只是一種搞笑手段,無非就是飛檐走壁,是一種花哨的可被人觀看的雜耍性的表演,這點從影片開始時東方神龍的選秀中可以看出。本來神圣的功夫高手選徒硬生生被鑼鼓喧囂的集市所消解。影片借著“功夫”“熊貓”這兩張東方牌敘述著一個符合西方審美觀和價值觀的個人英雄主義的故事。
西方文化在描述、界定東方時是無法揭示出一個廣博而豐富的東方的,這時候它需要挑選出東方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部分。功夫和熊貓恰恰是符合這種特性的。這兩者都是中國所特有的文化和生物現象,這就決定了將這兩者結合便有了表述東方的強大的力量。影片中西方人通過人物所持的語言——英語在場。
通過整個影片可以再次看到“……東方從一個地理空間變成了一個受現實的學術規則和潛在的帝國統治支配的領域。”薩義德曾說過,東方話語產生的條件是軍事上比東方要強大得多的西方。而在當代社會,西方不僅憑借著其強大的軍事力量作為后盾,更多的是在對作為其異質而存在的東方進行經濟、文化上的滲透與控制。特別在電子時代,當互聯網悄悄地改變著人們交往、閱讀的習慣,把世界變得越來越小時,龐大而又復雜的好萊塢電影制作機制也以一種積極的姿態加入到對該領域進行規劃和管理當中來了。影視作品以其直觀性、普遍大眾性以及較高的娛樂性成為各國文化宣傳的提速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