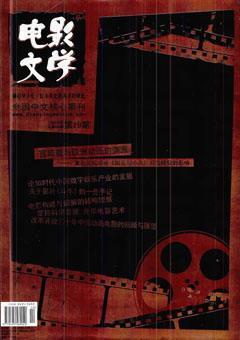《肖申克的救贖》所折射的美國假釋制度的成敗
周 艷 俞 彬
摘要《肖申克的救贖》講述了青年才俊銀行家安迪·桂弗倫被指控謀殺入獄,并最終奔向自由、重獲新生。影片所敘述的是監獄對人是如何從肉體和精神上進行改造的,該片的諸多細節都可以寫成研究美國刑事司法制度的文章。其中安迪的牢友瑞德和布魯克斯展示了美國假釋制度的起源、執行及其最終作用。
關鍵詞《肖申克的救贖》;瑞德;假釋
《肖申克的救贖》(The Shawshank Redemption)講述了青年才俊銀行家安迪·杜弗倫被指控謀殺妻子及其情夫,在經過19年的漫長等待之后,他最終奔向自由、重獲新生。該片不僅僅是一部越獄的懸念片,它同時也說明監獄對人是如何從肉體和精神上進行改造的。該片的諸多細節都可以寫成研究美國刑事司法制度的文章。其中安迪的牢友瑞德和布魯克斯展示了美國假釋制度的主要特征。
一、《肖申克的救贖》體現的美國假釋制度
安迪的牢友瑞德是影片的第二號人物,他有三條人命在身,所以被判為終身監禁。在安迪入獄時,他已經在獄中服刑20年。安迪和瑞德在漫長而艱苦的監獄生活中,結下了深厚的友情。瑞德分別于1947年(入獄第20年)、1957年(入獄第30年)兩次申請假釋都被拒絕。劇中還有一位人物布魯克斯,1905年被關進肖申克監獄,在被關了50年假釋出獄,而這時他已是一個80歲的老人了。瑞德入獄第40年后,在第三次申請中得以假釋出獄。
美國的假釋制度是伴隨法院“不固定刑期”制度產生而產生的。假釋制度肇始于18世紀的歐洲。1868年,美國制定了假釋法,第一次將假釋納入刑罰執行制度的范疇。1930年,美國國會決定成立全國假釋委員會,到1944年,美國聯邦政府和各州均確立了假釋制度,在一些主要的工業州。80%的重罪犯人通過假釋的途徑走出監獄大門。在1997年,美國的假釋人數為52.7萬,占監獄在押犯的45%。假釋制度成為解決監獄擁擠以及使罪犯重返社會的重要途徑。特別是對被判終身監禁的人來說,這幾乎是他們活著走出監獄的惟一方式。
美國的假釋制度可以分三種形式。第一種形式是,假釋委員會對“不固定刑期”的判決幾乎有絕對的決定權。第二種形式是,法律對假釋委員會的決定權實施某些限制,例如法律規定,犯罪人員必須在服滿最低刑期之后才能被考慮是否給予假釋以及某些犯罪不能得到假釋,犯罪人員必須服滿整個刑期才能出獄等。第三種形式是。對于“固定刑期的判決”,假釋委員會在是否釋放監獄犯人的問題上沒有任何決定權,它只能設定假釋條件,如果犯罪人員在假釋期間違反了假釋規定,假釋委員會有權撤銷他的假釋資格。美國的假釋制度目前主要在州一級才有,而且每個州的情況不同。
有權力做出假釋的為美國聯邦假釋委員會(UnitedStates Parole Commission),該委員會成立于1930年,屬司法部領導,處理聯邦監獄罪犯的假釋問題。各州情況差別很大。雖然絕大多數州仍然有關于假釋的規定,但是只有14個州保留了假釋委員會。假釋委員會成員備州不一,少的3~5人,多的超過10人,一般由州長任命,多數任期5~6年。一個犯人的假釋,是要看罪犯是否已經“洗心革面”。在《肖》中對瑞德的三次假釋重點進行了表現。每次都是假釋委員會委員3~5人,到監獄中聽瑞德的自白,都問他:“你改過自新了嗎?”
二、瑞德三次假釋申請體現的假釋標準
按照當時美國的假釋制度,瑞德可以獲得申請假釋的機會,影片給出了瑞德三次申請假釋的不同場景。
第一次應當是1947年,也就是安迪入獄的同一年,鐵門打開,瑞德走進假釋委員會的辦公室,表情緊張不安。
委員會的官員問:“你改過自新了嗎?”
瑞德答:“是的,絕對如此,我已經得到了教訓,我已經洗心革面。上帝作證,我不會再危害社會了。”
結果是:駁回(REJECTED)。
第二次是1957年,這時是布魯克斯獲假釋后在絕望中自殺,這讓瑞德意識到假釋雖然意味著獲得自由,但也意味自己將成為社會棄兒。可是自由對于被關了30年的人來說畢竟是魅力難擋的。鐵門打開,瑞德走進假釋委員會的辦公室,去等待當局的決定。瑞德在門口立正,然后坐下,臉上帶著企盼和討好的笑容。
委員會的官員問:“你改過自新了嗎?”
瑞德答:“我已經洗心革面,上帝作證,我不會再危害社會了。我已經完全洗心革面了。”
結果仍是:駁回。
第三次是1967年,此時安迪已經成功越獄,和安迪為友的日子使瑞德對希望、自由和罪惡都有了不同的理解。所以瑞德對于結果并不抱希望,他在門口立正,然后坐下,表情沉靜,甚至有些高傲。
委員會的官員問:“你改過自新了嗎?”
瑞德回答:“改過自新?我想想,我還真不知道‘改過自新是什么意思?”
官員說:“就是說準備好了重返社會。”
“這我懂,年輕人,”瑞德回答,“對我來說,這只是政客發明的虛詞,讓你們穿西裝打領帶有活干,你到底想了解什么呢?我是否后悔曾經犯罪嗎?”
“你后悔嗎?”官員問。
“我沒有一天不后悔,但這并不是因為受到懲罰才感到后悔,而是覺得應當后悔。當我回首往事的時候,看到那個犯下重罪的小蠢蛋,我想跟他談談,跟他講講道理,但我辦不到,因為那個傻小子已經不存在了,只剩下我這個垂老之軀。我只能接受這事實。
‘改過自新?狗屁不通的詞!你蓋章吧。別在這兒浪費我的時間。”
結果是:同意(APPROVED)。
回顧三次審查,其委員一次比一次年輕,用語一次比一次客氣,而相對比的是瑞德的一次比一次衰老。前兩次的申請被拒絕讓他根本看不到希望;同時對于社會也有著恐懼心理使他認為最好呆在獄中。所以其語言也是玩世不恭的,對于假釋的標準——改過自新,進行了冷嘲熱諷。對于假釋委員會委員也毫不留情。這里涉及一個重要的司法問題——假釋的標準,就是犯人是不是已經改過自新了。
瑞德能否假釋的場景只圍繞一個問題,那就是瑞德是否“改過自新”了,但什么是“改過自新”,用什么來判斷“改過自新”,這樣的問題恐怕連高堂之上的官員也難說真正明了。但罪犯自己卻能夠明白,如果他的靈魂里再也找不到原來的影子,那他的確是已經改過自新了。假釋,要想作為一項有意義的刑罰制度,它的實質性條件應當在于,罪犯是否改造好了,或者說是否對社會不再造成危害了,但這兩個乍看之下和諧統一的標準對于現實個體來說卻充滿了矛盾。
假釋是一項特權,而不是權力,監獄犯人有申請假釋的自由,但不一定能得到假釋。在美國幾乎所有的司法管轄區,監獄犯人都必須在服滿一定刑期之后,才有申請假釋的資格。監獄犯人服刑多長時間因州而異,不同犯罪判刑也不同。監獄犯人服刑一段時間,并具備申請假釋的資格以后,一般會整理出一套材料,列舉自己在服刑期間做了些什么以及參加過哪些計劃等,他還會把計劃負責人員、監獄官員和教師的推薦信以及他返回的社區中有雇主
愿意雇用他的證明,呈交給假釋委員會。他一般會表示對自己的罪行感到悔恨,并保證永遠不重犯。假釋委員會還要派假釋官員到監獄犯人所在的社區,對他將來的就業和住處等情況進行調查。在確定一切都符合要求之后再將其釋放。同時在假釋期間,犯人必須遵紀守法,不能擁有武器,不準吸毒,必須遵守假釋官員提出的所有規定等。如果獲得假釋的犯罪人員違反假釋條件,他就會再次被關入監獄,繼續服刑。所以瑞德越境前往墨西哥,就是違反了假釋條例。
三、瑞德和布魯克斯的結局是對假釋制度的批評
《肖》中,布魯克斯出獄后,無法適應社會生活,使他壓力越來越大,整日生活在恐懼之中,最后自殺。50年的監禁生活,早已把布魯克斯“體制化”了。瑞德結合監獄所說的那樣:“這些墻很有趣。剛入獄的時候,你痛恨它們;慢慢地,你習慣了生活在其中;最終你會發現自己不得不依靠它們而生存。這就叫體制化。”而瑞德自己,盡管他比布魯克斯有能耐,比布魯克斯精明,在監獄里什么東西他都能搞到,但也被監獄“體制化”了。他甚至認為自己像布魯克斯一樣,我在外邊做不了什么。所以,他一點也不希望走出監獄,所以第三次假釋委員會問他改造好了沒有,他才那么冷嘲熱諷,玩世不恭。假釋后瑞德也和布魯克斯一樣,總是感到莫名的惶恐,渴望重回監獄,他說:“我要面對殘酷的現實,永遠無法適應外面的生活,腦子里老是想著怎么樣破壞假釋條例,好讓他們送我回去,生活在惶恐之中,太可怕了,布魯克斯知道這一點,知道得太清楚了。我只想回到我熟悉的地方,在那兒,我不必誠惶誠恐。”
從影片看出,當罪犯不再對社會具有危險性,是否刑罰已經將他正常生活的能力也連同犯罪能力一同剝奪了呢?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刑罰的結果遠不是改造了,或者矯正了罪犯,因為罪犯雖然不再是危險人了,但也不再是正常人了,他是一個無法重返社會的病態人。《肖》片中的布魯克斯就是這樣的人。假釋制度顯示出人性化的一面,也解決了監獄人滿為患的問題。但也存在著影片中所反映問題。所以,這種制度始終是美國刑事法中引起廣泛爭議的問題。支持和反對的都大有人在。反對假釋的人認為。美國在過去15年中采取了嚴厲的法治政策,這個政策說:我們不能縱容罪犯,他們既然犯了法,就應該在監獄中接受懲罰,而且一部分人是無法重返社會的病態人。還有人認為,假釋制度在實際運作中不是很成功。因為假釋的犯罪人員知道。如果自己表現不好,不做一個好公民,就有可能被送入監獄繼續服刑。但實際上,因為得到假釋重返社會的犯罪人員的人數太多,而社會為他們提供的資源卻很缺乏,導致他們重新犯罪。這在本片中布魯克斯和瑞德身上,就有所體現。他們已經成為無用之人,總是想再次犯罪,從而回到獄中。所以,到了20世紀70年代中期,美國的假釋制度出現大的變革,重新確立的判刑條例要求法官施以“固定刑期”,而且對很多刑事犯罪都規定了必須有最低刑期,有些假釋委員會也被取消。1984年,美國國會通過《全面控制犯罪法》,在聯邦一級廢除了假釋制度。根據這項法律,在1987年11月1號之前有過犯罪活動的聯邦監獄犯人在服滿三分之一刑期后,仍然有資格得到假釋,但是,在這之后有犯罪行為的聯邦監獄犯人不享受這種待遇。如果他們在獄中表現好,每年最多可以減刑54天,釋放后一段期間內仍要繼續接受監視。
四、結語
影片就是通過布魯克斯和瑞德的命運。將被“體制化”后的悲慘生活狀態淋漓盡致地向我們展示美國假釋制定的成與敗、好與壞。如果罪犯在內心上不能自認有罪,又怎能認為他會接受被懲罰,哪怕只是被矯正呢?而對于認罪的人,又如何使之不成體制化的產物,不是讓被假釋的人成為社會問題。成為被掃出門的垃圾。這又為中國的假釋制定提供了重大的借鑒意義,促進我們如何才能建立—個科學而完善的司法體制和改造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