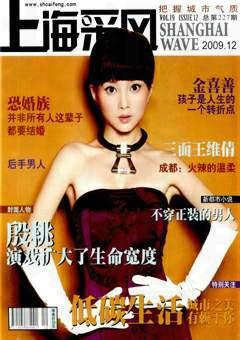后奧運的空間想象
張頤武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從事中國當代文學、電影、大眾文化和批評理論的教學與研究。90年代以來,在全球化與中國當代文化關系方面進行了一系列前瞻性的研究,著有《在邊緣處追索》、《大轉型》、《從現代性到后現代性》等論著多種。
奧運之前,我總是感到北京人有一種把未來的時間借到現在的強烈的渴望。是,大家都習慣于把當時還在建設的鳥巢、水立方等當作現實的存在來認知,我們會從三維動畫、圖片和PPT的展示來接觸這些尚未建成的建筑,我們常常想象它們已經在我們身旁存在了。我們常常如此現實地談論它們。我們常常把這個虛擬的北京和真實的北京混淆起來,想象補充了現實,擴張了現實,使得想象比現實更現實。因為這些建筑是我們對于北京未來現實的一種建構,它們在現實中的建設和我們在想象中對于現實的展開是同步進行的。我們想到奧運的那個時刻,想到一個社會可能的前景就會心馳神往,不能自己。因此,這些建筑其實不僅僅是體育場館,而是一個社會自己夢想的投射,所以我們才會讓這樣驚世駭俗的一切展現在我們面前,我們才有熱情將這些建筑變成現實。而在這個過程之中,我們經歷了一個高速成長的社會對于自身想象的展開。
奧運過去,鳥巢和水立方已經作為城市的地標存在于我們身邊。它們非常巨大,具有超越性的形象,顯示了這個城市的體量和能量,但太大而難以具體化地使用,太宏偉而難以世俗化地感受。而承載這一象征的歷史事件已經完成,它們最核心的功能就已經通過十六天的奧運得到實現了。于是,我們會面臨它們如何被具體地、世俗地使用的困惑。它們標定了我們的夢想的高度,而城市的日常生活其實往往還是平淡無奇的,城市的底色還是具體而微的。而這樣的象征物如何和一個城市平淡無奇的日常生活平和安適地相處就變成了一個不易處理的現實課題。西方當年有個現代藝術的潮流未來主義,但未來主義式的建筑變成了現實,而且還是想象已經實現后的現實,如何讓它脫胎換骨,在現實之中既保持它的象征性,有又實實在在地有用,就不那么容易了。
其它那些運動場館都容易發現它們的多樣功能,因為它們本身沒有多少象征性,也不會激發出象征物所具有的高度的意義,因此轉成什么,大家都不會有異議。如在北大的乒乓球館,就順勢改造為游泳館,這當然都是必然的,也不會有所爭議。而鳥巢和水立方原有的象征意義和超越性的形象,使得許多平常的使用讓人覺得會消解它的象征性。就好像當年梁左寫的那個關于天安門廣場變成農貿市場的相聲,正是由錯位產生的笑談。所以,后奧運時代,現在我們在這樣宏偉的空間中所能做的,一方面是參觀和回味當時的盛況,另一方面還是在上面做宏偉的極品演出,也就是在其中做加法。無論成龍、宋祖英還是張藝謀的《圖蘭朵》都是這個城市的極品的盛事,都是嘗試大體量的空間中展示出的壯觀的、難以重復的演出。這當然有道理,也是大家必然的選擇,也是成功的選擇。因為奧運過去才一年,大家都還在回味那宏偉的開幕式。因此在這上面做加法,也就是不斷出現相當宏偉的大規模的演出時一個可行的策略。這些新的演出雖然同樣了不起,但肯定不可能做到像開幕式那樣的恢弘。加法讓恢弘的背景還有自己的價值和意義,也使得這個空間被利用了起來。但大家當然還會感到這個空間還是太大,這樣的演出還是覺得撐不滿場子。但我覺得加法還是可以做的,而且以后還可以繼續做下去。但這種加法必然不可能日常化,不可能讓鳥巢有平常的應用,而僅僅是幾個月才可能有的奇觀和盛事。
我其實覺得還有做減法的機會。特別的時候做加法,平常做減法。像這樣宏偉的空間,一個演出,或者一個表演當然撐不滿,還是覺得空。那么何妨把它零散化,把它分成一些區域,一些多樣化的表演的空間。比如用馬戲表演式的大棚將它分割成不同的區域,這樣整個鳥巢就活起來了,這里可以有話劇的表演,可以有馬戲和時裝展示等等,也可以有其他的有趣演出。它的象征性是一個大背景,而它的內面則有都市的日常生活在延續,這樣整個空間有它日常的應用,變成了城市固定生活的一部分。而同時也可以在真正的大規模的演出或象征性的事件來到時,可以合為大空間來做大手筆的事情。當然這就需要新的設想和新的意念與設計,也需要有別出心裁的靈活的想象力,也還需要讓年輕人、老人、孩子、旅行者在這里逐漸開發出他們的創意可以想到的新的功能。這里是開放的、有活力的,才會讓它真正成為城市有機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