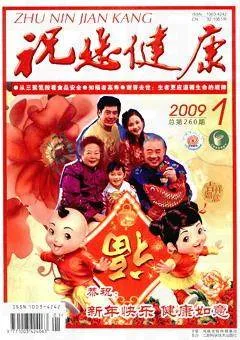知福者高壽
司長河
清代養生家石成金有一首《知福歌》:“人生盡受福,何苦不知足;思量愚昧苦,聰明就是福;思量饑寒苦,飽暖就是福;思量負累苦,逍遙就是福;思量離別苦,團圓就是福;思量刀兵苦,太平就是福;思量牢獄苦,自在就是福;思量無后苦,有子就是福;思量疾病苦,健康就是福;思量死去苦,活著就是福;苦境一思量,就有許多福;可惜世間人,幾個會享福;有福要能知,能知才享福;我勸世間人,不要不知福!”石老先生的這些話,平實質樸,耐人尋味。提醒那些境遇不順的人,要穩住神,不要因為一點挫折而失掉了生活的勇氣;要善于自我寬慰,淡泊名利,笑對逆境。我想,人生只要能活到這個份上,肯定能長壽。
大凡人,對幸福都情有獨鐘,從不放棄對它的向往與追求。而對幸福的認知卻各有千秋,有的認為有錢就幸福,有的感到工作著就幸福,還有的覺得家庭和睦就幸福等,不一而足。而自古以來。一切賢哲都主張修身養德,以保持精神上的愉悅為幸福,故而有“大德必得其壽”的說法。
周游列國而屢不得志的孔子,以“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為養生法而活了73歲:為官杭州的白居易享年75歲,以清白廉明為做官之道,當地人送他兩塊“天竺石”,他用“懼此兩片石,無乃傷清白”而自律;眾所周知的劉墉,可說是為官做人擇善納福一生,無私無畏,于嘉慶九年(公元1805年)安然而去,時年85歲;清代著名畫家、詩人鄭板橋,曾任縣令,是位廉吏,后來辭官不做,以賣字畫為生,活到72歲。鄭板橋寫過這樣一首詩:烏紗擲去不為官,囊橐蕭蕭兩袖寒。寫取一支清瘦竹,秋風江上作漁竿。如此無足輕重地對待功名利祿。心情恬靜,自然有利于福壽延年。據史載,堯活118歲,舜活110歲,都與他們圣賢仁愛,節制欲望,淡看榮辱得失,知福常樂不無關系。
不過,真正福至心靈的要算是戰國時期著名的哲學家、思想家和文學家莊子,在人均壽命只有30歲的先秦時代,他竟然活了83歲。他在《莊子·天道》篇中寫道:無為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意思是說,對一個從容自得,清心寡欲,泰然自若的人來說,任何的憂愁病患不能在他身上停留,所以他能延年益壽。這大概就是現代人所說的“精神系統的健康”。看來“無欲壽自長”是人生幸福的首要條件。
相反,放眼世界,能做到“生在福中知福”和“精神內守”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我家鄉就有這么一個民間傳說:有一個富人,全鄉十里八村的土地都屬于他。可他還想另一個村的土地,但那個村的人就是不讓。有一天。一個窮人對他說,你只要扛著村東的那半塊磨盤走上10里路,中間不準停歇,我就把地讓給你。富人看了那塊磨盤,足有100公斤重。當他扛著磨盤走到9里路時,就體力不支,口吐鮮血,想用力甩掉為時已晚,腿一軟,被磨盤砸死了。傳說的真假,無關緊要。其中蘊含的道理對我們應有所啟迪:不知足的人,可能什么也得不到。
大家都知道有句老話:人心不足蛇吞象。“不足”的“人心”無幸福可言。在明、清之間,有一本閑書,名叫《解人頤》。其中,有一首白話詩:終日奔波只為饑,方才一飽便思衣。衣食兩般皆俱足,又想嬌容美貌妻。娶得美妻生下子,恨無田地少根基。買到田園多廣闊,出入無船少馬騎。槽頭拴了騾和馬,嘆無官職被人欺。縣丞主簿還嫌小,又要朝中掛紫衣。若要世人心里足,除是南柯一夢西。這是在告誡人們,欲望過高,就會煩惱叢生。總是這山看著那山高的人,幸福只會離他越來越遠。
人生不過百年光陰,除了一些基本的需求之外,還會有很多瑰麗的夢想。如果這僅僅作為多彩人生的一個點綴,倒也不失為一件好事。可是,有些人卻往往輕易地將一生的幸福全部押在一個不知足的追求上,并為此而勞精費神,這不是給自己制造了枷鎖又是什么呢?
(編輯王建國)